共赴山与海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共赴山与海(闻云笙四年)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
|
双男主照顾失明京圈大佬闻云笙四年,我任劳任怨,倾尽所有。如今闻云笙眼睛痊愈,所有人都觉得我会借此要挟他。但我却连夜离开了,连行李都不曾带上。 因为我不是他一个人的光,我要给更多人带去光。1宴会厅里水晶灯的光芒流泻而下,空气中交叠着香槟的馥郁与名流们低语的笑谈。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一切浮华光影都簇拥着中心那个人,闻云笙。他穿着剪裁精良的黑色礼服,身姿挺拔,曾经蒙尘的眼眸此刻深邃锐利,正与人从容谈笑,举手投足间又是那位掌控一切的京圈翘楚。 四年失明仿佛只是一场被拂去的尘埃,不曾在他身上留下半分狼狈。 没人再记得他身边那个沉默的影子。我站在最不起眼的廊柱阴影里,手里托着一杯未动的酒,冰凉的杯壁沁得指尖微冷。视线掠过他英俊的侧脸,掠过满场为他痊愈而绽放的奉承笑脸,最后落在窗外浓重的夜色里。昨日闻夫人优雅的语调似乎又响在耳边,伴着茶香与无声的压迫感。精致的茶室里,她语气温和,措辞却像经过精密打磨的刀,每一句都恰到好处地划清界限。“时安,这四年,真是辛苦你了。没有你,云笙不会恢复得这么好,我们闻家上下都记着你的情。”她将一张薄薄的支票推过桌面,釉色温润的茶杯映出她不容置疑的神情,“这是一点心意,足够你下半生衣食无忧。 云笙的眼睛好了,他的世界会变得很大,很不同……有些关系,需要回到更合适的位置上。
你明白吗?”我看着那张支票,数字后面的零确实能买断很多人的几年。 但我只是轻轻将它推了回去。“夫人,我照顾他,不是因为他是闻云笙,也不是为了这个。 ”我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上了一点轻松的意味,“他的眼睛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闻夫人眼底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是更深的审视,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以退为进的痕迹。 但她只看到一片坦然的倦怠。庆功宴的喧嚣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传到我所在角落时,只剩模糊不清的嗡鸣。我看着闻云笙,他正与人举杯,眼底重获的光彩锐利而明亮,彻底驱散了失明四年间偶尔流露的脆弱。他又成了那个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京圈大佬,不再需要谁亦步亦趋地搀扶、阅读文件、或是深夜耐心描述窗外渐明的天色。够了。 我无声地吐出一口气,最后看了一眼那繁华中心。然后转身,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衣香鬓影之地。我没有回那间住了四年的、属于闻家宅邸一隅的客房。 我的行李简单得近乎寒酸,一个背包装尽所有。唯一留下的是床头柜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里面是闻家给我的所有银行卡,分文未动。 一份我整理了近半年的、关于西南某个偏远山区小学的详细调研报告和长期支教申请确认函,那是他失明初期,一次听财经新闻提及教育资源不均时,曾哑声说过一句“若以后能看见,或许该在这些事上尽些力”的地方。我当时记下了,如今,连同我无法带走的、他用不上的东西,一并留下。机场广播响起通往云崖方向的登机提示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闻云笙”三个字。我顿了顿,接通,放在耳边。 那头是他惯有的、带着一丝颤抖的沉冷嗓音,背景里宴会的乐声还未散尽:“时安? 你去哪儿了?我没有看见你。”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带着刚恢复清明的锐利,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我望着舷窗外无垠的、翻涌的云海,天际线正透出第一缕曙光。 “闻先生,”我的声音透过电流,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头骤然沉默,只有压抑的呼吸声。我看着窗外的云海,继续开口,声音很轻,却清晰:“您的世界已经恢复广阔,不再需要我的手指充当您的眼睛了。 ”他似乎被这句话钉住了,过了好几秒,才像是找回了声音,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沙哑:“你留下的那份东西……山区支教?你什么时候……”“四年,”我打断他,唇角微微扬起一个他看不见的弧度,“从您第一次提到那个地方开始,就在准备了。每一天,都在准备。”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久到我以为信号已经中断。 最终,传来他极其复杂、几乎磨过砂纸般低哑的一句:“……你的梦想,可不可以等等我? ”航班起飞的推力将我按在椅背上,我看着窗外逐渐远离的、灯火璀璨的都市。“闻先生,”我轻声说,像是对他说,也像是对自己宣告,“我的梦想,从来是能看见更多人的世界发出微光,等不了人。”“再见。”电话挂断的忙音响起,我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窗外,云层之上,天光大亮。2从小到大,父母都一致认为我过分冷静。有明确的目标,直接的执行方式,连最后的结果都一丝不苟。 他们曾说我这性格,不像会为什么人或事狂热,注定活得清醒,也难免孤单。飞机平稳飞行,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我靠在舷窗边,下方是连绵不绝的、墨绿色的山峦,如同凝固的巨浪。 这与京城的繁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机舱内灯光调暗,邻座的乘客早已入睡,我的清醒却如同冰层下的流水,无声而持续。四年前,接到这份工作时,我刚从师范毕业。 最好的朋友抓着我的胳膊,又急又气:“时安!你疯了吗?放弃保研资格,去给一个瞎子当……当保姆?那可是四年!你的专业、你的前途都不要了?”那时的我,只是平静地收拾着简单的行李,语气没有起伏:“我需要钱。很多钱。闻家给的报酬,足够解决我家里现在的困难,还能有结余。”“那你的梦想呢?你说过想去支教,想去最需要老师的地方!”我拉上背包拉链,看向窗外车水马龙的城市。“梦想可以推迟,”我说,“但有些责任,不能。”朋友恨铁不成钢,最终颓然:“你总是这样,冷静得可怕! 好像什么都算计好了!”我沉默。并非算计,只是选择。用四年自由,换取家庭的喘息空间,以及或许还能攒下一点未来追逐梦想的资本。这委实是很公平。初见闻云笙,他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侧脸线条冷硬,周身笼罩着一层拒人千里的阴郁和暴戾,地上是摔碎的茶杯和飞溅的茶水。“滚出去。”他甚至没有转向我这边,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错辨的命令和厌弃。我没有动,也没有像前几任看护那样惊慌失措地道歉或收拾。 我只是站在原地,平静地陈述:“闻先生,我是新来的看护,时安。从现在起,由我负责您的日常生活。”他猛地转过头,空洞的目光精准地钉在我所在的方向,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怒意:“我说,滚!”我没有滚。日复一日,在他摔东西时沉默地打扫,在他拒绝进食时安静地将饭菜保温,在他深夜因噩梦或焦躁无法入睡时,用平静无波的语调为他阅读商业文件,或者,只是描述窗外的天气。“今天下雨了,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像一条条小河。”“天放晴了,能看到西山轮廓,顶上还有一点没化的雪。”他的暴戾和抗拒,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得不到预期的激烈反应,渐渐也就失了力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或许是他第一次下意识地在我递过温水时,准确地道谢,或许是他重病高烧,攥着我的手腕,模糊地呓语“别走”,或许是在某个沉寂的夜里,他忽然开口,声音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疲惫和依赖:“时安,再说说外面什么样。”我曾是他无边黑暗里唯一能抓住的、稳定而可靠的声音,是他的另一双眼睛。但我始终记得第一天朋友的话。这只是一份工作,一份报酬丰厚且有期限的工作。期限是四年,或者,到他重见光明的那一天。我尽职尽责,甚至称得上鞠躬尽瘁,但我从未让自己“陷”进去。我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在他休息时,在他处理那些由我念给他听、却无需我参与的公司事务时,我看书,在线学习课程,查阅所有关于支教的资料。闻家给的薪水极高,我几乎全部存了下来,一部分寄回家,另一部分,悄悄投向那个遥远的、他曾经无意提及的西南山陲。 我冷静地规划着四年后的离开,如同我冷静地接受这四年的禁锢。飞机开始下降高度,轻微的失重感传来。云层散开,下方是层叠的梯田和散落其间的低矮房屋。 一个小型机场的跑道映入眼帘。我的心跳,在持续了数小时的平静后,终于难以抑制地加快了一些。这里没有香槟、水晶灯和虚伪的奉迎。这里只有泥土、山风,和等待启蒙的孩子。手机早已没有信号。我与过去的那个世界,彻底切断。 我拎起那个简单的背包,随着人流走下舷梯。高原炽烈而干净的阳光瞬间拥抱了我,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猛烈地灌入肺叶。我深吸一口气,眯着眼看向远处苍翠的山峦。 一辆破旧的绿色皮卡停在机场外简陋的空地上,一个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的中年男人举着块歪歪扭扭写着“接时老师”的木牌。我走过去,朝他伸出手:“您好,我是时安。”“哎哟!时老师!可算等到你了!我是瓦拉小学的校长,你叫我老杨就成!”他的手粗糙有力,握手的力度透着真诚的热情,“路不好走,咱们得赶紧出发,天黑前得赶到镇上!”我坐上副驾,皮卡颠簸着驶上坑洼不平的土路,扬起漫天尘土。京城的一切,飞速后退,最终缩成一个模糊的光点,消失在重峦叠嶂之外。 新的生活,开始了。以我自己的名义,为我自己的梦想。 而在我曾经留下的那份支教申请报告扉页,用钢笔写着一行清瘦的小字,那是我四年前写下,却从未打算给任何人看的话。“他曾说想看的光,我替他去看见。 ”3皮卡在崎岖山路上颠簸,每一次颠簸都像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震得移位。 尘土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带着干燥而原始的气息。老杨校长絮絮叨叨介绍着学校的情况,声音混在引擎的轰鸣里,时断时续。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贫瘠山岩和偶尔闪现的一抹顽强绿意,思绪却不受控制地飘回四年前那个堆满医疗器材、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房间。 我和闻云笙的契合并不在于我始终以冷静的态度来维持我们薄弱的关系。 这更像两个孤独的灵魂在深夜寻求慰藉,也更像是艺术家和他的缪斯。 闻云笙不是传统的小说霸总,他更像是怀揣着一腔梦想的热血青年,奔走在建设康庄大道的泥泞上。四年前我是毕业生,他同样也是。海归的商学硕士,响当当的名号,加上闻家这个所谓的京圈第一的名头,他的未来大有出路。 闻夫人说他并不像外表一样冷漠,相反,他的性格极其好相处。 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祸端使得他变得有些暴虐。闻云笙在支援灾区时遭遇车祸,脑内大出血挤压视神经,意外失明。闻夫人说得没错。最初的闻云笙,并非后来那个阴郁易怒的盲人。车祸发生前,他刚刚从海外学成归来,顶着光环,却一头扎进了当时最不被看好的灾区重建项目。闻夫人提起儿子时,眼底有骄傲,也有无奈:“那孩子,心太热,总觉得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劝他慢慢来,偏不听……”我见到他时,那腔热血已被突如其来的黑暗和剧痛冻结、碾碎。 他被困在无尽的夜里,所有的抱负、所有的蓝图都成了讽刺。他摔东西,拒食,用最刻薄的语言驱逐每一个试图靠近的人,仿佛这样就能连同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一并驱逐。 但偶尔,在药物作用下昏沉时,或是疼痛暂歇的短暂间隙,那层坚冰会裂开一丝缝隙。 有一次,他深夜无法入睡,疼痛折磨得他精疲力竭。我例行公事地为他念一份商业简报,是关于某个偏远地区教育投资的可行性报告。他忽然打断我,声音嘶哑,却奇异地褪去了平日的暴戾:“……那种地方,路都没修通,投再多钱,见效也慢。 ”我停下阅读:“报告显示,长期回报在于人才储备和地区声誉提升。”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哼了一声,像是自嘲,又像是惋惜:“商人算账……可有些账,不是这么算的。 那里缺的不是钱,是……能扎下根的人。可惜,我看不见了。”那句话,很轻,却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我心里那片为他四年服务期规划的冰冷土壤里。还有一次,他难得情绪稍霁。或许是因为窗外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我向他描述雪花如何安静地覆盖了花园的枯枝。他忽然问:“你以前是学什么的?”“师范。 中文。”我答。“……老师?”他似乎有些讶异,随即又了然,“难怪,念东西比之前那几个听着舒服点。怎么来做这个?”“需要钱。”我一如既往地坦诚。 他顿了顿,没再追问,只是过了一会儿,极轻地说了一句:“可惜了。 ”不知是可惜我的专业,还是可惜他自己的境遇。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并非纯粹的雇佣关系。更像两个被困在各自囹圄里的灵魂,他在物理的黑暗中挣扎,我在现实的泥潭里前行。寂静的深夜里,我的阅读声,他偶尔破碎的言语,成了彼此唯一的慰藉。他是失去了疆场的将领,而我是暂时折翼的鸟。 我们互相依凭着那点微弱的热度,熬过漫漫长夜。4“到了!时老师,你看,那就是我们瓦拉小学!”老杨校长洪亮的声音将我从回忆里拽出。 皮卡停在一个简陋的黄土操场边上。几排低矮的砖房围成一个小小的院落,一面褪色的国旗在旗杆顶上飘扬。操场边上,十几个孩子穿着不合身的、洗得发白的衣服,小脸黝黑,眼睛却亮得出奇,正好奇又怯生生地望过来。没有钢琴,没有香槟,没有衣香鬓影。只有最质朴的山峦,和最澄澈的眼睛。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悄然落地。我推开车门,双脚踩在坚实的土地上。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被同伴推搡着,怯生生地走上前,手里捧着一束野花,五颜六色,沾着露水,有些蔫了,却努力绽放着。 “老师……好……”她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小声说道。我蹲下身,接过那束花,花香混着泥土味,扑面而来。“谢谢。”我看着她清澈眼底映出的自己的影子,露出了抵达后的第一个真心笑容。这一刻,京城、闻家、那四年,都真正成了遥远的背景。 我的新生活,在这一声稚嫩的“老师好”中,正式开始了。“这些孩子一直盼着你来呢,”老杨搓着手,黝黑的脸上笑容淳朴又带着点局促,“我们这儿条件差,留不住老师。 上一个老师走了小半年了,娃娃们的课都耽搁了。”孩子们围拢过来,不敢靠太近,一双双清澈的眼睛里盛满了好奇与小心翼翼的期待。 那束野花在我手中散发着淡淡的、顽强的香气。“没关系,杨校长。 ”我的目光掠过那些低矮的教室,墙皮有些剥落,窗户上的塑料布在风里哗啦作响,“这里很好。”是真的觉得很好。这里的一切都真实、粗粝,却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 与闻家那座精致却压抑的大宅相比,这里的空气自由得令人心醉。 老杨帮我提着那个有点小的背包,里面几乎全是书和教案,引着我走向其中一间教室:“这是你的宿舍,也是教室。后面隔出个小间,能放张床。 条件艰苦了点……”推开门,一股混合着尘土和木头气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屋子不大,摆着十几张陈旧却擦得干净的课桌,一块小小的黑板挂在墙上,角落用布帘隔开,后面放着一张窄小的木板床。“很好,真的。”我再次肯定,将那束野花小心地放在窗台上。 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棂照进来,在花瓣上跳跃。安顿出奇地简单。我没有多少东西需要整理,老杨校长忙着去给我张罗点热水和吃的,孩子们聚在门口不肯散去,窃窃私语。我走到门口,看着他们:“我叫时安,以后是你们的老师。”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参差不齐地、带着浓重口音地喊:“时——老——师——好——”我笑了。那一刻,四年在京圈顶级豪宅里积攒的沉静与疏离,仿佛被这山风吹散了些许。下午,我请老杨校长带着我熟悉学校周围的环境。瓦拉小学坐落在半山腰,俯瞰着散落在山坳里的几十户人家,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最难的是没有路,”老杨指着山下那条蜿蜒曲折、时隐时现的土路,“下雨就成泥汤,根本出不去。 娃娃们上学,近的走个把钟头,远的得天不亮就起床翻山。”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群山沉默,云雾缭绕在山腰。美得惊心动魄,也闭塞得令人窒息。 忽然想起闻云笙失明第二年,某个雷雨夜。他被窗外剧烈的风雨声搅得心烦意乱,无法入睡。 我坐在离床不远的沙发上,例行公事地为他描述:“雨很大,砸在玻璃上像鼓点。 花园里的树摇晃得很厉害。”他沉默了很久,忽然问:“如果是山里的孩子,遇到这样的天气,怎么去上学?”那时我以为他只是随口打发无聊, |
精选图文
 司柠林钦小说无弹窗(司柠林钦)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司柠林钦)司柠林钦最新章节列表(司柠林钦)
司柠林钦小说无弹窗(司柠林钦)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司柠林钦)司柠林钦最新章节列表(司柠林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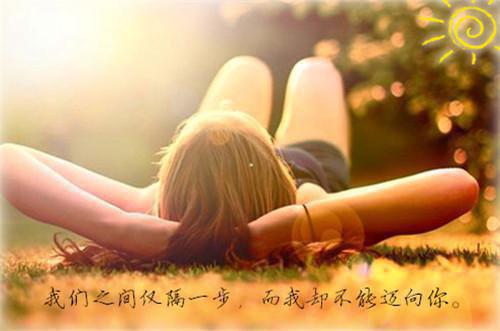 陆言裴昱慎小说(陆言裴昱慎)小说全文免费陆言裴昱慎无弹窗大结局_(陆言裴昱慎)陆言裴昱慎小说全文免费陆言裴昱慎读最新章节列表(陆言裴昱慎)
陆言裴昱慎小说(陆言裴昱慎)小说全文免费陆言裴昱慎无弹窗大结局_(陆言裴昱慎)陆言裴昱慎小说全文免费陆言裴昱慎读最新章节列表(陆言裴昱慎) 许时伊尚延景小说:许时伊尚延景(许时伊尚延景)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时伊尚延景:许时伊尚延景小说)许时伊尚延景小说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许时伊尚延景)
许时伊尚延景小说:许时伊尚延景(许时伊尚延景)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时伊尚延景:许时伊尚延景小说)许时伊尚延景小说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许时伊尚延景) 姬小卿墨衍(姬小卿墨衍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姬小卿墨衍)姬小卿墨衍小说最新章节列表(姬小卿墨衍小说)
姬小卿墨衍(姬小卿墨衍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姬小卿墨衍)姬小卿墨衍小说最新章节列表(姬小卿墨衍小说) 沈蓓依贺司晔小说:沈蓓依贺司晔(沈蓓依贺司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沈蓓依贺司晔小说:沈蓓依贺司晔最新小说(沈蓓依贺司晔)
沈蓓依贺司晔小说:沈蓓依贺司晔(沈蓓依贺司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沈蓓依贺司晔小说:沈蓓依贺司晔最新小说(沈蓓依贺司晔) 付胭霍铭征(渣了霍少后,她被囚宠了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付胭霍铭征)渣了霍少后,她被囚宠了在线阅读最新章节列表(付胭霍铭征)
付胭霍铭征(渣了霍少后,她被囚宠了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付胭霍铭征)渣了霍少后,她被囚宠了在线阅读最新章节列表(付胭霍铭征) 桑宓陆砚小说(桑宓陆砚)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桑宓陆砚)桑宓陆砚小说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桑宓陆砚小说)
桑宓陆砚小说(桑宓陆砚)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桑宓陆砚)桑宓陆砚小说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桑宓陆砚小说) 豪安檀容宴西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豪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豪安檀容宴西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豪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豪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
豪安檀容宴西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豪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豪安檀容宴西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豪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豪门:小公主就得放心尖上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