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新娘王爷请吃鸡(刺客灵堂)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在线阅读免费小说灵堂新娘王爷请吃鸡(刺客灵堂)
|
我被父亲逼着嫁给将死的靖王冲喜。花轿落地时,府内白幡飘荡,喜乐戛然而止。王爷已死? 直接守寡?我啃着烧鸡腿掀开棺材盖,里面的人突然睁眼。“王爷没死? ”我捏紧油乎乎的鸡骨头。他盯着我袖口露出的油纸包:“饿三天了,分我一只? ”当夜刺客破窗而入,他重伤未愈无力招架。我举起烧鸡腿塞进刺客嘴里:“敢动我饭票? ”棺材里传来闷笑:“夫人,护驾有功。”1.五岁那年,娘亲大病一场死了。
爹每次看到我,都会大哭一场。他说我和娘亲长得太像了。慢慢的,爹不怎么来了。后来,爹又娶了一个姨娘。再后来,姨娘生了两个孩子。爹更不来看我了。 从此我变成了王府里的小透明,只有娘的陪嫁丫鬟李嬷嬷一直照顾我。直到十六那年,有人给王府送来了一份江南丝路契书,爹的书房亮了一夜的灯。第二天,爹就把我叫到了堂前。妹妹苏清漪正死死攥着她娘亲的衣袖,哭得梨花带雨:娘,女儿不要嫁过去守寡!听说靖王爷……他、他撑不过这个月了呀!声音里的恐惧,大家都听的真切。姨娘和妹妹跪在地上一起哭,爹皱了皱眉,抬头看着我说:苏渺渺,爹已经收了聘礼,三日后,你就嫁进靖王府吧,给王爷冲冲喜。别听他们胡说,冲冲喜王爷就好起来了。嫁过去要安分守己,不要给王府丢脸。一个没娘的孩子,就成了这桩冲喜买卖里最合适的替代品。这三日,王府上上下下都在忙碌,忙着准备嫁妆,忙着装扮王府。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也没有在意我的感受。出嫁当天,婆子们都在忙着给我梳妆打扮,只有李嬷嬷偷偷塞给我两只烧鸡腿。 她浑浊的老眼里满是心疼小姐,拿着……垫垫肚子,王府里……指不定什么光景呢。 喜轿颠簸的厉害,轿外喧天的锣鼓和喜乐隔着厚重的轿帘传进来,格外刺耳,盖头闷得我喘不过气来,心口也堵的发慌。那股子被硬塞进这顶华丽囚笼的憋屈感,怎么也压不下去。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刺痛,总算是压下了喉头的酸涩。 另一只手却下意识地摸索到袖中那个油纸包。隔着粗糙的纸,能摸到里面那两只硕大、微凉的烧鸡腿。肚子适时地咕噜了一声,在空荡的轿厢里格外响亮。 我深吸一口气,管他什么规矩体统!一把扯下那碍事的盖头,胡乱塞进怀里,再毫不犹豫地撕开油纸包。浓郁的肉香猛地窜入鼻腔,瞬间盖过了轿内沉闷的熏香。 我狠狠咬了一大口,鸡皮焦脆,内里软嫩多汁,油脂的丰腴感暂时填满了空荡荡的胃和更空荡的心。嫁个死人怎么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琢磨以后怎么活。花轿终于停了。外面锣鼓喜乐被骤然掐断,死一般的寂静沉甸甸地压了过来。只余下轿夫们粗重的喘息,还有几声压得极低的、意义不明的咳嗽。我胡乱把啃了大半的鸡腿重新裹好塞回袖中,又手忙脚乱地抓起那方红盖头,胡乱往头上一蒙。指尖残留的油腻感,蹭在滑溜的绸缎上,分外狼狈。轿帘被猛地掀开。没有预想中喧闹的迎亲人群,也没有喜娘尖利的唱和。 刺眼的白光涌了进来,冲得人眼前发花。我下意识地眯起眼。目光所及,是铺天盖地的白。 白幡。白灯笼。白纱帐。覆盖了原本该有的喜庆红色。 一个穿着体面素服、腰系麻绳的婆子踉跄着上前几步,她脸上沟壑纵横,老泪纵横,声音嘶哑。王妃……老奴……老奴给您请安了……她扑通一声跪倒在轿前冰冷的石板上,身后呼啦啦跪倒一片素白的身影。王爷……王爷他…… 婆子抬起那张涕泪横流的脸看着我说道,……薨了!刚刚……刚刚咽的气啊! 连……连拜堂都等不及了!她哭嚎着,枯枝般的手颤抖着捧起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孝服,高举过头顶,直直递到我面前。您……您节哀!直接……直接守寡吧!她伸手来扶我。 我避开那只手,自己一步跨出了花轿。脚踩在冰冷的石板上,寒气透过薄薄的绣花鞋底直往上钻。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动那些白幡,发出扑啦啦 的轻响。几个穿着素白麻衣的下人垂着头,杵在廊下阴影里,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那个婆子大概是王府的管事,见我站着不动,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颤抖的声音压得极低:王妃……请随老奴来。她引着我,穿过挂满白幡的庭院。 我没有侍女,没有送亲的队伍,更没有所谓的娘家人。苏府,连同我那个爹,在我踏出花轿的那一刻,就彻底与我割断了。李嬷嬷那张布满皱纹、写满担忧的脸,在我心头一闪而过。我下意识地拢紧了袖子,指尖触碰到油纸包粗糙的边角。 管事婆子把我领到一处高大的正堂前。堂门洞开,里面光线昏暗,一股更浓烈的香烛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像是陈木和草药的味道扑面而来。堂中央,一口巨大的、乌沉沉的棺椁停放在那里。棺木前,供桌上惨白的蜡烛跳跃着昏黄的光,映照着灵牌上几个大字——靖王萧珩之位。王妃,管事婆子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同我说道。按规矩,您…您得给王爷…磕个头,见…见最后一面。 她的目光飞快地扫过我头上歪斜的盖头,还有袖口隐约透出的油渍,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最终什么也没说。我站着没动。红盖头遮住了我的脸,也遮住了我此刻的表情。 爹那句轻飘飘的冲冲喜王爷就好起来了还在耳边,像个笑话。 而我成了这场笑话里最合适、也最不值钱的祭品。最后一面?我开口,声音透过盖头传出来,有点闷,却异常平静,隔着棺椁,能见着什么? 管事婆子明显噎住了,脸上掠过一丝慌乱:这…这…王爷已然大行,不便惊扰…… 不便惊扰?我轻轻重复了一遍,带着一丝嘲讽。既是冲喜,不亲眼『冲』一下,怎知有无效果?话音未落,我猛地抬手,一把扯下了头上那碍事的红盖头。眼前骤然清晰。 昏暗的灵堂,惨白的烛火,漆黑的棺木,几张惊愕呆滞的脸。我谁也不想看,径直走向那口巨大的棺椁。沉重的乌木棺盖尚未钉死,只是虚虚地合着。 灵堂里响起几声压抑的抽气声,管事婆子失声惊呼:王妃!不可!万万不可啊! 她想要上前阻拦。我猛地回头,眼神冰冷地扫过她。目光里没有任何新嫁娘的羞涩或恐惧,只有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决绝和漠然。管事婆子被这眼神吓在原地,伸出的手僵在半空。 我转回头,双手抵在冰冷的棺盖上。乌木沉重异常,我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推! 嘎吱——沉重的摩擦声在死寂的灵堂里格外刺耳。棺盖被我推开了一道一掌宽的缝隙。 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药味混合着一种奇特的气息,猛地从缝隙里冲了出来。我屏住呼吸,凑近那道缝隙,朝里看去。昏暗的光线下,棺木内部铺着厚厚的锦褥。一个人躺在里面。 他穿着亲王品阶的深紫色寿衣,脸色灰白,嘴唇紧抿着,毫无血色。他静静地躺着,胸膛没有丝毫起伏,确实像一具冰冷的尸体。只是……那双紧闭的眼睛上方,两道墨黑的剑眉,斜飞入鬓,即使此刻毫无生气,也透着一股凌厉的余韵。他的鼻梁很高,下颌线条绷得很紧。这张脸,即使是死后灰白,也掩不住那种刀锋般的冷硬轮廓。 我死死地盯着那张脸,袖中的手指下意识地蜷缩起来,指尖捏住了油纸包里那根坚硬的鸡骨头。这就是我的夫君?一个死人? 一个被塞给我、让我陪葬的死人?愤怒和一种冰冷的荒谬感交织着,在胸口翻腾。 突然——棺中那张灰败的脸上,那双紧闭的眼睛,毫无征兆地睁开了! 2.那张脸的眼珠极黑,深不见底,像两口寒潭。里面没有任何将死之人的浑浊或涣散,只有一片冰冷的、锐利的清醒,直直地穿透昏暗的光线,撞进我的眼底! 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骤然停止了跳动。身体僵直,连呼吸都忘了。我袖中的手猛地收紧,坚硬的鸡骨头硌得掌心生疼,这细微的刺痛才让我找回一丝神智。 棺材里的人无声地把手放在唇边,对我比了一个嘘。我怔了一瞬,稳了稳心神,对身后的人说了句你们都出去吧,我想和王爷单独待会儿。待身边的人都退了出去,我才声音干涩地开口王……王爷没死?轻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 袖中捏着鸡骨头的手指,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棺中那双深黑的眼睛,极其缓慢地转动了一下。视线没有落在我的脸上,反而微微下移,极其精准地盯住了我那只拢在袖口、微微露出的油纸包一角。然后,一个沙哑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从棺材里传出来,微弱却清晰:饿三天了。分我一个?我没想到,他要说的就是这个?灵堂里的空气彻底凝固了,烛火不安地跳跃着。棺材里那双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我袖口的油纸包。荒谬!巨大的荒谬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最初的惊骇。给死人冲喜,死人却在棺材里睁眼跟我要吃的? 袖子里烧鸡腿的油腻感从未如此真实。我深吸一口气,此刻却格外清醒。不管他是人是鬼,是装死还是真活,我只知道,苏府把我扔进了这个坟坑。袖中的油纸包窸窣作响。 我飞快地抽出那个还没来得及吃的烧鸡腿,油腻腻地握在手里,递向棺内那道缝隙。接着。 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稳,甚至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干脆。棺内那只手动了。 一只骨节分明、异常苍白的手从紫锦寿衣的宽袖下伸出,精准地抓住了鸡腿的另一端。 他的手很稳,指关节微微泛白,显然虚弱,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感,利落地把鸡腿拖了进去。紧接着,棺材里传来一阵压抑的、急促的撕扯和咀嚼声。声音不大,但在落针可闻的灵堂里,清晰得令人头皮发麻。我靠在冰冷的棺壁上,听着里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进食声。过了好一会儿,咀嚼声停了。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食物下肚后的微弱气息:水。我目光扫过供桌。上面除了香烛,只有一个白瓷酒壶和几个供杯。我走过去,拎起酒壶晃了晃,里面有液体晃动的声音。 拔开塞子闻了闻,一股清冽的酒味。是祭奠用的清酒。我拿过一个干净的供杯,倒了小半杯,走回棺边,递了进去。那只苍白的手再次伸出,接过了酒杯。片刻后,空杯递了出来。 里面的声音似乎顺畅了些:你叫什么?苏渺渺。我接过空杯,放回供桌。 苏家庶女?他问,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是。我站直身体,目光落回棺内那道缝隙上,王爷没死,为何装死?我的问题直接得近乎莽撞。到了这一步,虚与委蛇毫无意义。 棺材里沉默了一瞬。那双深黑的眸子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寒潭。本王遇刺,重伤是真。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沉疴在身的虚弱,却字字清晰。『死』讯传出,只为引蛇出洞。江南丝路契书背后的人,坐不住了。他顿了顿,冲喜……倒是意外。 苏府把你推出来,打的好算盘。意外?我扯了扯嘴角。好一个意外,断送了我本就可有可无的人生。王爷现在打算如何?戏,得唱下去。 他的气息有些急促,外面……都是眼睛。『死』人,不能活。多久?等。 他吐出一个字,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等本王能下地。等幕后的人……露出马脚。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积攒力气,目光再次投向我的袖口方向。这灵堂,是牢笼,也是堡垒。苏渺渺,你既已入局,此刻出去,必死无疑。留下,本王或可保你一线生机。 你选。一线生机?我咀嚼着这四个字。苏府的回门?那是催命符。靖王府这口活棺材,外面是虎视眈眈的刺客和眼线。袖子里油纸包窸窣作响。留下,陪一个死人演戏,赌那虚无缥缈的一线生机。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异常平静,我留下。 没有第二条路。我走到供桌旁,拿起那个白瓷酒壶,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清酒。 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丝辛辣的暖意。我把空杯放回桌面,发出清脆的一声轻响。 不过,我转身,目光再次投向棺内那道缝隙,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王爷记着,您欠我一条命,外加一只烧鸡腿。棺材里,似乎传来一声极轻、极短促的气息,像是被呛了一下,又像是一声闷在胸腔里的笑。那双深黑的眸子在昏暗的棺木深处,似乎极快地闪动了一下。成交。3.灵堂的烛火跳动着,将我的影子拉长,扭曲地投在惨白的布幔上。偌大的正堂里,空气中飘着香烛、药味、血腥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烧鸡油脂冷却后的腻味。我拖过一个蒲团,放在距离棺椁几步远、靠近一根粗大廊柱的地方坐下。背靠着冰冷的柱子,视线却牢牢锁着那口乌木棺椁。黑暗像浓稠的墨汁,从高高的房梁、从四面的角落无声地渗透进来,渐渐吞噬掉跳跃的烛光。 灵堂的光线越来越暗,只有棺前那对白蜡烛还顽强地燃烧着,两簇幽微的火苗,成了这巨大空间里唯一的光源。寂静被放大了无数倍。风吹动白幡的扑啦声,烛芯偶尔爆出的轻微噼啪声,还有……从棺椁深处传来的,极其压抑、极其轻微的呼吸声。那声音时断时续,带着一种重伤之人特有的滞涩和艰难,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我的心跟着一紧。他伤得很重,装死消耗的体力远超想象。 时间在黑暗中缓慢地爬行。疲倦像冰冷的潮水,一阵阵涌上来,眼皮沉重得直往下坠。 我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掌心,尖锐的疼痛带来片刻清醒。不能睡。这灵堂看似只有我们,但谁知道暗处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口棺材?王爷萧珩,现在就是砧板上的肉。 就在这时——咳……咳……一阵极力压抑的、沉闷的呛咳声从棺材里传来。声音不大,但在死寂中格外清晰。咳嗽撕扯着他的气息,呼吸声变得更加破碎急促。我立刻起身,快步走到供桌前,倒了一杯清酒。走到棺椁旁,低声道:王爷? 棺内的咳嗽稍稍平复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更粗重的喘息。……水。 那个沙哑的声音挤出来,带着撕裂般的痛楚。我赶紧将盛着清酒的杯子从缝隙递了进去。 苍白的手颤抖着接过,很快,里面传来急促吞咽的声音。空杯递出时,他的手指冰冷,触碰到我的指尖。伤……他喘息着,只说了一个字,便没了下文,显然连多说一个字的力气都耗尽了。那压抑的痛苦透过棺木清晰地传递出来。我犹豫了一下。 他伤在何处?需要什么?我对医术一窍不通。袖中的油纸包还残留着一点余温。 我猛地想起李嬷嬷总念叨的,饿着肚子伤好得慢。他昏迷三日,只靠我塞进去的那点烧鸡腿和清酒……我转身走向灵堂门口。门虚掩着,推开一条缝。 冰冷的夜风立刻灌了进来。外面庭院一片死寂,白灯笼在风里摇晃,投下惨白的光晕。 廊下空无一人,那些仆妇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来人!我提高声音,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而不容置疑。过了好一会儿,角落里才窸窸窣窣地探出一个脑袋,是带我进来的管事婆子。王妃…有…有何吩咐?王爷虽已大行,但冲喜之礼不可废。 我盯着她,声音不容置疑。灵前需备清粥小菜,四时供奉。立刻去备些温热的米汤来,再取些干净的温水布巾。快!管事婆子眼神闪烁,似乎想说什么,但触及我冰冷的目光,最终只是哆嗦着应了声是,转身飞快地消失在黑暗的廊道里。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我回到蒲团坐下,背靠着柱子,竖着耳朵听棺内的动静。他的呼吸似乎平缓了一些,但依旧微弱得让人心悬。终于,管事婆子端着一个红漆托盘回来了。 上面放着一碗冒着微弱热气的米汤,一壶温水,还有一叠干净的素白布巾。 她远远地放在灵堂门槛内,像是怕沾染什么晦气,飞快地又缩了回去。我走过去端起托盘。 米汤很稀,温度也只是微温。布巾倒是干净的。我端着东西回到棺旁。王爷,米汤。 我将碗从缝隙递进去。里面传来轻微的声响,那只手再次伸出,接了过去。 接着是缓慢、小口的吞咽声。喝了小半碗后,空碗递了出来。 我又将温水壶和布巾递进去:水……擦洗。我不知道他具体需要什么,只能这样模糊地说。里面沉默了一下,然后传出布巾沾水拧动时细微的水声。过了片刻,他用过的、带着暗红血污的湿布巾被递了出来。血污的颜色在惨白的布巾上显得格外刺目。 我心头一沉。他还在渗血。换下的布巾被我扔进供桌下一个空着的铜盆里。做完这些,我重新坐回蒲团。灵堂里只剩下他偶尔几声压抑的轻咳和粗重的呼吸。疲惫再次汹涌袭来,意识开始模糊。4.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个恍惚。嚓! 一声极其轻微、却异常刺耳的异响,好像是瓦片被踩裂,从头顶漆黑的房梁上传来! 我全身的汗毛瞬间倒竖!睡意被彻底惊飞,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我猛地抬头,死死盯住声音来源的方向,却只看到一片黑暗。灵堂外,风声似乎也停了,一片死寂。 棺材里,萧珩的呼吸声也骤然屏住,消失无踪。来了!几乎是念头闪过的同时——哗啦!! !靠近棺椁后方的一扇高高的雕花木窗,猛地爆裂开来! 破碎的木屑和窗纸碎片像雪片般飞溅!一道黑影,裹挟着冰冷的夜风,迅疾地穿过破窗,直扑向那口停放在灵堂中央的乌木棺椁!黑影手中,一道雪亮的寒芒在昏暗烛光下骤然亮起,直刺棺盖缝隙!目标明确——靖王萧珩!快!太快了!我离得很近,身体的本能先于思考。 几乎是那黑影破窗而入、寒芒乍现的同一瞬间,我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从蒲团上弹射而起! 不是冲向刺客,而是扑向供桌!我的目标是供桌上那个沉重的白瓷酒壶! 那是我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有分量的东西!黑影的速度快得超乎想象!我刚扑到供桌前,指尖刚触碰到冰冷的瓷壶,眼角余光已经瞥见那道寒光,精准无比地刺向棺盖那道缝隙! 不!一声低吼卡在我喉咙里。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砰! 一声沉闷得令人心悸的巨响从棺内炸开!厚重的乌木棺盖, |
精选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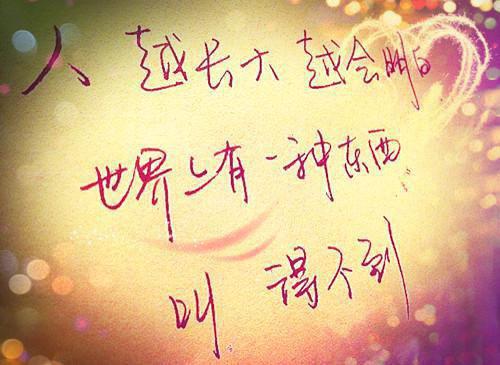 主角为褚赫越贺青穗的小说(褚赫越贺青穗)大结局免费阅读-褚赫越贺青穗全文免费阅读
主角为褚赫越贺青穗的小说(褚赫越贺青穗)大结局免费阅读-褚赫越贺青穗全文免费阅读 傅祁韫宋时漾(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傅祁韫宋时漾最新章节列表(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
傅祁韫宋时漾(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傅祁韫宋时漾最新章节列表(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 傅祁韫宋时漾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阅读无弹窗)穿越小说免费阅读
傅祁韫宋时漾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阅读无弹窗)穿越小说免费阅读 傅祁韫宋时漾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最新章节列表
傅祁韫宋时漾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蓄意撩惹:诱吻小玫瑰最新章节列表 池妤祁沉渊推荐免费新书 池妤祁沉渊高甜小说最新章节
池妤祁沉渊推荐免费新书 池妤祁沉渊高甜小说最新章节 池妤祁沉渊(池妤祁沉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池妤祁沉渊小说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
池妤祁沉渊(池妤祁沉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池妤祁沉渊小说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 乔喻孟以圆(乔喻孟以圆)小说全文小说免费阅读_乔喻孟以圆最新章节列表
乔喻孟以圆(乔喻孟以圆)小说全文小说免费阅读_乔喻孟以圆最新章节列表 谢晚筝邱驰川免费阅读无弹窗谢晚筝邱驰川(谢晚筝邱驰川)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谢晚筝邱驰川)谢晚筝邱驰川最新章节列表(谢晚筝邱驰川)
谢晚筝邱驰川免费阅读无弹窗谢晚筝邱驰川(谢晚筝邱驰川)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谢晚筝邱驰川)谢晚筝邱驰川最新章节列表(谢晚筝邱驰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