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者不回(姜霁月姜池)最新免费小说_完本小说免费阅读失者不回姜霁月姜池
|
1.落幕与继承电话铃响的时候,林溪正悬在半空。她腰上挂着安全绳,手里攥着一只500瓦的PAR灯,试图把它拧进头顶的灯架。舞台下方,导演用卷成筒的剧本指着她喊:“林溪!左边一点,再左边一点!光区要卡准男主角的脑门,不是他的领带!”“知道,别催。”林溪嘀咕着,手腕用力。螺丝滑了最后一圈,灯卡紧了。 她兜里的手机还在震,像个不耐烦的虫子。她腾出一只手摸出来,瞥了一眼。是老家邻居,陈阿姨。这个点打来,准没好事。她挂断,用牙咬掉一只手套,回拨过去。电话接通了,背景音里有嘈杂的人声,还有隐约的哭声。陈阿姨的嗓子又干又紧,像生了锈:“溪溪啊……你奶奶……走了。早上发现的,很安详。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林溪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灯架上的黑色胶带。下面导演又在喊:“灯!林工! 那灯到底好了没?排练要用了!”“好了。”她对着空气说了一句,不知道是回答导演,还是回答电话那头。声音有点飘。她清了清嗓子,“知道了,陈阿姨。谢谢您。我马上买票。 ”她挂断电话,把手机塞回兜里。手指有点僵,解安全扣解了两次。顺着梯子爬下来,脚踩到实木地板时,膝盖软了一下。导演凑过来:“怎么了?脸色这么差。”“家里有事。
”林溪把安全绳团起来塞进工具包,“我得请假。回老家。”“现在?开玩笑吧! 下周就首演了!”“我奶奶去世了。”林溪拉上工具包拉链,声音平直,没有起伏。 她抓起椅背上的外套,“手续我线上补。麻烦你了。”她没看导演的表情,径直往外走。 经过道具架时,顺手把一支摇摇欲坠的假花往里推了推。后台很乱,电线像蛇一样盘踞在地上。她小心地跨过去,一次也没低头。高铁呼啸着离开城市。 窗外的楼群逐渐稀疏,变成田地。林溪靠着窗,玻璃冰着她的额头。奶奶。 那个固执的老太太,守着一座破剧院过了大半辈子,最后连走都挑了个这么不凑巧的时间。 她上次回去还是春节。剧院更旧了,观众席的红色绒布座椅蒙了厚厚一层灰。 奶奶穿着旧棉袄,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指着空荡荡的舞台对她说:“你看,当年你爷爷就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幕布没拉好,他差点被绊个跟头。 ”林溪当时只关心奶奶的暖气够不够热,年夜饭的饺子馅够不够咸。她没接话茬。现在,那句话像个迟到的回声,撞在她耳膜上。天黑透时,出租车把她扔在剧院门口。门楣上,“自然之声”四个字的霓虹招牌大部分灭了,只剩“自”和“声”还顽强地亮着,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铁门没锁,虚掩着。她推开。灰尘味混着老木头特有的潮气扑面而来。 她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几下。头顶的一盏老式吊灯闪烁几下,勉强亮起昏黄的光。 观众席空着。舞台空着。寂静压得人耳朵发闷。忽然,舞台中央的黑暗动了一下。 一对幽绿色的光点亮起,缓缓转向她。那是一只通体漆黑的猫。它蹲坐在舞台中线的位置上,尾巴尖优雅地卷绕着前爪。像个谢幕后的主演。林溪和它对峙着。猫不动,也不叫。“喂。 ”林溪试着发出声音。黑猫站起身,伸了个漫长的懒腰。然后它轻巧地跳下舞台,无声地落在铺着破地毯的过道上。它从一排排空座椅前走过,最后停在她脚边。 用脑袋蹭了蹭她沾满灰尘的裤脚。喉咙里发出呼噜声,沉重又沙哑。 陈阿姨之前电话里好像提过一句,奶奶养了只老猫,叫墨瞳。看来就是这位了。林溪蹲下身,手指犹豫了一下,落在猫头上。皮毛温暖,骨头坚硬。“就剩你了?”她问。 猫的呼噜声更响了。绿眼睛在昏暗光线下,深不见底。它转身,尾巴扫过她的小腿,朝着舞台侧面的小门走去。走几步,回头看她。意思很明显:跟上。林溪吸了口气,站起来。 工具包还挎在肩上,沉甸甸的。里面装着螺丝刀、钳子、胶带、测电笔。 对付现实问题的工具。现在,她要跟着一只猫,走进一场落幕的戏里。 2.尘封的舞台与不眠的观众墨瞳没走小门。它轻巧地跳上舞台,消失在厚重的深紫色幕布里。林溪没跟上去。她走到观众席第一排,中间那个位置。 奶奶常坐的地方。绒布座椅的弹簧发出疲惫的呻吟。她坐下,把沉重的工具包放在地上。 视野很好,正对舞台中心。吊灯的光线勉强铺到台口,舞台深处是一片模糊的黑暗。 空气里有灰尘和旧梦的味道。她得想想接下来怎么办。丧事要办,剧院要处理,这猫……也得找个地方安置。脑子里乱糟糟的,像缠成一团的信号线。“嘿。 ”她对着空荡荡的剧场出声,声音被吸走了,没一点回声,“有人吗?”当然没人。 只有墨瞳从幕布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绿眼睛瞥了她一眼,又缩回去。 像是在嫌弃她问了个蠢问题。林溪扯了扯嘴角,站起来。还是先干点实际的。她找到电箱,闸刀老得快掉牙了。她推上总闸,又逐个推上分路。头顶的灯管闪烁几下,亮了一片。 舞台两侧的壁灯也醒了,投下昏黄的光晕。光线亮了些,灰尘更明显了,在光柱里慢悠悠地跳舞。舞台显得更旧了,木地板有深深的划痕,幕布边缘磨损得起了毛边。 她绕着观众席走。手指划过座椅靠背,留下一条清晰的痕迹。这么多座位,以前坐满过吗? 她想象不出来。奶奶守着的,到底是什么?墨瞳又出现了。它蹲在舞台最前面,看着她来回走。像个监工。“看什么看?”林溪对它说,“没见过大活人给自己找麻烦? ”猫甩了一下尾巴。后台更乱。杂物堆得到处都是。褪色的戏服,歪斜的布景片,缺角的道具瓷器。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霉味。最里面有个小房间,门虚掩着。 是奶奶平时住的地方。一张窄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简单得过分。 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桌子上有个搪瓷杯,里面插着几支干枯的野花。林溪在床边坐下,床板嘎吱响。她感到一种沉重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外面静得可怕。 和排练厅那种充满期待的安静不同,这是一种彻底的、被遗忘的静。她躺下去,拉过被子蒙住头。被子有奶奶常用的皂角味,很淡。她想着明天要去见的殡仪馆的人,要联系的老家亲戚,要处理的种种手续。想着想着,意识就模糊了。不知道睡了多久。 她猛地惊醒。周围一片漆黑。停电了?还是天根本没亮?她屏住呼吸。 听见一种极其细微的、布料摩擦的声音。像是有人拖着脚步在走。还有……叹息?很轻,很远,像是从舞台那边飘过来的。是风吧。老房子总有怪声音。她摸出手机,按亮屏幕。 凌晨三点。屏幕光在绝对的黑暗里刺得眼睛疼。她借着光找到门口,摸到电箱。闸刀没跳。 估计是片区停电。声音好像没了。她摸黑回到小房间,重新躺下。睡不着了。 瞪着眼睛看天花板,虽然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又有声音。不是叹息。是……哼唱? 断断续续的,几个音符,不成调。像个忘记后面怎么唱的人。林溪坐起来,竖起耳朵。 声音又没了。她光脚走出去,摸到观众席。黑暗中,舞台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她隐约看见两点绿光。在舞台中央。“墨瞳?”她低声叫。绿光动了一下。呼噜声响起。 猫还在那儿。那刚才是什么?墨瞳的呼噜声在寂静里显得特别响。它慢悠悠地走过来,跳下舞台,蹭她的腿。然后朝着通往后面小花园的那扇门走去。它用爪子挠了一下门。 林溪跟过去,拉开门闩。凌晨冰冷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潮湿气味。 小花园黑黢黢的,树影摇晃。墨瞳溜了出去,蹲在一棵老槐树下,开始认真地舔爪子。 林溪靠在门框上,看着外面。城市的光污染让夜空发红,看不到几颗星星。 她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剧院。观众席的座椅轮廓在微弱的光线下,像一排排沉默的听众。 刚才那些声音,是错觉吗?墨瞳舔完爪子,开始洗脸。一副“天下太平,别无他事”的安稳样子。林溪关上门,重新插好门闩。“怪地方。”她对猫说。墨瞳站起来,尾巴尖勾了勾,领路往回走。这次,它跳上了舞台,回头看她。 那对绿眼睛在黑暗里亮得惊人。林溪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爬上舞台。木地板冰着她的脚心。 墨瞳走到舞台正中心,趴下,不动了。仿佛这里才是它该待的地方。林溪站在它旁边,环视这个被黑暗笼罩的空间。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打扰了某种永恒的宁静。 “好吧,”她低声说,不知道在对谁说,“我先待几天。办完事就走。”黑暗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像是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落进了尘埃里。 3.猫瞳中的灵魂低语天亮了。电也来了。林溪在后台水槽用冷水扑了把脸,水冰凉刺骨。 她看着镜子里挂着眼袋的自己。“挺好,”她对镜子说,“像个合格的奔丧人士。 ”墨瞳蹲在窗台上,舔着毛,对她这副德行毫不关心。今天事儿多。她得去殡仪馆,见律师,处理一堆文件。出门前,她开了罐昨天买的鱼罐头,倒在个小碟子里,放在地上。“看家。 ”她对猫说。墨瞳跳下来,闻了闻罐头,开始慢条斯理地吃。尾巴尖轻轻晃动。忙了一整天。 签字,听人说话,点头。奶奶的后事办得简单,没多少亲戚来。结束时已是傍晚。 林溪拖着步子往回走,手里拎着份快餐。推开剧院门。里面和她早上离开时一样静。 小碟子空了,洗干净了,放在桌角。墨瞳不见踪影。她放下快餐,喊了一声:“墨瞳? ”没回应。她走到观众席。然后她看见了。猫蹲在第三排最左边的座位上。 那不是奶奶常坐的位置。它坐得笔直,头微微歪着,盯着它旁边的空座位。绿眼睛一眨不眨。 仿佛那空位上坐着人,它正听得入神。林溪停下脚步,没打扰它。过了一会儿,墨瞳的耳朵轻微地转动了一下。它低下头,用脑袋蹭了蹭那空座位的扶手。 喉咙里发出轻柔的呼噜声。像是在安慰谁。然后它跳下座位,轻盈地走向下一排,重复同样的动作:凝视空座,歪头,偶尔蹭一下,发出呼噜声。它不是在玩。它在巡逻。 或者说,在问候。林溪后背有点发凉。她想起昨晚那些细微的声响。“嘿。”她出声。 墨瞳停下来,回头看她。眼神平静,仿佛她的打扰才是不正常的。“你跟谁说话呢? ”林溪问。声音在空剧场里显得有点傻。猫当然没回答。它转身跳上舞台,走到堆在角落的一堆旧布景片后面。那里光线很暗。林溪跟过去。布景片画的是一片森林,颜料剥落,树干扭曲。墨瞳用爪子扒拉着布景片后面一个旧木箱。箱子没锁。林溪蹲下,打开它。里面不是道具。是相册。厚厚几大本。还有散落的黑白照片,用皮筋捆着的信件,几张老唱片。最上面是张照片。一对年轻男女站在舞台中央,穿着戏服,笑容明亮。 男人有点紧张,女人靠着他,眼神灵动。是爷爷奶奶。背景就是这个剧院,但更新,更亮堂。 林溪拿起照片看着。奶奶从没给她看过这些。墨瞳用脑袋顶了顶她的手。 然后它走到舞台前方,看着下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它叫了一声。短促,清晰。 不像平时的叫声。林溪走过去,站在它旁边。“怎么了?”猫看看她,又看向观众席。 它的目光缓缓移动,从左到右,像是在追踪什么移动的东西。但那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夕阳透过高高的窗户,投下几道长长的光柱,光柱里尘埃飞舞。林溪顺着它的目光看。 空座位。灰尘。寂静。但她忽然觉得,这片寂静,好像没那么空了。她想起奶奶说过,剧院是有记忆的。每一场戏,每一次掌声,每一滴眼泪,都会渗进木头里,留在空气中。 她当时觉得奶奶老了,爱说玄乎话。现在,看着身边这只行为诡异的猫,看着它注视虚空的样子,一个荒谬的念头冒出来。那些“记忆”,难道还没离开? 墨瞳结束了它的“巡视”,跳下舞台,走向后台。尾巴高高翘着。林溪没动。 她还站在舞台边缘,看着下面。“喂。”她小声对着空气说,“有人……在吗?”没人回答。 但有一瞬间,她好像闻到了一丝极淡的、旧式发油的香味。转瞬即逝。可能是错觉。她低头,看见脚边地板上有一小块深色的印记,像是水渍干了。她用手指蹭了一下。不是水。 是印进去的什么。形状有点像个模糊的侧脸。她站起来,快步走回后台。 墨瞳正蹲在她的快餐袋旁边,用爪子扒拉。“别动。”林溪把它拨开,拿出饭盒。手有点抖。 她掰开一次性筷子,看着猫。“这地方不对劲,对不对?”墨瞳盯着她筷子上的红烧肉。 “你不是普通的猫。”林溪说,把一块肉挑给它,“你是……接线员?管理员?”猫叼走肉,几下吞了。然后它舔舔嘴巴,跳上衣柜顶,趴下,闭上眼睛。拒绝再交流。林溪扒拉着饭,味同嚼蜡。她得赶紧处理掉这剧院。越快越好。这地方旧得都产生幻觉了。或者,招东西了。 吃完收拾好,她拿出笔记本电脑,想查查房产处理的手续。网络信号时断时续。 她烦躁地拍了几下电脑。一抬头,墨瞳又醒了。它蹲在衣柜顶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那个荒芜的小花园,更远处,能看到几栋新建高楼的反光玻璃幕墙。猫的背部弓起,喉咙里发出一种极低的、威胁般的呜噜声。绿眼睛盯着远处那些现代化建筑,瞳孔缩成一条窄线。那表情不是警惕,是厌恶。林溪看着它。又看看窗外那些逼近的楼。 她忽然明白了。奶奶守着的,墨瞳守着的,可能不只是这座破剧院。还有别的。 一些她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东西。一些被遗忘的、却依然固执存在的东西。她合上电脑。 “行吧,”她对着猫的背影说,“我再看看。”4.自然的悲鸣与城市的推土机第二天早上,林溪是被一种低沉的轰鸣吵醒的。不是雷声。是某种机械,持续地、固执地响着,像一头野兽在远处咆哮。她爬起来,推开剧院的后门。小花园里,墨瞳已经在了。 它蹲在那棵老槐树的虬结树根上,背毛微耸,盯着铁艺围栏的外面。围栏外,隔着一片荒废的空地,几台黄色的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作业。巨大的金属铲斗起落,啃噬着土地。一栋老旧的低矮楼房在尘土飞扬中坍塌了一半。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味和尘土味。 林溪皱起眉。这动静也太近了。她记得这片区域确实在搞拆迁,但没想到已经推到眼皮底下了。她回屋拿了手机,想看看具体规划。信号依然烂得可以,网页加载半天。终于,一张模糊的区域规划图弹出来。她用手指放大,心脏沉了一下。 红色标记的拆迁范围线,像一条贪婪的舌头,不偏不倚,正好舔过了“自然之声”剧院和她所在的这片小花园。也就是说,她和奶奶的猫,还有这一剧院说不清道不明的“记忆”,全都坐在了推土机的必经之路上。“操。 ”她低声骂了一句。墨瞳从花园溜达回来,蹭过她的腿,喉咙里发出不满的呼噜声,像是在附和她的脏话。它走到舞台口,对着空观众席叫了一声,声音比平时尖利。就在这时,林溪又听到了那种声音。不是机械的轰鸣。是另一种……低语。很多个声音混杂在一起,很轻,很模糊。听不清内容,但能感觉到一种焦躁不安。像风吹过破窗棂的呜咽,又像很多人同时在远处小声议论。声音来自舞台,来自观众席,来自她头顶的灯架。 无处不在。墨瞳的耳朵转动着,绿眼睛警惕地扫视剧场,仿佛在追踪那些看不见的声源。 它不再慵懒,显得有些焦躁。林溪后背窜起一股寒意。这次不是错觉。 那些“东西”也感觉到了。外面的威胁。它们也在不安。她强迫自己冷静。也许是结构振动? 或者风声?老房子对噪音敏感很正常。她走到舞台侧面,想检查一下建筑结构。 手指无意间碰到一块墙面。她猛地缩回手。墙是温的。不是阳光晒的那种暖。 是一种……奇怪的、微微发热的温。仿佛墙壁内部有东西在躁动。她把手掌重新贴上去。 那温度又似乎消失了。只剩冰冷粗糙的涂料表面。墨瞳跳上音响箱,对着一个老旧的、布满灰尘的喇叭单元,发出低沉的哈气声。喇叭当然静默无声。 林溪看着猫的异常举动,又看看窗外那些轰鸣的钢铁巨兽。 一个荒谬却越来越清晰的念头在她脑子里成型:这座剧院,以及困在里面的 whatever-they-are,正在发出抗议。 一种无声的、却被一只猫清晰接收到的悲鸣。自然之声。奶奶给剧院取的名字。 现在听起来像个黑色幽默。自然的悲声,敌不过推土机的轰鸣。她拿出手机,找到规划局公示的联系电话。拨过去。忙音。她又试着打给拆迁办。电话通了,一个不耐烦的男声问她什么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中山路127号,‘自然之声’剧院的拆迁事宜……”“那片区整体规划,商业开发。所有建筑一律平整。 ”对方打断她,语速很快,“补偿标准按面积算,公告都贴了,自己去看。 没问题就尽快签协议搬走,别耽误工程进度。”“可是这剧院有历史价值……”“价值? ”那边嗤笑一声,“值多少钱评估报告说了算。破房子不值钱。赶紧签了拿钱走人,就这样。 ”电话被挂断。林溪握着手机,指节发白。墨瞳不知何时安静下来。它不再对着空气哈气,而是走到她脚边,用身体紧紧靠着她的小腿。一种无声的依靠。那些细微的低语声也消失了。 剧院重归寂静,只有窗外持续的轰鸣作为背景音。它们好像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林溪低头看着脚边的黑猫。它仰着头,绿眼睛深邃得像古井。“他们说要拆了这里。 ”她对猫说,声音干涩,“把我们全都‘平整’掉。”墨瞳的尾巴轻轻扫过她的脚踝。 她走到观众席第一排,奶奶常坐的位置,坐下。工具包还放在脚边,里面是她的螺丝刀、钳子、胶带。她能修好松动的灯,接好断掉的线,却修不好眼前这一切。 推土机的咆哮声更响了。仿佛又近了一些。她闭上眼睛。黑暗中,那些模糊的低语似乎又出现了。这一次,不再是焦躁不安。 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悲伤的叹息。无可奈何的叹息。墨瞳跳上她旁边的座位,学她的样子,蜷缩起来,看着空荡的舞台。一人一猫,并排坐着,听着墙外时代的推土机,步步紧逼。 5.最后的演出计划推土机的轰鸣成了新的背景音。它响一整天,只有在深夜才短暂停歇。 像一种倒计时。林溪睡不着。她坐在工具箱上,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发愣。 房产处理的网页打开着,表格空了一半。她填不下去。墨瞳不像以前那样到处巡视了。 它大部分时间窝在衣柜顶上,或者蜷在林溪的椅子旁边。 只有推土机声音特别响、震得窗户发颤时,它才会抬起头,耳朵压平,发出不满的低吼。 第三天下午,声音停了。不是暂时的停顿,是那种彻底熄火后的寂静。太静了。 反而让人心慌。林溪走到窗边。看到工地那边围了几个人,指着剧院的方向在说什么。 一个戴安全帽的人拿着图纸比划。她心里咯噔一下。轮到这边了?墨瞳跳上窗台,和她一起看。它的尾巴焦躁地甩动着。晚上,那种“低语”又出现了。比之前更清晰些。 不再是碎片式的叹息。她好像能捕捉到一两个模糊的词。 “…光…”、“…上场…”、“…错了…”。是焦虑的、催促的片段。 舞台侧翼一个废弃的老式调光台,几个旋钮自己轻轻转动了一下,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上面的指示灯诡异地闪烁了几下,又灭了。林溪盯着那调光台,汗毛立起。 墨瞳却像是收到了信号。它跳下窗台,走到舞台中央,坐下。它仰起头,对着头顶上方一条空悬的灯杆,长长地、清晰地叫了一声。“喵嗷——”不像猫叫,更像一个开幕的指令。刹那间,剧院里那种被压抑的“存在感”达到了顶峰。 林溪几乎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舞台上,聚焦在墨瞳身上。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墨瞳回过头,看着观众席里的林溪。绿眼睛里没有任何戏谑,是一种平静的等待。 林溪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啪地断了。“好吧。”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好吧!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鬼话!但你们不想走,对不对?”空气微微振动。 “我也不想就这么让它没了。”她指了指四周,又指指窗外,“虽然这地方又破又怪,还有只神经病猫。”墨瞳的尾巴尖扫了一下地板。“但他们要拆了这里。用那些铁家伙。 ”她提高声音,像是说给那些看不见的听众,“我们搞不过推土机。懂吗?搞不过。”寂静。 只有她的呼吸声。她深吸一口气,说出那个盘旋了一整天的疯狂念头。 “走之前……搞点动静吧。最后一场。不是给他们看。”她顿了顿,“是给我们自己。 行不行?”她说完,觉得自己疯了。在跟空气商量。但就在那一刻, |
精选图文
 聂安澜岳崖儿的小说(聂安澜岳崖儿)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聂安澜岳崖儿的小说)聂安澜岳崖儿的小说(聂安澜岳崖儿)
聂安澜岳崖儿的小说(聂安澜岳崖儿)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聂安澜岳崖儿的小说)聂安澜岳崖儿的小说(聂安澜岳崖儿) 虞笙霍嵩尧的小说完整版(虞笙霍嵩尧)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虞笙霍嵩尧的小说最新章节(虞笙霍嵩尧)
虞笙霍嵩尧的小说完整版(虞笙霍嵩尧)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虞笙霍嵩尧的小说最新章节(虞笙霍嵩尧) 岳崖儿聂安澜(岳崖儿聂安澜)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岳崖儿聂安澜最新章节列表(岳崖儿聂安澜)
岳崖儿聂安澜(岳崖儿聂安澜)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岳崖儿聂安澜最新章节列表(岳崖儿聂安澜) 牧渊郁声声(郁声声牧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牧渊郁声声最新小说(郁声声牧渊)
牧渊郁声声(郁声声牧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牧渊郁声声最新小说(郁声声牧渊) 霍祁年虞莺(虞莺霍祁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霍祁年虞莺最新章节列表(虞莺霍祁年)
霍祁年虞莺(虞莺霍祁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霍祁年虞莺最新章节列表(虞莺霍祁年) 震世天王叶峰(震世天王叶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震世天王叶峰在线阅读(震世天王叶峰)
震世天王叶峰(震世天王叶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震世天王叶峰在线阅读(震世天王叶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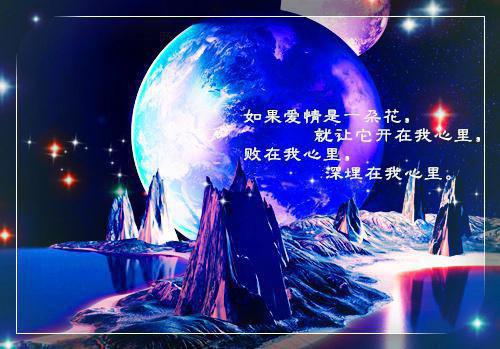 岑菡霍昀全文(岑菡霍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岑菡霍昀)岑菡霍昀全文最新章节列表(岑菡霍昀全文)
岑菡霍昀全文(岑菡霍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岑菡霍昀)岑菡霍昀全文最新章节列表(岑菡霍昀全文) 岳崖儿聂安澜(岳崖儿聂安澜)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岳崖儿聂安澜章节列表
岳崖儿聂安澜(岳崖儿聂安澜)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岳崖儿聂安澜章节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