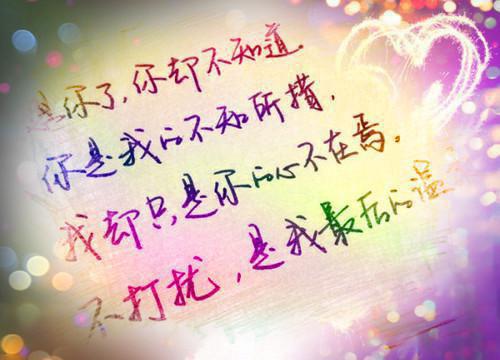妹妹身患绝症,我cos芙蓉圆直播跳舞赚钱乔碧萝芙蓉圆最新全本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妹妹身患绝症,我cos芙蓉圆直播跳舞赚钱(乔碧萝芙蓉圆)
|
八十年代末,浪潮奔涌。一座被时代镀上铁锈色光辉的国营大厂,迎来了一位信奉数据与铁腕的新厂长,和一条价值千万、从西德进口的精密生产线。裴声,是厂里最后一位配得上“匠人”二字的老钳工。他的手,能感知千分之一毫米的误差;他的世界,由机油的芬芳、金属的轰鸣和绝对的精准构成。 梁宗盛,是那位意气风发的新厂长。他的眼,只看得到报表上的赤字与利润;他的世界,由规章、效率和不容置喙的权威组成。故事,始于一张十块钱的罚单。为了一滴溅落的机油,为了一道被新规定义为“违章”的旧日习惯,匠人的尊严被这微不足道的金额彻底碾碎。 这不是一个关于金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扳手与王冠的对决。当一个时代视若珍宝的匠心,被另一个时代弃如敝履的规则所羞辱,沉默的齿轮,开始酝酿一场吞噬一切的风暴。 裴声决定用他毕生所学,为那条冰冷的生产线,也为自己被折断的傲骨,举行一场最盛大、最精确、也最悲壮的葬礼。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也是两个时代的挽歌。 在轰然倒塌的钢铁巨兽之下,埋葬的,究竟是谁的功勋,谁的罪过,谁的黄金时代?
1机修车间里,空气永远是温热的,混杂着金属切削液特有的甜腥气和老旧风扇徒劳的嗡鸣。 裴声的白布手套已经看不出本色,浸满了油污,却依旧稳定。他手中的千分尺没有一丝颤动,目光专注,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与手中这枚小小的轴承。“0.02毫米。”他轻声自语,声音被巨大的车床声响吞没。公差之内,完美。他满意地放下轴承,摘下手套,露出那双布满老茧、指节粗壮,却异常灵巧的手。这是他的王国,每一台机器的脾性,每一个零件的宿命,他都了如指掌。“裴师傅,歇会儿吧。 ”年轻的徒弟赵小川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泡得浓黑的酽茶。裴声接过,没有喝,只是用手握着感受那份温度。他望向车间另一头,那里被一道崭新的玻璃墙隔开,里面是一片洁净得刺眼的光明。巨大的、通体银灰的机械巨兽安静地匍ک着,那是厂里花了血本从西德进口的全自动生产线。它有自己的恒温恒湿空调,有专门穿防尘服的年轻技术员,与裴声所在的这个油腻、嘈杂的老车间,宛如两个纪元。 “那就是个娇小姐。”裴声的语气里听不出是羡慕还是不屑,“离了那些伺候它的大学生,屁都不是。”赵小川嘿嘿一笑,不敢接话。他知道自己师父的脾气,也知道全厂只有师父敢这么说。脚步声由远及近,清脆、坚定,与车间的混乱鼓点格格不入。 新上任的厂长梁宗盛,带着几个干部,出现在车间门口。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工装,干净得能照出人影,脚下的皮鞋一尘不染。他的目光锐利,扫过车间的每一个角落,眉头越皱越紧。“脏、乱、差!毫无纪律性!”梁宗盛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这还是国营大厂的车间吗?简直就是个废品回收站! ”工人们的动作慢了下来,车床的噪音似乎也减弱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股寒意。 梁宗盛的目光最后定格在裴声的工位上。准确地说,是定格在裴声脚边地面上的一小滩油渍上。那是在给一台老旧镗床更换液压油时,不小心滴落的几滴。在满是油污的地面上,它本不显眼。“你,叫什么名字? ”梁宗盛指着裴声。“裴声。”裴声站直了身体,平静地回答。“地上的油,是你弄的? ”“是。”“按照新颁布的《车间环境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作业期间造成环境污染,罚款十块,记过一次,全厂通报。”梁宗盛的声音冰冷,像是在宣读一份判决书。 他身边一个干部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记录。整个车间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十块钱。 在八十年代末,对于一个普通工人,这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钱。 但对于裴声这样的八级钳工、厂里的技术支柱,这无关金钱,关乎颜面。全厂的人都知道,裴声的手艺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几十年来,别说罚款,连一句重话都没人对他说过。 赵小川的脸涨得通红,想替师父说几句,却被裴声一个眼神制止了。裴声看着梁宗盛,一字一句地开口:“梁厂长,这台老镗床漏油,密封圈老化了,我打了报告,申请更换的报告还在你办公桌上压着。”“我问的是地上的油,不是机器里的油。 ”梁宗盛毫不退让,“报告我会批,规矩也要守。难道机器旧,就可以成为我们管理落后的理由吗?今天罚你这十块钱,就是要给全厂立个标杆! 从我梁宗盛到任的这一天起,这座工厂,必须姓‘规矩’!”他说完,不再看裴声一眼,转身带着人,走向那片被玻璃墙隔开的光明地带。裴声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能感觉到全车间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惊愕,也有些许的幸灾乐祸。他一生骄傲,从未受过如此羞辱。这不是一次批评,这是一场示威。 新来的厂长,拿他这块最硬的骨头,来祭自己的新旗。那张薄薄的罚单很快被送了过来。 裴声接过,看着上面用钢笔写下的“十元”字样,以及那个龙飞凤舞的签名“梁宗盛”。 他忽然笑了,笑得有些渗人。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十块钱,递给那个来送罚单的小干部。然后,他弯下腰,用那张罚单,仔仔细细地,将地上的那滩油渍擦得干干净净。他擦得很慢,很用力,仿佛要将那纸片揉进水泥地里。 做完这一切,他把那张浸透了油污的罚单,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了自己上衣最里层的口袋,紧贴着胸口。那晚,裴声没有回家。他在车间里待了一整夜。 他把自己所有的工具——那些德国进口的、擦得锃亮的扳手、卡尺、锉刀,一件件拿出来,摆放整齐,用绒布反复擦拭,对着灯光,审视着它们完美的刃口和冰冷的寒光。 它们是他一生的荣耀,是他尊严的延伸。而今天,有人告诉他,这份荣耀,这份尊严,连同他四十年的心血,只值十块钱。2第二天,裴声没有出现在车间。 这是四十年来的头一遭。赵小川心急如焚,跑到裴声的宿舍,敲了半天门也无人应答。 厂里关于昨天那件事的议论已经传遍了每个角落。有人说裴师傅这是撂挑子了,有人说新厂长杀鸡儆猴,做得太过火。梁宗盛对此置若罔闻。他在全厂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并将对裴声的处罚作为正面典型,要求各车间引以为戒。他宣布,为了迎接那条千万生产线的正式投产,全厂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纪律整风运动”。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梁宗盛激昂的声音在回荡。会计科的喻秋白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纸上画着圈。她认识裴声,那是一位沉默寡言但内心温和的长者。 她父亲还在世时,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她无法想象,那样一个把工厂当家的老人,会因为一滴油而被如此对待。而裴声,此刻正坐在城市的另一头,一家尘土飞扬的小酒馆里。 桌上只有一碟花生米,一瓶劣质白酒。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眼神空洞,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酒馆里人声嘈杂,说着家长里短,说着物价飞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沉默的老人。他想起了二十年前,自己带着一群徒弟,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关,在车间里连着睡了一个月。那时候的厂长,亲自给他们端来肉包子,拍着他的肩膀说:“裴声,你就是咱们厂的定海神神针!”他又想起十年前,他亲手改造的一台设备,为厂里节约了上百万的成本。奖状和奖金送来时,他只留下了那张红纸,把钱都分给了车间的兄弟们。他说,手艺人的脸面,比钱金贵。 那些日子,都去哪儿了?铁锈的气味,曾是他最熟悉的故乡的味道。而现在,他嗅到的,只有冰冷的、被遗弃的尘埃气息。旧人,似乎注定要被新的时代所淹没,连哭声都不会被听见。他喝光了最后一滴酒,站起身,步履有些踉跄,但眼神却恢复了清明。 他没有回家,而是朝着反方向走去。那里是市图书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裴声都没有去上班。他办了“长期病假”,每天准时出现在图书馆的外文科技阅览室。 他曾经跟随苏联专家学过一年俄语,后来为了钻研技术,又自学了德语。虽然口语不行,但阅读那些技术资料,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他找出了所有关于西德“克虏伯K3000”型精密冲压生产线的资料。 那是梁宗盛引以为傲的那条生产线的同系列产品。厚厚的德文原版手册,在他手中一页页翻过。他看得极其仔细,不仅看操作流程,更看内部结构图、液压系统图、电路控制图……图书馆管理员注意到这个奇怪的老人。 他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不看报纸,不看小说,只抱着那些天书般的德文图纸,一坐就是一天。他的手指在图纸上缓缓移动,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他的眼神,专注而炽热,仿佛一个饥饿的人看见了面包。喻秋白是在第三天找到他的。 她拿着家里熬的鸡汤,找到了图书馆。看到裴声那一瞬间,她鼻子一酸。老人瘦了,眼窝深陷,下巴上长出了灰白的胡茬。“裴伯伯。”她轻声喊道。裴声抬起头,看到是她,眼中闪过一丝暖意。“秋白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您。 ”喻秋白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您别跟梁厂长置气了,他那个人就那样,对事不对人。 我替他给您道个歉,您消消气,回厂里吧,大家都想您呢。”裴声摇了摇头,指着面前的图纸,说:“秋白,你看这个。”喻秋白凑过去,完全看不懂那些复杂的线条和德文标注。“这是艺术品。”裴声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颤音,“每一个齿轮的啮合,每一个阀门的开启,都计算得分毫不差。设计它的人,是个天才。 这是工业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王冠。”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赞叹,甚至是一种虔诚。 喻秋白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他不懂。”裴声忽然说,声音低沉下去,“梁宗盛,他不懂。他只知道这东西值一千万,能带来多少利润。 他把它当成一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他不知道,这东西有生命,有灵魂。你不尊重它,它就会毁了你。”“裴伯伯,您这是什么意思?”喻秋白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裴声没有回答,他合上手册,目光投向窗外。图书馆外,一棵老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 秋天要来了。“回去吧,秋白。”他说,“告诉他们,我的‘病’,还要再养一阵子。 ”喻秋白带着满心的疑虑和担忧离开了。她回头看了一眼,老人又重新埋首于那些图纸之中,身影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孤独而又执拗。她不知道,那不是一个老工人在学习新技术,那是一个顶级的刺客,在研究他目标的骨骼与血脉,寻找那个最致命的要害。3一个星期后,裴声销了假,回到了工厂。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不再抱怨新规矩,不再对那条新生产线冷嘲热讽。他每天准时上下班,沉默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车间里的老伙计们想跟他聊几句,他也只是点点头,不多言语。那张十块钱的罚单,似乎真的磨平了他所有的棱角。梁宗盛对此很满意。在他看来,裴声的“服软”,证明了他的铁腕管理是有效的。这只最难驯服的“老猴子”已经被镇住了,其他人更不在话下。在一次会议上,他还不点名地表扬了裴声“思想转变快,积极拥抱新变化”。只有赵小川和喻秋白觉得不对劲。赵小川发现,师父虽然话少了,但在工具台前待的时间却更长了。他常常一个人,对着一些废旧的零件发呆,手里拿着卡尺,不停地测量、记录。那些数据,他都记在一个从不离身的小本子上。喻秋白则是在下班后,几次看到裴声没有回家,而是绕到新车间外,隔着那面巨大的玻璃墙,久久地凝视着里面那条生产线。那眼神,复杂得让她心惊。有痴迷,有惋惜,还有一丝她读不懂的……冷酷。“裴师傅最近好像对新设备很感兴趣。”一次,梁宗盛在走廊上碰到喻秋白,状似随意地说道。“裴伯伯一辈子就爱跟机器打交道。 ”喻秋白谨慎地回答。“是啊,老一辈工人,有热情,有干劲,就是思想跟不上时代了。 ”梁宗盛背着手,用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不过没关系,事实会教育他们。你看,那条生产线,一条线顶你们一个老车间。这就是科学,这就是效率。个人的经验主义,在它面前,不值一提。”喻秋白低下头,没有接话。她觉得梁宗盛的话,像一把精密的尺子,能衡量出所有东西的价值,却唯独量不出人心。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条德国生产线在试运行期间,出了一个小故障。一个传送带上的气动抓手,在抓取钢板时,总是出现微小的偏差。虽然不影响生产,但产品的美观度却打了折扣。 几个年轻的大学生技术员,围着机器研究了两天,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给德国方面发了电报,也没找到症结所在。梁宗盛的脸色很难看。 这条生产线是他力排众议引进的,是他最重要的政绩。现在刚开始就掉链子,让他脸上无光。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裴声默默地走进了这个他从未踏足过的新车间。他没有穿防尘服,一身油腻的工装,与这里的洁净环境格格不入。“你来干什么? ”一个年轻技术员皱眉拦住他。裴声没有理他,径直走到那台巨大的机器前。他没有看图纸,也没有碰任何操作面板,只是侧耳倾听着机器运行的声音。他闭上眼睛,像一个老中医在为病人诊脉。“气压不稳。”几分钟后,他睁开眼,断言道,“主气泵的稳压阀,有杂音。不是机器的问题,是你们的气源有问题。”“不可能! ”为首的技术员立刻反驳,“我们的气源系统是全新的,所有指标都符合德国方面的要求。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裴声淡淡地说,“你们厂房地基沉降不均,导致气管在某个连接处有极其微小的扭曲,造成了压力波动。这个波动太小,压力表显示不出来,但机器能感觉得到。”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地基沉降? 这种事情谁会想到?梁宗盛也闻讯赶来,听到裴声的诊断,将信将疑:“老裴,你确定? ”裴声没有回答,而是走到墙边,拿起一把扳手,在一个看似毫无异常的管道连接处,轻轻敲击了几下。然后,他用扳手,以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将一个螺母拧动了不到四分之一圈。“再试试。”他说。技术员将信将疑地重启了机器。 奇迹发生了。那个气动抓手,动作变得精准无比,每一次抓取都稳稳当当,再无偏差。 整个车间一片死寂。那些刚才还一脸傲气的大学生们,此刻看着裴声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不可思议。这已经不是技术,这是玄学。梁宗盛的表情很复杂。他走上前,拍了拍裴声的肩膀,这是他第一次做出如此亲近的举动:“老裴,好样的! 你为厂里立了大功!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发双份!”他以为这是一种奖赏,一种和解。 但他没有看到,裴声低着头,嘴角勾起了一抹无人察觉的、冰冷的笑意。从那天起,裴声被特批可以自由出入新车间。他成了这条德国生产线的“特聘顾问”。梁宗盛觉得,这是他知人善任、不计前嫌的体现。他甚至在想,或许可以让这个老家伙在新岗位上发挥余热。他不知道,他亲手递给这位“刺客”的,是一张可以随意进出目标的通行证。裴声每天都会在新车间待上几个小时。他不再只是看,他开始动手。他帮技术员们校准设备,调整参数,解决各种小毛病。 他比任何人都更爱护这台机器。他会用最柔软的棉布擦拭它的外壳,会为它的每一个运动部件涂上最合适的润滑油。他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比设计它的人更了解它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会如何“水土不服”。 他知道它最强壮的地方,也洞悉了它最脆弱的命门。那本记录着数据的小本子,内容越来越厚。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关于这条生产线的核心参数、运行极限和材料强度。 精密之尺,确实量不出人心。梁宗盛用他的尺子,量出了裴声的“利用价值”。而裴声,也在用他的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着这座千万帝国,走向毁灭的距离。4秋意渐浓,厂区里的梧桐树叶子大片大片地落下,铺了一地金黄。那条德国生产线已经正式投产一个月,运行平稳,效率惊人,产量是过去的三倍。梁宗盛在全厂的总结大会上意气风发,将这一切归功于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裴声的名字,作为“新老技术结合的典范”被提及,获得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裴声坐在台下,面无表情。他看着台上口若悬河的梁宗盛,如同在看一个即将走上断头台而不自知的囚犯。 复仇的念头,早已不是一时的冲动。它在他的脑海里,经过了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变得如同他手中打磨出的零件一样,冰冷、坚硬、且无比精确。他不是要搞一次简单的破坏,不是要出胸中一口恶气。他要做的,是一场完美的、无法挽回的、艺术品级别的“谋杀”。 他要杀死的,是这条千万生产线的“灵魂”。他已经找到了那个“灵魂”所在。 不是最复杂的中央处理器,也不是最庞大的液压总泵。 那是整条生产线的心脏——一台由特殊合金锻造的主驱动齿轮箱。 它负责将主动力精准地分配给每一个工位,所有的节拍、速度、力量,都源于它的完美运转。 这个齿轮箱,是德国工程师的骄傲。它被设计成一个几乎无法被摧毁的整体。 外壳用的是特种钢,内部的齿轮啮合精度达到了微米级,并且在恒定的油浴中工作,理论上可以使用五十年而无需大修。手册上用加粗的字体写着:严禁任何非授权的拆解,任何试图打开它的行为,都将导致不可逆的结构性损伤。这,就是裴声的目标。 他开始为这场“谋杀”做准备。这需要耐心,和绝对的隐秘。他利用自己“顾问”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向设备科申请了一批材料。其中包括一些高强度的研磨砂,几瓶化学性质极其稳定的溶剂,还有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电子元件。 设备科的人看他是为新生产线办事,又是梁厂长面前的红人,一路绿灯,无人过问。 他白天依旧在老车间工作,帮新车间解决一些小问题,表现得一如既往地沉默而可靠。 但到了晚上,他宿舍的灯,总会亮到深夜。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实验。 他将那些研磨砂,用不同的溶剂调和,测试它们的悬浮性和附着力。 他需要一种特殊的混合物,它必须能够长时间悬浮在机油中而不沉淀,并且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才会释放出它那致命的磨损能力。这像是在调制一种慢性毒药。 他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齿轮的转速、扭矩、工作温度,以及那种特殊合金的硬度和脆性。 他需要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破坏不能太快,否则会立刻被发现;也不能太慢,否则等不到他想要的结果。他要让这条生产线,在最辉煌、最万众瞩目的时刻,在所有人——尤其是梁宗盛的面前,轰然崩塌。它要在以最高效率运转时,自己把自己碾碎。 齿轮箱里那些精密齿轮的低语,在他耳中,不再是工业的颂歌,而是复仇的、越来越响亮的前奏曲。喻秋白来看过他几次,送来一些自己做的饭菜。 她总觉得裴声的状态很奇怪,他瘦得更快了,但精神却异常亢奋,眼睛里常常布满血丝,闪烁着一种灼人的光。“裴伯伯,您要注意身体。”她担忧地说,“您是不是还在为之前的事……心里不舒服?”“没事。”裴声总是这样回答,然后迅速转移话题,问一些厂里的近况,问喻秋白的工作。 他甚至会和蔼地问起她父亲过去的一些趣事,仿佛在刻意营造一种温情的假象。但有一次,喻秋白临走时,无意中瞥见了他桌上的草稿纸。上面画着一些她看不懂的零件图,旁边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德文单词。其中一个单词,她恰好认识——“Ermüdung”,疲劳。她不懂技术,但她能感觉到,那张纸上透出的,不是一个技术顾问的研究热情,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执念。 她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赵小川。这个年轻的徒弟也同样感到不安。 “师父最近总让我帮他找一些废弃的齿轮和轴承,”赵小川压低声音说,“他还问我,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新车间的夜间巡逻。”两人的心,都沉了下去。他们隐约感觉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但他们谁也无法想象,这场风暴的中心,会是那条代表着工厂未来的生产线。他们更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那张十块钱的罚单,和一个手艺人被碾碎的尊严。5夜,深了。 整座工厂都沉睡在黑暗中,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空旷的厂区里投下寂寥的光晕。 远处的城市,传来几声零星的犬吠。裴声宿舍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只透出一条微弱的光缝。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机油混合的奇特气味。一张大桌子上,铺满了从图书馆复印来的“克虏伯K3000”的结构图纸。旁边,放着一个酒精灯,一个小烧杯,还有几瓶贴着手写标签的化学试剂。裴声没有开大灯,只在桌角点了一盏台灯。 昏暗的光线勾勒出他专注的侧脸,眼窝深陷,神情如同一个正在进行神圣仪式的炼金术士。 他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烧杯里,是深褐色的润滑油,与那台德国机器里用的一模一样。 他用滴管,小心翼翼地滴入几滴自己调配好的、如同墨汁般的悬浊液。然后,他将烧杯放在酒精灯上,缓缓加热。他需要模拟齿轮箱在高速运转时内部的温度和环境。 随着温度升高,烧杯里的液体开始变得浑浊。 那些原本均匀悬浮的、比粉尘还细微的研磨颗粒,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仿佛被激活了。 它们不再温和,而是开始显现出一种奇异的粘附性,牢牢地吸附在裴声投入烧杯的一小块金属片上。成了。裴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感觉一阵眩晕。这半个多月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的大脑一直在高速运转,推演着每一个细节。酒精、图纸、深夜的孤独,这些成了他唯一的伴侣。 他看着桌上那瓶最终成型的“毒药”。它看起来平平无奇,就像一小瓶普通的石墨润滑剂。 谁能想到,这不起眼的液体,一旦进入那台精密机器的心脏,就会化作最致命的癌细胞,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疯狂扩散,直到将那些坚硬的合金齿轮,从内部一点点啃噬、碾碎。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望向工厂的方向。黑暗中,那个安装着新生产线的巨大厂房,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他仿佛能听到它平稳的呼吸。 他就要去,亲手切断这头巨兽的喉咙。行动的时间,他选择在后天。那天,市里和省里的领导要来厂里视察,梁宗盛一定会命令生产线开足马力,全速运行,以展示其最高的生产效率。那将是“毒药”发作的最佳时机,也是这场“葬礼”最完美的舞台。他需要在那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瓶“毒药”注入齿轮箱。齿轮箱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口和注油孔,平时用螺栓密封着。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必须在夜间巡逻的间隙,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完成开封、注入、再重新密封的全过程。并且,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他已经为此演练了无数次。他用一块大小相仿的废铁块,模拟那个注油口的螺栓。 |
精选图文
 极品狂帝推荐免费新书 赵恒苏夕瑶全本阅读
极品狂帝推荐免费新书 赵恒苏夕瑶全本阅读 前夫哥,温家的火葬场请签收程茵茵(前夫哥,温家的火葬场请签收程茵茵)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前夫哥,温家的火葬场请签收程茵茵全文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大结局_
前夫哥,温家的火葬场请签收程茵茵(前夫哥,温家的火葬场请签收程茵茵)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前夫哥,温家的火葬场请签收程茵茵全文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大结局_ 周嘉栩徐璐璐全文(徐璐璐周嘉栩)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周嘉栩徐璐璐)徐璐璐周嘉栩全文最新章节列表(徐璐璐周嘉栩全文)
周嘉栩徐璐璐全文(徐璐璐周嘉栩)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周嘉栩徐璐璐)徐璐璐周嘉栩全文最新章节列表(徐璐璐周嘉栩全文) 江鹤时梁沐荞(梁沐荞江鹤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江鹤时梁沐荞)梁沐荞江鹤时最新章节列表(梁沐荞江鹤时)
江鹤时梁沐荞(梁沐荞江鹤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江鹤时梁沐荞)梁沐荞江鹤时最新章节列表(梁沐荞江鹤时) 周花楹梁骁辰全文(梁骁辰周花楹)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周花楹梁骁辰)梁骁辰周花楹全文最新章节列表(周花楹梁骁辰全文)
周花楹梁骁辰全文(梁骁辰周花楹)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周花楹梁骁辰)梁骁辰周花楹全文最新章节列表(周花楹梁骁辰全文) 颜涵影赵尧黎(颜涵影赵尧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颜涵影赵尧黎小说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列表(颜涵影赵尧黎)
颜涵影赵尧黎(颜涵影赵尧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颜涵影赵尧黎小说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列表(颜涵影赵尧黎) 墨渊佟小卿(佟小卿墨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墨渊佟小卿免费阅读)佟小卿墨渊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佟小卿墨渊)
墨渊佟小卿(佟小卿墨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墨渊佟小卿免费阅读)佟小卿墨渊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佟小卿墨渊) 洛筠顾锦旬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顾锦旬洛筠)全文免费洛筠顾锦旬读无弹窗大结局_ 顾锦旬洛筠免费洛筠顾锦旬最新章节列表(洛筠顾锦旬小说)
洛筠顾锦旬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顾锦旬洛筠)全文免费洛筠顾锦旬读无弹窗大结局_ 顾锦旬洛筠免费洛筠顾锦旬最新章节列表(洛筠顾锦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