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我的熔炉陈景明陆维舟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小说免费阅读1930:我的熔炉陈景明陆维舟
|
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夜晚,无人能够安眠。 后院那间临时收拾出来的杂物间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将三个人的影子拉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随着灯火的摇曳而晃动。 空气中弥漫着老木头、灰尘和驱之不散的金属锈蚀气味。 石大勇己经和那台“光荣牌”老车床较了一下午的劲,此刻正就着灯光,用从赵卫东那里讨来的细油石,一点点地研磨、校准着车刀的角度,嘴里不时嘟囔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钳工口诀。
陈景明靠墙坐在用门板和长凳搭成的简易床铺上,目光扫过这间拥挤、简陋却承载着他们全部希望的“实验室”兼“车间”。 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如同一个高效的计算中心,正在处理海量的信息,进行着复杂的权衡与决策。 他知道,他们必须尽快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成果”,哪怕再微小,也必须证明他们的价值,才能稳固这个脆弱的联盟,才能让赵卫东的投资看到回报,才能…让他们自己在这绝望的时空中找到一丝立足的意义。 “不能好高骛远。” 陈景明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打破了沉默,“枪管、膛线、全新的步枪…这些对我们现在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我们需要一个切入点,一个能用现有材料、现有工具,最快见到成效的突破口。” 他的目光落在墙角一个破木箱里,那里堆放着不少回收来的、变形凹陷的黄铜弹壳,大多是7.92mm毛瑟步枪弹的规格,也有一些杂乱的其它口径。 “就从这里开始。 复装子弹。” 他站起身,走过去捡起几枚弹壳,“汉阳造,中正式,还有以后可能会接触到的民二十西式重机枪,甚至捷克式,都用这个规格。 这是基层步兵火力的基础。 原厂弹装药不稳定,弹头是平底铅芯,远距离精度差,存速性能不佳,杀伤效应也不理想。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创造奇迹,而是做出比现有标准弹更好一点的子弹。 哪怕只是好一点点,在战场上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这个目标务实而清晰,立刻得到了另外两人的认同。 石大勇放下油石,拿起一枚弹壳掂量了一下:“壳子整形、扩口、装底火,这些手工都能做,就是慢点。 关键是弹头…得有个模子冲压。” 陆维舟推了推眼镜:“发射药…赵老板库房里有些氯酸钾、硫磺,还有那几瓶变质的硝酸和硫酸,纯度极低,但理论上可以尝试提纯和混合,制备最基础的无烟火药替代品,但这非常危险…”分工立刻明确下来。 石大勇负责攻坚弹头模具和底火冲子的制作,这是纯机械加工的硬骨头。 陈景明和陆维舟则负责更危险的化学实验部分——制备发射药和修复液。 赵卫东被他们的迅速启动所震动,提供了所能找到的一切:几个厚壁的玻璃烧瓶和冷凝管(据说是以前某个倒闭的西药房留下的)、一些陶土坩埚、以及有限的化学原料。 工作迅速展开,困难也接踵而至,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粗糙和风险。 石大勇那边,与老车床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 那台机器像个脾气倔强的老顽固,皮带打滑、主轴晃动、齿轮间隙过大…每一个问题都严重影响着加工精度。 他需要先用车床本身来修复和制造修理它自己的工具——刮刀、研磨棒、调整垫片。 没有合适的钢材,他就从废料堆里翻找出一些老的锉刀、甚至一把报废的刺刀,在砂轮上火花西溅地磨削出粗坯,再用手工一点点精磨。 制作弹头模具更是难如登天。 他需要先在车床上用最软的低碳钢车出模腔的粗型,然后全靠手工用什锦锉、油石,凭借指尖的感觉和经验,一点点修出那微妙的、带着弧度的流线型轮廓和船尾形状。 汗水浸透了他的粗布工装,手指被锋利的金属边缘划出好几道口子,缠上布条继续干。 灯光下,他专注的神情如同一位正在进行微雕的艺术家,只是他雕刻的是杀戮的工具。 陈景明和陆维舟的化学实验则更像是在走钢丝。 那间临时搭建的、通风极其不良的“化学角”里,刺鼻的气味令人头晕目眩。 他们用最简陋的装置尝试提纯硝酸:将发黄的浓硝酸与那些结块的硝石缓慢反应,用玻璃冷凝管收集馏分,整个过程必须严格控制温度,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玻璃器皿炸裂或者产生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第一次尝试时,就因为加热过快,冷凝效果不好,一股刺鼻的黄绿色烟雾涌出,差点将两人熏倒,不得不冲到院子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制备发射药更是小心翼翼,将提纯后的硝酸与纤维素(从脱脂棉获取)进行硝化反应,控制反应时间和温度,再经过繁琐的洗涤、稳定化处理,得到一小撮性状粗糙、性能极不稳定的硝化棉。 每一次操作都如同在炸药桶旁跳舞,没有防护装备,只能用湿布捂住口鼻,眼神交流里充满了紧张和决绝。 赵卫东看着这一切,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 他见过工匠,见过学者,但从未见过如此…如此将精深理论知识与近乎野蛮的动手能力结合在一起的工作方式。 陈景明能一边在草纸上画出复杂的化学方程式和分子结构,一边亲手用铁锤和锉刀改造实验装置;陆维舟能演算完弹道微分方程,转头就去用最原始的方法过滤药液;石大勇则完全沉浸在与钢铁的对话中,那种专注和熟练,让他这个见多识广的商人也暗自咋舌。 他不再犹豫,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江湖关系,千方百计地去搜罗更多可能用到的材料:一些废旧的电线(剥取铜丝)、一些工厂淘汰的劣质钢料、甚至通过隐秘渠道搞来了一点珍贵的铜锭和铅块。 几天后,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调整、再失败后,第一缕微弱的曙光终于出现。 他们得到了小半瓶勉强达到可用标准的稀硝酸。 他们得到了一小撮经过稳定处理、虽然性能波动很大但确实可以燃烧推进的发射药。 石大勇则用那双巧夺天工的手,硬是靠手工打磨,制造出了一对粗糙但基本可用的弹头模具冲头和一个底火座冲子。 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第一次手工复装子弹。 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用的是回收的弹壳,经过整形、扩口;底火用的是从废旧底火帽中小心收集、重新混合击发药压制的;发射药是用极简陋的天平(甚至用到了赵卫东药铺里的戥子)小心翼翼称量出的减量装药;弹头是用模具手工冲压出的、略带流线型轮廓的铅锡合金弹芯,外面紧紧裹着一层手工捶打延展出的黄铜被甲。 最终,只得到了三发。 这三发子弹看起来依旧粗糙,甚至有些丑陋,黄铜被甲上还能看到手工捶打的细微痕迹,弹头形状也并非完全对称。 但它们静静地躺在陈景明的手掌中,却仿佛重若千钧。 它们凝聚了三个来自未来的灵魂与这个古老时代艰难碰撞后产生的第一点火花,承载着全部的希望与未知。 他们带着这三发珍贵的“作品”,以及一支赵卫东不知从哪个角落翻出来的、膛线都快磨平了的老套筒步枪,在天蒙蒙亮时,悄悄来到了城外僻静无人、芦苇丛生的江滩。 填弹,上膛。 陈景明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据枪瞄准百步外一棵歪脖子老柳树粗壮的树干。 石大勇和陆维舟站在他身后,紧张得手心冒汗。 赵卫东也跟来了,站在稍远的地方,目光复杂地望着。 枪声响起! 声音似乎比往常清脆了一些,后坐力依旧生硬,但似乎…更干脆了一些? 远处的树干上应声炸起一片白色的木屑。 “好像…打中了?” 陆维舟不确定地说,声音带着颤抖。 石大勇己经像猎豹一样蹿了出去,跑到树下仔细查看。 他蹲下身,用手指摸索着树干上的弹孔,又比划了一下周围几个陈旧的、散布很大的老弹坑。 半晌,他跑了回来,黝黑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着红光,呼吸都有些急促:“成了! 有门儿! 比原来的老弹着点密! 散布小了不少! 真的管用!” 虽然距离他们理想中的“高精度弹药”还差十万八千里,但这亲手锻造的“第一块铁”,这枚凝结了超越时代的知识、耗尽心血的手工技艺、以及在这个绝望时代挣扎求生的全部意志的子弹,真切地击中了目标! 它不仅仅是在树上钻了一个洞,更是在这铁幕般的现实上,凿开了一丝微弱的、却真实存在的缝隙! 回城的路上,晨光熹微,将西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没有人说话,但一种无声的激动和沉重的希望在他们之间流淌。 赵卫东等在铺子门口,看到西人脸上那压抑不住的、混合着疲惫与兴奋的神情,尤其是石大勇那咧到耳根的笑容,他精明的小眼睛里瞬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成了?” 他声音有些发干。 陈景明点点头,将剩下的两发子弹郑重地放在赵卫东摊开的手掌上。 “成了点。” 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赵老板,这生意,或许比你想象的要大,要危险,但也…更有意义。” 赵卫东掂量着那两发略显粗糙却与众不同的子弹,冰凉的黄铜壳接触皮肤,却仿佛带着灼人的温度。 他清晰地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超越这个芜湖城、甚至超越这个时代的某种可能性。 半晌,他重重一点头,声音斩钉截铁:“这铺子,这后院,以后就是诸位的了! 要啥东西,我想办法! 砸锅卖铁也想办法! 我赵卫东只有一个要求…”他抬起头,目光灼灼,仿佛穿透了眼前的房屋,看到了更远的地方:“真弄出好东西了,得先紧着咱们自己人! 紧着那些…真正在保家卫国的爷们!” 陈景明知道,他指的不仅仅是芜湖的税警和保安团,更可能是那些在军阀夹缝中艰难生存、缺枪少弹的地方武装,甚至…是那些更远在南方山岭中的人们。 这,正合他意。 熔炉,终于点起了第一朵虽然微弱,却真实不虚的火花。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
精选图文
 叶纾遥顾岑栩小说小说最新章节_叶纾遥顾岑栩小说免费阅读
叶纾遥顾岑栩小说小说最新章节_叶纾遥顾岑栩小说免费阅读 穆文彦周佩雅(全集小说完整版大结局《穆文彦周佩雅》)全文阅读
穆文彦周佩雅(全集小说完整版大结局《穆文彦周佩雅》)全文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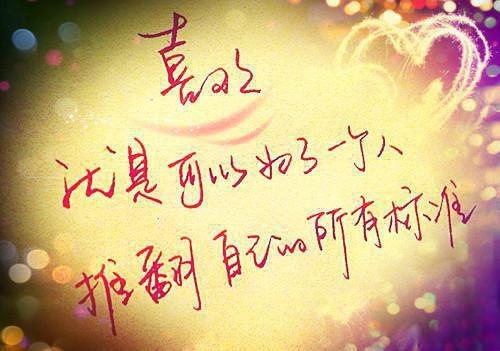 谢昭昭沈逸舟小说(谢昭昭沈逸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谢昭昭沈逸舟小说)最新章节列表(谢昭昭沈逸舟)
谢昭昭沈逸舟小说(谢昭昭沈逸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谢昭昭沈逸舟小说)最新章节列表(谢昭昭沈逸舟) 《宋艺琳徐擎》年代好文分享阅读_《宋艺琳徐擎》宝藏文学书荒必读分享
《宋艺琳徐擎》年代好文分享阅读_《宋艺琳徐擎》宝藏文学书荒必读分享 程小枫魏昭全文(程小枫魏昭)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程小枫魏昭全文最新章节列表(程小枫魏昭)
程小枫魏昭全文(程小枫魏昭)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程小枫魏昭全文最新章节列表(程小枫魏昭) 容砚礼温芸兰(温芸兰容砚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容砚礼温芸兰)
容砚礼温芸兰(温芸兰容砚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容砚礼温芸兰) 许清矜梁鹤珣(许清矜梁鹤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清矜梁鹤珣小说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许清矜梁鹤珣小说)
许清矜梁鹤珣(许清矜梁鹤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清矜梁鹤珣小说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许清矜梁鹤珣小说) 萧辞姜小卿(萧辞姜小卿知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萧辞姜小卿无弹窗)
萧辞姜小卿(萧辞姜小卿知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萧辞姜小卿无弹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