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宴被泼包养贫困生脏水!我变身跨国CEO砸垮他(顾延琛书悦)完整版免费全文阅读_最热门小说生日宴被泼包养贫困生脏水!我变身跨国CEO砸垮他顾延琛书悦
|
腊月初八的雪,埋了我儿子的最后一口气。丈夫顾晏廷站在庭院里,手里那碗救命的药,最终喂给了嫂嫂柳玉容的儿子。他说:“长房香火不能断。”三天后,我儿子下葬,他没来,只派管家送了一箱东海明珠。管家躬身:“王爷说,这是给夫人的补偿。 ”我看着那箱冰冷的珠子笑了。原来我十月怀胎、夜夜哺乳的念安,只值一箱珠玉。 后来嫂嫂抱着她的儿子登堂入室,故意打碎我母亲留给念安的唯一遗物,还柔声劝我:“妹妹,死物哪有活人重要?”丈夫冲进来时,满身酒气地踹翻了我的炭盆:“沈微你闹够了!她是你嫂嫂,念祖是顾家的根! ”我擦了擦溅在脸上的火星,第一次直视他冰冷的眼:“顾晏廷,我们合离。 ”他笑得残忍:“离了我,你沈微算个什么东西?念安是顾家的种,灵位只能入我顾家祠堂!
”他拽着我闯进祠堂,将念安的牌位钉在他亡兄的牌位下,像个卑微的陪葬。 “沈微你看清楚,”他声音淬着冰,“你儿子的命,本就是为顾家大义垫脚的! ”我看着牌位上稚拙的“念安”二字,突然笑出声。顾晏廷,你真以为,躺在这牌位里的,是你的儿子?腊月初八,雪下了整整一夜。沈微坐在东院的窗边,指尖抚过冰冷的窗棂。 窗纸上映着西院的灯火,红得像血,丝竹声混着宾客的笑闹,顺着风雪飘过来,扎得人耳膜生疼。今天是顾念祖的周岁宴,顾晏廷的嫡子,顾家名义上的长房香火。 而她的念安,已经走了整整三个月。“夫人,夜深了,该添件衣裳。 ”张嬷嬷捧着件银狐斗篷进来,声音压得低低的。她眼眶还是红的,三个月前念安断气时,这个伺候了沈家两代人的老嬷嬷,哭得比沈微还凶。沈微没动,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枯萎的腊梅上。那是念安满月时,顾晏廷亲手栽的,说东院太素净,添点活气。如今花死了,人也没了,倒衬得这满院的白,像座冰窖。“嬷嬷,你说,人的心怎么能那么硬?”她轻声问,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张嬷嬷手一顿,将斗篷搭在沈微肩上:“夫人,有些人心,从来就没热过。”这话戳到了沈微的痛处。 三年前她嫁入顾王府时,顾晏廷不是这样的。那时他是京城有名的少年将军,眉眼间带着沙场的锐气,却会在她生辰时,翻遍京城的花店,只为寻一株开得最盛的白牡丹。 他会在寒夜里守在产房外,听到念安的第一声啼哭时,红着眼圈说“微微,我们有家了”。 变故是从顾晏之死开始的。顾晏廷的兄长,顾家真正的世子,在戍边时中了埋伏,尸骨无存。 老王爷一病不起,临终前攥着顾晏廷的手,反复念叨“长房不能断了香火”。 顾晏之的遗孀柳玉容,那时刚怀了身孕。于是有了那场荒唐的“兼挑两房”。 顾晏廷以世子之礼,将柳玉容娶进了王府,理由是“代兄抚孤”。他对外说的是“手足情深,不敢忘本”,可沈微清楚,柳玉容那双看向顾晏廷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过“叔嫂”的分寸。 从此王府分成了两半。她居东院,柳玉容住西院。顾晏廷每月十五宿在东院,其余时候,要么在西院,要么在书房。沈微不是没闹过,可顾晏廷只说“微微,委屈你了,等孩子生下来,一切都会好的”。她信了。直到去年冬日,念安和刚满半岁的顾念祖同时染上了时疫。太医跪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冷的青砖:“王爷,解药只够一剂。两位小公子……只能保一个。”那天的雪也像今天这样大。 顾晏廷站在庭院中央,玄色锦袍上落满了雪,像个雪人。沈微抱着烧得滚烫的念安,看着他的背影,喉咙里像堵着滚烫的铁,喊不出一个字。她看见柳玉容跪在顾晏廷脚边,哭得梨花带雨:“王爷,念祖是长房唯一的根啊!您不能让大哥在地下也闭不上眼! ”雪落了一夜,顾晏廷沉默了一夜。天亮时,他拿着那碗黑漆漆的汤药,走向了西院。 沈微怀里的念安,小手还抓着她的衣襟,身体却一点点冷下去,最后彻底松开了。她没有哭,也没有像柳玉容那样去求,只是静静地抱着念安,直到天边泛白。念安下葬那天,顾晏廷没来。他派管家李福送来一口箱子,打开时,赤金元宝滚得满地都是,还有整整一匣子南海珠,颗颗饱满,在阴沉沉的屋里泛着冷光。“王爷说,让夫人节哀。 这些……是给夫人的补偿。”李福低着头,不敢看沈微的眼睛。沈微笑了,笑声哑得像破锣。 原来她的念安,她十月怀胎、夜夜哺乳的儿子,只值一箱金银。她看着李福:“管家觉得,这些东西,能换一条人命?”李福脸一白:“夫人,王爷也是为了大局。 长房香火……”“滚。”沈微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带着你的东西,滚出东院。”李福愣了半晌,终究是躬身退了出去。沈微叫张嬷嬷:“把这些东西抬去库房,锁在最里面,跟我那些嫁妆放一起。别让它们脏了念安住过的地方。”张嬷嬷眼圈通红,应了声“是”,转身时,肩膀却在发抖。从那天起,东院就空了。念安的笑声、哭声,甚至他半夜饿了的哼唧声,都没了。沈微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是顾晏廷送的。 那支他初遇时为她簪上的羊脂玉簪,玉质温润,是当年他在古玩街淘来的,说“配得上沈家小姐的眉眼”;那件他打了胜仗归来送的紫貂裘,毛针顺滑,是圣上御赐的贡品;还有那方他亲手刻的端砚,砚台背面刻着“执子之手”,那时他说,等念安大了,要教他写字。从前她以为这些是爱,是独属于她的心意。可现在看来,不过是他扮演“好丈夫”时的道具,就像每月十五来东院留宿的流程,像他给柳玉容送去的长白山人参、给老夫人的暖手炉,都是明码标价的“赏赐”。 她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用油纸包好,装进箱子,贴上封条。心死了,连带着身体也麻木了,整理完最后一箱时,窗外的腊梅落了最后一片花瓣。她翻出母亲的遗物,一本线装的《女诫》,书页间夹着一张小像。是她亲手画的念安,刚出生时的样子,眉眼像她,鼻子和嘴巴却像极了顾晏廷,睡得安稳,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沈微用指腹轻轻摸着画像上的小脸,眼眶终于热了。西院的热闹还在继续。 柳玉容大概是嫌隔着墙不够显眼,竟亲自来了东院。她穿着一身绯红蹙金锦裙,裙摆上绣着缠枝莲,走一步,金线就晃眼。怀里抱着顾念祖,孩子穿着杏色袄子,脸蛋红扑扑的,正啃着个蜜饯果子。“妹妹,你这院里怎么一股子药味儿? ”柳玉容捂着鼻子,故作关切地皱着眉,“闻着都让人心里发堵。你也别总闷着,人会闷出病的。”她把顾念祖往前递了递:“念祖,快叫婶娘。你婶娘以前最喜欢你了。 ”顾念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沈微,眼里满是陌生,甚至还带着点被柳玉容惯出来的骄纵,扭过头,往柳玉容怀里缩了缩。沈微的目光落在孩子脸上。真像啊,眉眼间竟有几分像念安。 只是念安的眼睛更亮些,像淬了星光。“妹妹也别太伤心了。”柳玉容自顾自地坐下,端起桌上的茶盏,又嫌恶地放下,“这茶都凉透了,下人是怎么伺候的? 赶明儿我给你送两个伶俐的过来。”“不必。”沈微开口,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东院的人,笨是笨了点,至少不会乱说话。”柳玉容脸上的笑僵了僵。 她知道沈微在指什么——上个月府里传言,说柳玉容怀顾念祖时,顾晏廷在西院宿了整整三个月。虽然后来被顾晏廷压下去了,但这根刺,显然扎在了沈微心里。“妹妹这是还在怪我?”柳玉容叹了口气,伸手想去拍沈微的肩,“我知道你心里苦,可念安那孩子……也是福薄。你看念祖多结实,这才是顾家该有的根苗。 ”她的手不经意一挥,扫到了沈微腰间的玉佩。“啪”的一声脆响,玉佩摔在青石板上,碎成了三瓣。那是沈微的母亲留给她的遗物,和田暖玉,雕着并蒂莲。念安满月时,她还把玉佩用红绳系着,挂在孩子脖子上,说“保我儿平安”。 柳玉容故作惊慌地捂住嘴:“哎呀!妹妹,对不住!我这手太笨了!”她弯腰想去捡,又立刻直起身,笑着说,“碎了就碎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回头我让王爷给你寻十块八块更好的,保准水头比这个足。”她顿了顿,意有所指地补充,“说到底,死物哪有活人重要呢?”沈微慢慢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柳玉容。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像结了冰的寒潭,直直地看着她。柳玉容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最后抱着顾念祖,几乎是落荒而逃。沈微没有去捡地上的碎玉,就那么坐着,直到天色擦黑。顾晏廷来了。他大概是从柳玉容那里听了什么,脸色阴沉得可怕,一进门就踹翻了脚边的炭盆,火星溅得满地都是。“沈微,你闹够了没有? ”他低吼,玄色锦袍上还带着西院的酒气和脂粉香,“玉容好心来看你,你给她脸色看? 就为了一块破玉,把念祖都吓哭了!”他走近几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一个寡嫂,在王府本就不易,你身为弟媳,不帮衬也就罢了,还处处刁难!你就不能顾全大局? 就不能让我省点心?”沈微抬眸,看着这个曾经让她心动的男人。他的眉眼还是俊朗的,只是眼底多了些她看不懂的算计和冷漠。她轻声说:“顾晏廷,我们合离吧。 ”顾晏廷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冷笑出声:“沈微,你疯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合离? 你的吃穿用度,你的沈家小姐身份,都是顾家给的!离了我,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什么都不要。”沈微站起身,裙摆扫过冰冷的地面,“我只要带走念安的灵位。 ”“不可能!”顾晏廷厉声打断她,“念安是顾家的血脉,他的灵位必须入顾家祠堂! ”正吵着,柳玉容端着一碗参汤进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丫鬟,显然是故意来的。“王爷,您别跟妹妹置气。”她柔柔弱弱地劝,“妹妹刚没了孩子,心里苦,说些胡话也是有的。 ”她转向沈微,语重心长:“妹妹,你怎么能说合离呢?王爷待你还不够好吗? 当年你沈家落难,是谁帮你父亲保住了乌纱?再说,念安是顾家的种,灵位怎么能让你一个外姓人带走?传出去,顾家的脸面往哪搁?你这不是让王爷难做吗? ”沈微看着她,突然笑了。柳玉容被她笑得心里发慌,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参汤碗。 “顾晏廷,”沈微的目光重新落回丈夫身上,“我最后说一次,我要合离,我要带走念安。 ”顾晏廷气得额角青筋暴起:“好!好得很!你不是想要了断吗?我成全你! 你不是舍不得你儿子吗?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种!”他拽着沈微的手腕,一路拖向顾家祠堂。沈微的手腕被勒得生疼,裙摆扫过雪地,留下凌乱的痕迹,可她没挣扎,也没喊疼,就那么被他拖着走。张嬷嬷在后面跟着,急得直跺脚,却被李福拦住了。 祠堂里阴森森的,供奉着顾家列祖列宗的牌位。顾晏廷一把将沈微推到地上,指着最前排的牌位:“看清楚!这是我顾家的列祖列宗!念安是顾家的子孙,生是顾家的人,死是顾家的鬼!”他拿起三炷香,点燃,插进香炉,对着牌位躬身:“沈氏不肖子孙顾晏廷,告慰列祖列宗。念祖已平安周岁,长孙念安顽劣体弱,福薄缘浅,未能存世。然其生于顾家,死亦当为顾家之鬼,护佑顾家香火绵延。”他放下香,转身面对沈微,眼神冰冷:“沈微,你看清楚了。念安此生最大的用处,就是护着念祖长大,全我顾家大义。从今日起,他与你,尘缘已断。”沈微趴在冰冷的青砖上,手腕火辣辣地疼,可心里却像被冻住了一样,连疼都感觉不到了。她抬起头,看着顾晏廷那张冷漠的脸,突然轻声笑了出来,笑声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带着说不出的悲凉。顾晏廷皱眉:“你笑什么? ”沈微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目光平静地扫过那些牌位,最后落在顾晏廷脸上:“顾晏廷,你真以为,念安是你的儿子?”顾晏廷一愣,随即怒道:“沈微!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沈微笑了,眼底却没有一丝温度,“你仔细想想,念安出生那天,你在哪里?”顾晏廷的脸色瞬间变了。念安是早产的,比预产期早了整整一个月。那天顾晏廷正在西院陪着柳玉容——柳玉容说自己心口疼,太医守了整整一夜。沈微疼得在产房里打滚时,听到的却是西院传来的、柳玉容娇柔的笑声。 “你……”顾晏廷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被人戳中了最隐秘的心事,“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沈微转过身,一步步往祠堂外走,“只是觉得,你今日这番话,说得太早了。顾家的香火,到底能不能续上,还不一定呢。”她的背影挺直,像一株在寒风中倔强生长的梅。顾晏廷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窜上来,顺着脊椎,直抵心口。他想喊住她,想问清楚那句话的意思,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柳玉容端着参汤站在祠堂门口,脸色苍白。刚才沈微的话,她听得一清二楚。她看着顾晏廷,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被顾晏廷阴沉的眼神吓退了。 “王爷……”她嗫嚅着。“滚。”顾晏廷低吼,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带着你的参汤,滚回西院!”柳玉容吓了一跳,转身匆匆离开。走到回廊拐角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祠堂的方向,眼底闪过一丝慌乱,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狠戾。 东院的雪还在下。沈微站在廊下,看着雪花落在念安曾经玩过的拨浪鼓上,慢慢覆盖了那层薄薄的灰尘。张嬷嬷递来一件斗篷:“夫人,天太冷了,进屋吧。 ”沈微接过斗篷,却没有穿,只是拢在臂弯里。“嬷嬷,”她轻声说,“我母亲当年留下的那些铺子,账目还在吗?”张嬷嬷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眼睛亮了起来:“在!都锁在库房最里面的樟木箱里,老奴每月都亲自去核对,分文不少! |
精选图文
 阮希雅贺景(阮希雅贺景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希雅贺景)阮希雅贺景小说最新章节列表(阮希雅贺景)
阮希雅贺景(阮希雅贺景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希雅贺景)阮希雅贺景小说最新章节列表(阮希雅贺景) 墨泽韩小卿(韩小卿墨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墨泽韩小卿)最新章节列表(韩小卿墨泽)
墨泽韩小卿(韩小卿墨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墨泽韩小卿)最新章节列表(韩小卿墨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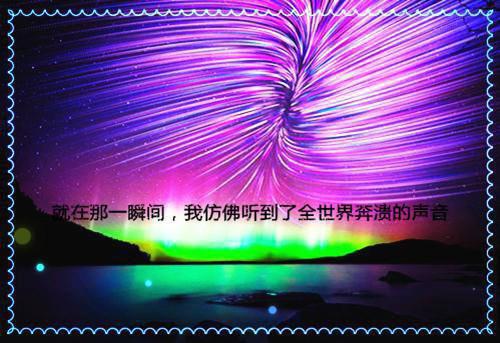 胡暮烟季君唯(胡暮烟季君唯)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胡暮烟季君唯后续免费阅读)胡暮烟季君唯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胡暮烟季君唯)
胡暮烟季君唯(胡暮烟季君唯)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胡暮烟季君唯后续免费阅读)胡暮烟季君唯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胡暮烟季君唯) 夏沐晴陆季初免费阅读无弹窗夏沐晴陆季初(夏沐晴陆季初)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夏沐晴陆季初)夏沐晴陆季初最新章节列表(夏沐晴陆季初)
夏沐晴陆季初免费阅读无弹窗夏沐晴陆季初(夏沐晴陆季初)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夏沐晴陆季初)夏沐晴陆季初最新章节列表(夏沐晴陆季初) 沈青禾徐清彦免费阅读无弹窗沈青禾徐清彦(沈青禾徐清彦)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青禾徐清彦)沈青禾徐清彦最新章节列表(沈青禾徐清彦)
沈青禾徐清彦免费阅读无弹窗沈青禾徐清彦(沈青禾徐清彦)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青禾徐清彦)沈青禾徐清彦最新章节列表(沈青禾徐清彦) 徐璐璐周嘉栩免费阅读无弹窗徐璐璐周嘉栩(徐璐璐周嘉栩)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徐璐璐周嘉栩)徐璐璐周嘉栩最新章节列表(徐璐璐周嘉栩)
徐璐璐周嘉栩免费阅读无弹窗徐璐璐周嘉栩(徐璐璐周嘉栩)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徐璐璐周嘉栩)徐璐璐周嘉栩最新章节列表(徐璐璐周嘉栩) 桑倪季琛免费阅读无弹窗桑倪季琛(桑倪季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桑倪季琛)桑倪季琛最新章节列表(桑倪季琛)
桑倪季琛免费阅读无弹窗桑倪季琛(桑倪季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桑倪季琛)桑倪季琛最新章节列表(桑倪季琛) 沈芮绮季坦越免费阅读无弹窗沈芮绮季坦越(沈芮绮季坦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芮绮季坦越)沈芮绮季坦越最新章节列表(沈芮绮季坦越)
沈芮绮季坦越免费阅读无弹窗沈芮绮季坦越(沈芮绮季坦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芮绮季坦越)沈芮绮季坦越最新章节列表(沈芮绮季坦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