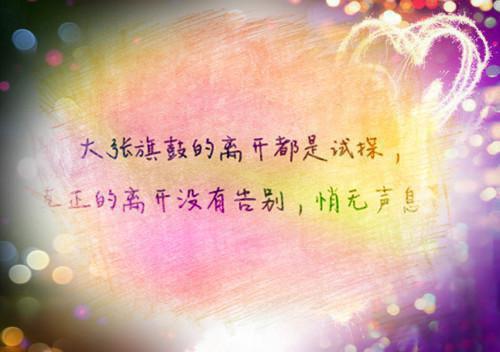也许我最终会停止思念你阿迟宋晚热门小说推荐_完本小说大全也许我最终会停止思念你(阿迟宋晚)
|
第一章 新婚第二天奔赴战场我叫沈如晦,今年二十三岁。三年前,我娶了宋晚。 那天我刚从边关回来,满身的血和泥。圣旨追到营门口,要我立刻成亲。我没见过宋晚,只知道她是丞相的女儿。我想,娶就娶吧,女人都一样。洞房夜里,我掀了她的盖头。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得像边关的星,却没说话。我喝了合卺酒就躺下。她坐在榻沿,手攥衣角,一整夜没合眼。第二天鸡鸣,我起身披甲。她替我系腰带,指尖冰凉。 我说一句“走了”,就再没回头。此后一年,我没回家。军营里,我忙着练兵、剿匪、杀人。 副将偶尔说:“夫人把老宅打理得极好,老夫人天天夸。”我嗯一声,心里无波。
我以为宋晚会哭会闹,会像别的女人那样写信诉苦。可她一个字都没写。我偶尔想起她,只有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别的都模糊。第二年春,我回京述职,顺路回家。 宋晚在廊下等我,穿淡青裙,头发松松挽着。她端茶,问我点心。我咬一口桂花糕,太甜,皱眉。她低声:“下次少放糖。”夜里她睡里侧,背对我,呼吸轻得像猫。我想抱她,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她太安静,安静得像不存在。第四天一早,我走了,没回头。半年后,我收到家信,说老夫人病重,要我回去。我连夜赶回,老夫人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 拉着我的手说:“如晦,晚晚是好孩子,你别辜负她。”我点头,心里却想:怎样才算不辜负?老夫人走后,宋晚更静。她穿素白,木簪挽发,日日抄经念佛。 我半夜回府,见她跪在佛前,背影像纸人,一戳就破。我想叫她,喉咙却像堵了棉花。 第三年,我升正二品镇北将军,皇上赐新宅。我吩咐管家:三日后搬家。宋晚站在院中,看箱子抬出。忽然说:“我能不去吗?”我愣一下:“你是我妻。”她笑,却比哭难看:“原来你还记得。”那天我们第一次吵。其实不算吵,只是两句顶两句。 最后她哭了,泪珠成串。我抬手想擦,她躲开:“沈如晦,你走吧,别回来。”我走了,真的没回去。新宅很大,我住书房,喝酒练剑,醉了就睡。副将劝我回旧宅,我说没空。 其实有空,只是怕见她。一个月后,宫宴。皇上问:“夫人怎没来?”我说她病。 皇上赐太医。我谢恩,心里知道她不会看。回府路上,我路过糕点铺,想起她的桂花糕。 我买了一盒,甜得发腻。我站在新宅门口,不知该进哪道门。我去了旧宅。 门房结舌:“夫人去了别院。”我又追到别院。小丫鬟指湖。她坐在石凳,手里一把鱼食,一点一点抛。湖水一圈一圈荡。我把盒子递过去:“桂花糕。”她没接:“沈将军怎来了? ”我张了张嘴:“宫里赐太医。”她笑:“我很好,不看。”我蹲下,与她平视。她瘦了,眼下青。我说:“晚晚,回家吧。”她摇头:“那不是家。”我心里一疼:“你是我妻。 ”她看我,像看路人:“现在不是了。”她从袖里抽出一张纸:和离书,已签。 我手指颤:“我不同意。”她起身:“由不得你。”我砸了书房。她站门边,看我疯。末了,递我一杯冷茶:“醒酒。”我坐地上,问她:“为何?”她说:“我不爱你了。 ”我笑:“爱过吗?”她不答,转身。我回新宅,日日酒,夜夜唤她名。副将看不下去,去求她。她来了,在门口,不进。我扑过去,她推开:“别让我恨你。”我松手,她走了。 我戒酒,上朝,练兵,像无事发生。可我知道,一切变了。半年后,北狄犯境,我请旨出征。 我去别院辞行。她种花,见我,不语。我说:“打仗去了。”她点头。 我说:“若回不来……”她截住:“你会回来。”我苦笑:“担心我? ”她低头:“不想欠你。”我站片刻,走。边关苦寒,我杀敌如麻。副将说我疯了。 我说想早点回家。其实心里明白:家已散。八个月,我们胜了。我左臂中箭,筋断,差点废。 皇上亲迎,赏金万两,我全辞,只求一事:解甲归田。皇上愣半晌,准。我回旧宅,人空。 丫鬟说夫人搬去城南庄子。我追去。庄子不大,篱笆围院。宋晚晾衣,手湿。见我,愣。 我说:“我辞官了。”她嗯。我递新纸:空白婚书,只我名。“这次换我等你。”她不接。 我站良久,转身。她忽喊:“沈如晦。”我回头。她眼睛亮,像三年前:“我饿了。”我笑,泪滚:“做饭给你。”那天起,我住庄子。劈柴、挑水、种菜。她仍少话,却偶尔弯眼。 第二章 回到庄子我在庄子的第一晚,睡的是柴房。宋晚没赶我,也没留我。 她把被褥扔在门口,说:“灶房有热水,自己烧。”说完便进了屋,门栓“咔哒”一声,干脆利落。我抱被褥站了片刻,抬头看天,月亮像一弯刀,冷冷悬着。 心里忽然想起三年前洞房夜她也是这般沉默地坐着,等我开口。那时我没说话,如今依旧不知从何说起。柴房有张窄榻,我躺下,旧伤隐隐作痛。左臂箭创未愈,白日里劈柴时又裂了口子,血透衣。我懒得换药,只用水冲了冲,疼得厉害时,我咬木柴,想起她递给我的那杯冷茶,苦得发涩,却把我从醉里拉回人间。天蒙蒙亮,我起身。 灶房冷锅冷灶,我生火,煮了一锅粥。米粒沉在锅底,我搅得急,粥糊了。宋晚进来,披一件旧青衫,头发散着,看锅里黑乎乎的粥,没说话,只舀了一盆水,重新淘米。 我站在一旁,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她煮粥,我添柴。火光映在她侧脸,睫毛上有细小的汗珠。 我开口:“昨晚……”她“嗯”了一声,没抬头。我便闭嘴。粥滚了,她盛两碗,一碗放我面前,自己端一碗坐门槛上喝。我喝一口,没味,却比昨晚的冷茶暖。饭后她下田。 我跟去,她拔草,我挥锄头。太阳毒,我背心很快湿透。她递水,我仰头灌,水沿下巴流到衣襟。她看我一眼,说:“伤口裂了。”我“哦”了一声,继续锄。血渗出,染了袖口。她皱眉,转身回屋,片刻拿来干净布条扔给我:“自己缠。”我单手笨拙,布条掉泥里。她叹了口气,蹲下替我包扎。指尖碰到皮肤,像那年替我系腰带,冰凉。 我屏住呼吸,怕一动她就缩回。正午,她回灶房做饭。我坐门槛,看远处青山。阿黄跑来,是条瘦狗,冲我摇尾。我摸它头,想起军营里的战马,不知它们如今怎样。宋晚出来,丢给我一把青菜:“择菜。”我择得慢,菜叶掉一地。她蹲下来一起择,手指飞快。 我偷看她,她眼角有细纹,却比从前柔和。饭后她午睡,我劈柴。木柴硬,震得虎口发麻。 我想起战场劈盾,比这省力。日头西斜,柴垛堆得高,我脱了外衫,汗水顺脊背流。 宋晚醒来,站窗边看我,目光淡淡。我冲她笑,她别开眼。夜里,我仍睡柴房。蚊子多,我翻来覆去。窗外有脚步声,轻得像猫。我屏息,门被推开一条缝,一只碗放在地上,是驱蚊草药。脚步声远去。我摸黑端起碗,心里像被蚊子叮了一口,痒,却挠不着。第二日,我起得早,挑水。井深,我臂伤未好,摇辘轳慢。宋晚路过,站一旁看。我咬牙,一桶上来,水泼半桶。她伸手帮忙,两人一起摇。水满了,她忽然说:“井绳快断了。 ”我点头:“明日换。”她说:“柴刀钝了。”我又点头:“磨。”她看我一眼,像看陌生人,又不像。早饭是昨日剩粥,我添水煮开,她没嫌弃。 饭后我去村里换井绳、磨刀。回来时,她正在院里晾衣,孩子衣裳小小一件,随风晃。 我心口一紧,想问她这些年怎么过,却开不了口。午后,我蹲在树下磨刀。 宋晚抱阿迟出来——那是个粉团似的女娃,三岁大,眼睛像她。我愣住,刀在石上划出刺耳声。宋晚说:“叫阿迟。”我张张嘴,嗓子发干:“阿迟。”孩子怯怯,躲她娘身后。我手在裤腿上擦了擦,不敢上前。宋晚解释:“你走后一个月,我发现有了她。 ”我点头,心里翻江倒海,脸上却木。她又说:“和离书我撕了,没用。”我低头继续磨刀,石屑飞溅,像那年战场乱箭。傍晚,阿迟在院里追蝴蝶,宋晚烧火做饭。我劈柴,一斧下去,木柴裂成两半,像把那些年劈开。阿迟跑近,仰头看我,忽然伸手:“抱。”我僵住,宋晚在灶房门口望来,目光安静。我蹲下,双手抱起孩子,她轻得像片羽毛。 她奶声奶气:“你是我爹?”我眼眶发热:“是。”她小手拍我脸:“那你为什么才回来? ”我答不出,只抱紧她,像抱住错失的三年。夜里,阿迟睡中间,宋晚睡里侧,我躺外侧,像真正的家人。孩子小脚蹬我肚子,我握住,软软一团。宋晚背对我,呼吸轻。 我小声:“以后不走了。”她没应声,却往孩子那边靠了靠,留给我半臂的空。我闭眼,听见自己心跳,像战鼓,却不再为杀戮,只为枕边人。第三日,我修屋顶。 宋晚在下面递瓦片,阿迟拍手笑。我低头,见她仰头,阳光落她眼里,碎成星。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归处,不过是有人等你抬眼。第三章 只想护好他们屋顶修好的那天傍晚,下起了小雨。瓦片刚铺好,一滴水也没漏。我蹲在屋脊上,看雨丝穿过桂花树,打在阿迟的小伞上,噼啪作响。她仰着头喊:“爹,雨停了我们能去捉知了壳吗? ”我应了一声,嗓子被雨气呛得发苦。宋晚在灶房门口招手,说饭好了。我踩着湿瓦下来,鞋边全是泥,心里却踏实。夜里,雨声未歇。柴房潮得厉害,我抱着被褥想另找个地方。 宋晚在正屋门口停了一会儿,淡淡一句:“地上凉,进来睡。”我愣了愣,抱着被子跨过门槛。阿迟已经睡熟,小脸红扑扑,手里攥着一块桂花糕。我把被褥铺在榻下,宋晚递给我一条旧毯子,上面绣着早春的燕子。我低声道谢,她没接话,只把油灯芯子捻短,屋里暗了。半睡半醒之间,听见她翻身,床板吱呀一声,像叹息。第二日雨停,地皮软得像发糕。我起得早,看院子里积了一洼水,天光映在里面,蓝得晃眼。 阿迟赤脚踩水,宋晚拎着她后领子往回拖:“鞋!”阿迟咯咯笑,甩得泥点子到处都是。 我拿了锄头,准备去后坡把菜畦翻一遍。宋晚在身后喊:“把早饭吃了。 ”桌上是白粥、咸菜,还有一盘摊得金黄的鸡蛋。我扒了两碗,她低头喝粥,睫毛上还沾着水汽。饭后我下地,阿迟跟在我后面像条小尾巴。她问:“爹,你打仗的时候怕不怕?”我锄头一顿,如实说:“怕。”阿迟瞪大眼:“那你怎么还冲? ”我说:“身后是国土,退不了。”她似懂非懂,拾起一块碎瓦片在地上画线,说是城墙。 我弯腰握住她的小手:“以后再画,先把草拔了。”她撅嘴,却乖乖蹲下。日头升上来,菜畦里一片青绿,我汗水滴进土里。心里生出奇异的感觉:这些土、这些苗,是我能守住的江山。中午,宋晚来送饭。她挽着篮子,步子稳,但眉心比从前松。 篮子里是韭菜盒子,两面煎得焦黄,香味蹿得老高。我吃得急,烫了舌头。 她拧开水囊递过来:“慢点,没人抢。”我含糊应声水囊里装的是温过的桂花茶,甜里带苦,像她当年递给我的那杯。阿迟坐在田埂上啃盒子,嘴角沾油。宋晚拿手帕给她擦,动作又轻又快。我低头,看见她腕子上有一道旧疤,像细线,心里一抽,想问,又咽回去。 下午,我把菜畦翻完,顺道砍了两捆柴。回院时,阿迟正跟狗追蜻蜓,宋晚在灶房蒸米糕。 锅盖掀开的瞬间,白汽涌出来,她侧脸被水汽蒸得发红。我把柴码好,去井边冲凉。 井水冰凉,浇在伤口上,像刀割。我咬牙,听见身后脚步,宋晚端着一盆温药水:“别逞能。 ”我坐下,她蹲下来替我擦洗。药水渗进裂开的虎口,我嘶了一声,她动作更轻。 夕阳照在她发梢,细小的绒发闪金光我忽然想起洞房夜她也是这样蹲着替我解甲,只是那时我一句话也没说。夜里,阿迟闹着要听故事。我搜肠刮肚,只能讲战场上的事,却怕吓着她。宋晚在旁缝补,头也不抬:“讲你小时候掏鸟窝。”我愣了愣,竟真想起五六岁在乡下爬枣树的事,便讲给她听。阿迟笑得打滚,宋晚嘴角也弯了。灯光下,我们像一家人——本来就是一家人,只是迟了四年。第三日,村里来收桂花。 宋晚把晒干的桂花卖给酿酒的赵家,换了三十文钱。她数铜钱时,手指沾了桂花香。 递给我十文:“去买斤肉,阿迟馋了。”我提着肉回来,顺路给阿迟带了个草编的蝈蝈笼。 阿迟高兴得满院跑,宋晚把肉切成小块,炖了一锅红烧肉。我蹲在灶口烧火,看火苗舔着锅底,心里像被什么填得满满当当。夜里,阿迟睡了,我和宋晚坐在门槛上乘凉。 月亮圆得过分,像谁剪了贴天上。我鼓了半天劲,问:“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她手指绕着发梢,语气平淡:“先是哭,后来不哭了,就熬。 ”我喉咙发紧:“为什么不写信骂我?”她侧头看我,眼神清亮:“骂你你就会回来么? ”我答不上来。风吹过,桂花落在她膝上,我伸手拂去,指尖碰到她手,她没有躲。第四日,我带着阿迟去河里摸螺。宋晚在岸边洗衣,偶尔抬头看我们。阿迟踩滑,我一把拎住后领,她咯咯笑,水花溅我一脸。宋晚在岸上喊:“别让她着凉!”我应着,心里却想:原来被人管是这般滋味。午后,我们把摸来的螺炒了,阿迟辣得直吸气,却还要吃第二碗。宋晚递水,嘴角带笑,那笑像桂花,小小一朵,却香得悠长。夜里,阿迟非赖在我榻上睡,宋晚也由她。小丫头蜷在我臂弯,像只暖炉。宋晚躺在最里侧,背对我。灯熄后,我轻声:“以后,我每月初一十五都去集市卖柴,换银子给你和阿迟添新衣。”她沉默片刻,嗯了一声。我听着她呼吸逐渐均匀,心里像雨后的田,软得能掐出水。第五日,我起了个大早,把院角的杂草全拔了,围上篱笆,准备来年种一架葡萄。阿迟在旁边递竹条,宋晚做早饭。炊烟升起时,我忽然觉得,这便是我拼命杀敌想要守的烟火气。从前我护的是千里江山,如今只想护这一方小院。 第四章 烟火气息第五日傍晚,我蹲在篱笆脚下钉最后一根竹桩。阿迟举着油灯,灯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她的小脸在光影里忽大忽小。宋晚端着簸箕出来,里头是晒干的桂花,金黄细碎,像一捧凝固的日光。她把簸箕放在石桌上,低头拣去碎叶,动作极轻,仿佛怕碰疼了那些花。我锤完最后一钉,抬头望她。她额角有汗,碎发黏在皮肤上,像雨后新出的柳条。我想替她拨开,手里却满是泥,只能攥了攥拳。 问:“今年酿多少桂花酒?”她没抬头,声音散在夜风里:“五斤,给阿迟留两斤做甜酿圆子。”我“哦”了一声,心里忽然生出一点贪念:若能年年如此,便是要我少活十年也认。夜里,我照例把被褥铺在榻下。阿迟滚到我怀里,小手揪着我衣领小声说:“爹,你给我做只风筝吧,要老鹰的。”我赢了。宋晚在灯下补衣,闻言抬眼:“她性子急,你做好她就扯坏。”我笑笑:“坏了再做。”她低头继续穿针,灯焰在她睫毛上跳着细碎的亮,像那年边关雪夜里的火把。我心里一动,话就脱口而出:“晚晚,我——”她截住:“早点睡,明日还要赶集。”我把话咽回去,抱着阿迟躺下。窗外虫声四起,像谁在远处敲鼓,鼓点落在心口,一声又一声。第六日,逢大集。我挑柴,宋晚挎篮,阿迟骑在我脖子上,小手揪我耳朵。晨雾未散,村道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却走得稳。集市上人声鼎沸,我把柴卖给赵家酒坊,得了四十文。 宋晚在布庄前站住,指尖掠过靛青细布,问价又放下。我掏出铜钱:“买吧,给你做夏衣。 ”她摇头:“阿迟长得快,先给她。”我执意买了布,又扯三尺桃红,给她做帕子。 她嘴角翘了翘,没再推辞。归途,阿迟抱着糖人舔得满脸黏。我挑着空扁担,宋晚走在我右侧,篮子里添了油盐针线。日头升上来,照得她耳廓透明。我侧头,看见她鬓边一根白发,心里猛地一揪。她察觉,抬眼:“看什么? ”我低声:“回去我给你拔。”她嗤笑:“一根而已,拔了还长。”我没说话,只是用扁担换了个肩,离她更近半步。午后,我把桃红布裁成帕子,阿迟在一旁捣乱。 宋晚在灶房和面,准备蒸桂花糕。我笨手笨脚,针脚歪扭,她看不下去,接过绣了几针,一对燕子便活了。阿迟拍手:“娘绣得真好。”我咧嘴:“爹也会。 ”宋晚瞥我:“你只会拿刀。”我讪笑,心里却想:若能拿一辈子刀护住这方小院,也值。 傍晚,邻居李婶送来一把春笋,说是谢我帮她家修犁。宋晚留她吃饭,李婶直摆手:“不打扰你们一家三口。”一句话,我耳根竟有些热。宋晚送她到门口,回身看我,目光软了软,像春水化冰。我低头劈柴,斧子落在木墩上,一声比一声脆。夜里,阿迟睡了。我烧好热水,端到宋晚跟前:“泡泡脚,解乏。”她没拒绝,脱了鞋袜,把脚浸进盆里。我蹲着,看那双曾经追出城门的脚,如今被岁月磨出薄茧。我伸手想摸,又怕唐突,只轻轻撩水。她忽然说:“那年我摔了,没哭,就是觉得,追不上了。 ”我喉咙发紧:“以后我慢慢走,等你。”她没应声,脚尖却在水面画了个圈,涟漪荡到我指边,一圈又一圈。第七日,我起了个大早,把屋后荒地翻了半亩,准备种瓜。 宋晚端着早饭来,看我满手血泡,皱了眉:“急什么?日子长着。 ”我笑笑:“想给你们娘俩攒点嫁妆。”她啐我:“阿迟才五岁。”我认真道:“先攒着。 ”她摇头,嘴角却翘着。午后,我把旧犁修好,借给李婶家。回来时,宋晚正在教阿迟认字,一笔一画写在沙盘里,是“安”字。我站在门边,看那母女俩头挨着头,心里像被什么填满。 阿迟抬头:“爹,你也来写。”我走过去,握住她的小手,在沙上写“归”。宋晚看着,睫毛颤了颤,没说话。傍晚,乌云压顶,我抢在雨前把晾的桂花收进屋。雨点砸在瓦上,像千军万马。宋晚在灶房烙饼,我添柴,火光映得她脸红。阿迟趴在门槛上,看雨线成帘。 我忽想起边关暴雨,兄弟们挤在帐篷里分酒,如今换了人间。宋晚递我一块刚出锅的饼,我咬一口,烫得吸气,却觉得甜。雨夜里,阿迟赖着不肯睡,非要看我雕风筝。我点起油灯,把竹篾削得极薄。宋晚坐在一旁补袜子,偶尔抬头指点:“翅膀要再弯些,才像鹰。 ”我照做,指尖被篾片划破,血珠渗出。她抓过我的手,用帕子包了,低声:“笨。 ”我任她包,心里却想:若能一直这样笨下去,也好。风筝骨架完成时,雨停了。 月光从窗棂缝里漏进来,照在宋晚低垂的睫毛上,像撒了一把碎银子。我轻声:“等风好了,带你们去后山放。她“嗯”了一声,声音轻得像猫。我忽觉胸口胀痛,伸手覆在她手背上。 她没躲,只是指尖微微抖了一下。第五章 放风筝风筝做好后的第三日,风终于来了。午后,阳光晃得河滩发白,芦苇沙沙作响。我扛着鹰形风筝,阿迟蹦跳着在前面带路,宋晚提着一只青竹篮,里头装着桂花糕和水囊。她步子不快,却稳,偶尔抬头看看风向,像从前在军营里望烽烟。阿迟跑得一脑门汗,回身催我:“爹,快些!”我应着,把线轴交给宋晚:“你拿稳,我举鹰。”她“嗯”了一声,掌心覆在木轴上,指尖被粗线勒出一道白痕。我踩着碎石往坡上跑,风鼓起风筝,猎猎作响。 阿迟在身后拍着手尖叫,声音脆亮,惊起一群白鹭。风筝越飞越高,线轴在宋晚手里呼呼转。 我回头,看见她仰着头,阳光落在她睫毛上,像撒了一把碎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所谓山河,也可以是一只纸鹰,被一根线牢牢牵在掌心。阿迟跑累了,赖在宋晚怀里吃桂花糕,碎屑沾了她一襟。我收了线,风筝缓缓落下,像归巢的鸟。 阿迟伸出小手:“娘,我也想放。”宋晚把线轴递给她,自己蹲下来,从后面环住她,教她如何迎风。风忽然大了,线猛地一紧,宋晚的手覆在阿迟手背上,母女俩同时往后仰。 我急忙托住她们后背,掌心碰到宋晚的肩胛,瘦却温暖。她没躲,只是低声说:“小心脚下。 ”风筝在空中稳住,阿迟笑得像刚开的桂花。我退后半步,看她们一大一小两个背影,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原来我拼命杀敌,守的不过就是这样的片刻。傍晚回家,阿迟趴在狗背上睡着,手里还攥着线轴。我抱着她,宋晚提肩并肩。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三条纠缠的线,一路拖进篱笆门。灶房的灯亮着,锅里有热水,我给孩子擦脸洗脚,宋晚在灶前下面条。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微微晃动,像一尾安静的鱼。吃面时,阿迟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却还惦记风筝:“爹,明天再放,好不好?”我答应。宋晚把面挑到我碗里:“多吃点,瘦得跟竹竿似的。”我扒了一大口,烫得直吸气,却舍不得吐。她低头喝汤,耳尖被热气蒸得发红。我夹了块煎蛋放她碗里,她没抬头,筷子却顿了顿。夜里,阿迟睡中间,我和宋晚各躺一侧。 孩子的小脚丫蹬在我肚子上,热烘烘。我侧身,看见宋晚背对着我,肩膀随着呼吸起伏。 我轻声:“今天谢谢你。”她没应声。过了会儿,我以为她睡着了,她却忽然开口:“风筝线旧了,容易断,明日我换新的。”我“嗯”了一声,心里像被什么填得满满的,连旧伤都不疼了。第二日,我起了个大早,把屋后那棵歪脖子枣树砍了,准备做一架更大的风筝。阿迟蹲在旁边数年轮,宋晚在灶房和面,说要蒸枣糕。斧头落下,木屑飞溅,我脱了外衫,汗水顺着脊背流。 宋晚端来凉茶,我仰头灌,看见她额角的汗珠顺着鬓角滑到下巴,滴在衣襟上,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午后,新风筝骨架搭好,比昨日那只大了一倍。阿迟兴奋地满屋跑,宋晚把旧布拆下来,洗净晾干,又找出早年绣剩的丝线,一针一线缝鹰羽。 我坐在门槛上削竹篾,偶尔抬头,看见她低垂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小扇子似的阴影,心里忽然生出一点贪念:若能日日如此,便是要我少活十年也认。风筝缝好时,天已擦黑。 阿迟抱着不肯撒手,宋晚拍她脑袋:“明日再放,风大夜凉。”孩子撅嘴,却还是乖乖睡觉。 我洗了手,帮宋晚把线轴缠上新麻线。灯芯爆了个花,她下意识往后躲,我伸手护住她发顶。 指尖碰到她额角,她僵了一下,没动。我低声:“晚晚,这些年……”她忽然把线轴塞到我手里:“快缠,别断了。”我闭嘴,老老实实缠线,心里却像打翻了一坛陈酿,苦辣酸甜全涌上来。第三日,风更猛。我们去了后山山顶,那里有一大片草甸。我举着风筝跑,宋晚牵着阿迟站在坡上,裙摆被风掀起,像一面青旗。 风筝刚离地就被风卷得老高,线轴在我手里呼呼转,几乎要脱手。阿迟尖叫着拍手,宋晚仰头望天,发丝飞舞,阳光穿过云层,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突然想起边关的雪夜,也是这样冷烈的风,吹得人骨头生疼,却吹不散心里的火。 风筝飞到最高处,线绷得笔直。我回头,看见宋晚双手护着阿迟的耳朵,怕风太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我拼命杀敌,守的不过就是这样一双手,这样一个侧影。下山时,阿迟趴在我背上睡着,宋晚提篮并肩。夕阳把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幅剪不断的画。 我侧头看她,她嘴角沾着一点桂花糕碎屑,我伸手想拂,又怕唐突。她忽然停步,从篮里拿出一块帕子递给我:“脸上,脏了。”我胡乱抹了一把,却越抹越花。她叹了口气,踮脚替我擦,指尖带着桂花香,轻轻掠过我的眉心。我屏住呼吸,听见自己心跳如鼓。夜里,阿迟睡沉,宋晚在灯下拆风筝线。我坐在对面削竹篾,偶尔抬头,看见她指尖被线勒出的红痕,心里一抽。我伸手:“我来。”她没推辞,把线轴递给我,自己揉了揉手,我缠线。她忽然开口:“阿迟生辰快到了,想不想去镇上逛逛?”我愣了愣,随即点头:“想。”她低头笑了笑,灯火在她睫毛上跳动,像碎星。那一夜,我躺在榻下,听雨打瓦,心里前所未有地安静。阿迟的小呼噜,宋晚偶尔的咳嗽,窗外风声,都成了最动听的乐章。我闭眼,想:若能这样过一辈子,刀口舔血的日子也算值了。第四日,我起了个大早,把屋后那棵老槐树也砍了,准备给阿迟做一只木马。宋晚在灶房蒸枣糕,香气飘得满院都是。我劈柴,阿迟蹲在旁边数年轮,每数一圈就喊一声:“爹,这树比我大好多!”我笑着应:“等你长大,爹给你做更大的风筝。”她眼睛亮亮的,像盛满了整个夏天的光。第六章 举办婚宴木马做到一半,阿迟的生辰就到了。那天一早,宋晚把阿迟支去李婶家借筛子,我趁机把木马搬到院里,用细砂纸打磨棱角。木头是槐树的, |
精选图文
 亡国妖妃,我真不是故意当祸水(桑宁贺兰殷)小说全文免费桑宁贺兰殷读无弹窗大结局_(桑宁贺兰殷)亡国妖妃,我真不是故意当祸水小说全文免费桑宁贺兰殷读最新章节列表(桑宁贺兰殷)
亡国妖妃,我真不是故意当祸水(桑宁贺兰殷)小说全文免费桑宁贺兰殷读无弹窗大结局_(桑宁贺兰殷)亡国妖妃,我真不是故意当祸水小说全文免费桑宁贺兰殷读最新章节列表(桑宁贺兰殷) 沈青玦裴邺免费阅读无弹窗沈青玦裴邺(沈青玦裴邺)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青玦裴邺)沈青玦裴邺最新章节列表(沈青玦裴邺)
沈青玦裴邺免费阅读无弹窗沈青玦裴邺(沈青玦裴邺)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青玦裴邺)沈青玦裴邺最新章节列表(沈青玦裴邺) 林稚语顾屿白免费阅读无弹窗林稚语顾屿白(林稚语顾屿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稚语顾屿白)林稚语顾屿白最新章节列表(林稚语顾屿白)
林稚语顾屿白免费阅读无弹窗林稚语顾屿白(林稚语顾屿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稚语顾屿白)林稚语顾屿白最新章节列表(林稚语顾屿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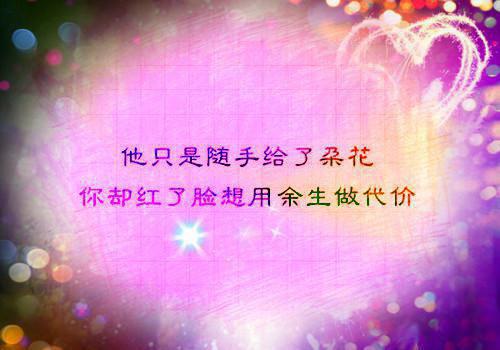 谢臻陆云烟小说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谢臻陆云烟小说免费最新章节列表
谢臻陆云烟小说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谢臻陆云烟小说免费最新章节列表 人气小说推荐谢臻陆云烟 谢臻陆云烟免费在线阅读
人气小说推荐谢臻陆云烟 谢臻陆云烟免费在线阅读 (热推新书)(祝芸汐司瑾)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祝芸汐司瑾全文阅读无弹窗
(热推新书)(祝芸汐司瑾)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祝芸汐司瑾全文阅读无弹窗 君照临慕容阀珍藏美文读物我渡佛子向红尘-我渡佛子向红尘已完结全集大结局小说君照临慕容阀
君照临慕容阀珍藏美文读物我渡佛子向红尘-我渡佛子向红尘已完结全集大结局小说君照临慕容阀 我渡佛子向红尘小说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君照临慕容阀小说免费最新章节列表
我渡佛子向红尘小说在线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君照临慕容阀小说免费最新章节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