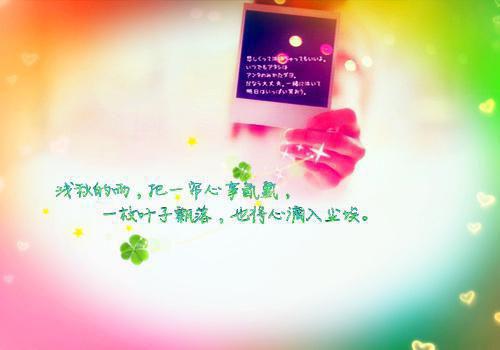他的深情,是致命的骗局钟伯庸厉骁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他的深情,是致命的骗局钟伯庸厉骁
|
挽着厉骁手臂的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刻折断自己的手。可我不能。从现在起,我是他深情款款的“新婚妻子”苏晚,而他,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那个间接导致我最好搭档终身残疾的疯子。我们伪装成夫妻,潜入这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豪门,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我必须对他巧笑嫣然,说着最甜蜜的谎言,同时在心里将他凌迟处死一万遍。这场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对我灵魂的酷刑。1钟家宴会厅奢华得令人窒息。 水晶吊灯的光芒冰冷地洒在长长的餐桌上,每一件银质餐具都反射着我僵硬的笑脸。 隔着薄薄的衣料,我能感受到他肌肉的坚实,那触感像一块烙铁,烫得我只想立刻甩开。 主位上,家主钟伯庸温文尔雅,笑容背后,一双眼睛却像手术刀,似乎要将我们的伪装层层剥开。钟伯庸微笑着示意仆人,将一盘精致的桂花糕,不偏不倚地推到我的面前。那甜腻的香气像一把钥匙,猛地捅开我记忆最深处的枷锁,瞬间将我拖回童年那间书房——父亲冷漠地推开母亲递来的同款糕点,严厉地斥责:“情感是混淆判断的毒药。”就在我快要被记忆溺毙的瞬间,钟伯庸含笑开口,问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看你们如此恩爱,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脸上的笑容几乎维持不住。这瞬间的僵硬,被钟伯庸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身体微微前倾,镜片后的眼神闪过一丝了然的精光,用更轻柔、更具穿透力的声音补充道:“怎么了,厉太太? 难道这段回忆……有什么不方便对我这个老头子讲的吗?”就在这时,我感到膝盖上传来一阵短暂而尖锐的压力——是厉骁的手,在桌布的掩护下,用指关节给了我一个警告性的触碰。那与其说是提醒,不如说是一种冰冷的命令。 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将那段冰冷的回忆压下去,从恐慌的深渊中,捞起另一段唯一真实、温暖的记忆——一段不属于厉骁,而属于我和林凯的回忆。 我脸上重新堆起最甜蜜羞涩的笑容,微微靠向这个我最憎恶的男人,开口说道:“有一次我们出外勤,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躲在一个老旧车站的屋檐下。 他看我冷得发抖,就把他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还给我讲笑话……”我一边说着,一边强迫自己将记忆中林凯那温暖和煦的笑容,安在厉骁这张冷漠的脸上。每一个字,都是对我挚友的背叛;每一次微笑,都是对我身边这个男人无声的反抗。说完,为了让表演更加天衣无缝,我拿起一块桂花糕,在钟伯庸审视的目光下,小口地、优雅地咽了下去。那甜腻的味道滑过喉咙,像在吞咽我自己的创伤与谎言。 2那场令人作呕的晚宴结束后,我和厉骁之间只剩下死寂。通往废弃灯塔的路崎岖不平,海风卷着咸腥的湿气,像一只冰冷的手,一遍遍抚过我的后颈。 我强迫自己复盘晚宴上的每一个细节,寻找钟伯庸的破绽,但思绪总会被身边这个男人的存在打断。他走在我左后方半步的距离,步伐轻得像一只猫,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投来的视线,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脚下一块湿滑的岩石让我踉跄了一下,他下意识地伸手想扶我,我却像被电击一样猛地躲开。 “别碰我。”我的声音比海风还冷。他的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秒,然后若无其事地收了回去。 这死寂的路上,我们之间无声的交锋,比任何争吵都更令人窒息。 当我们悄无声息地抵达灯塔时,我的警察本能让我立刻开始扫视地面。这里的痕迹太干净了,除了我们两人的脚印,几乎没有第三者留下的痕迹,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 厉骁却完全无视这些程序,他径直上前,单膝跪地,手指直接探向阴影中那具身体的脖颈。 就在他做出判断的瞬间,我也闻到了空气中那股浓烈的、代表氰化物的苦杏仁味。 唯一的线索,就这样在我们眼前被掐断了。我心脏猛地一沉,第一反应就是掏出加密通讯器向上级汇报。然而,屏幕上没有信号,只有一个冰冷的、刺眼的红色叉号。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蹿上天灵盖。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厉骁,他只是面无表情地拿出自己的设备,屏幕上是同样的死寂。 他收起设备,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说:“他们切断了一切。我们被困住了。 ”“被困住了”——这四个字像点燃引线的火星,瞬间引爆了我压抑已久的愤怒与恐惧。 我猛地转身,死死盯住他,将一年前林凯为了救他而倒在血泊中的画面,与眼前刘叔冰冷的尸体血淋淋地缝合在一起。当我嘶吼出“林凯”这个名字时,我清晰地看到,厉骁那张一直毫无波澜的脸上,瞳孔有了一瞬间难以察觉的收缩。 但这丝动摇没能平息我的怒火,反而让我更加歇斯底里:“告诉我,厉骁! 这又是你所谓的‘必要牺牲’吗?!”他静静地等我吼完,脸上恢复了那副冷得像冰的面具,然后用一种几乎是残忍的平静反问我:“你吼完了吗?吼完了就省点力气想怎么活下去。 ”这句话彻底击溃了我。我没有再看他,转身循着来路往回走。每一步都踩得极重,像是在确认脚下这片土地还不是我的坟墓。他跟了上来,不远不近,像一头沉默的野兽在评估我的弱点。我们之间隔着三步的距离,这是一个在警校里教官反复强调的、随时可以拔枪反击的安全距离。从这一刻起,我们的“同盟”关系已经死亡。他不再是我的同伴,只是我行动中最大的那个“可疑目标”。 3我和厉骁之间只剩下死寂。但调查不能停止。失去了唯一的外部线索,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埋藏在钟家那座巨大的、据说收藏着家族所有秘密的档案室里。 我将这次潜入视为一次独立的行动,而厉骁,只是一个我必须忍受并时刻提防的、不可控的危险变量。 档案室里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坟墓。我按照标准程序,从房间布局和文件分类开始进行系统性排查,寻找人事档案和访客记录。而厉骁则像个幽灵,无声地在书架间穿行,手指偶尔划过书脊,或用指关节轻轻敲击墙壁,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那种毫无章法的直觉式行动,让我本就紧绷的神经愈发烦躁。 就在我拉开一个标记着“工程维修”的档案抽屉时,身后那扇厚重的橡木门发出了几乎不可闻的“咔嗒”一声——那是老式机械锁芯落下的声音。 这不是意外,这是一个无声的陷阱。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四肢开始发软,空气似乎变得稀薄,呼吸也愈发困难。 我的大脑告诉我需要立刻评估毒气成分、呼叫支援、寻找疏散路线——但在这里,这些程序都成了废纸。我的身体迅速失力,意识开始模糊,连拔枪自卫的力气都在快速流失。 我所信奉的秩序和规则,在这个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死亡陷阱面前,彻底失效了。我,一个精英警察,第一次如此纯粹地、无助地滑向死亡的深渊。就在我即将坠入黑暗的瞬间,那个被我视为“混乱”代名词的厉骁,却展现出一种令人心惊的、野兽般的生存本能。 他没有丝毫慌乱,用一把拆信刀精准地撬开墙上一幅画的暗扣,露出一个被遗忘的通风管道。 他没有用身体护住我这种英雄式的表演,而是迅速从档案架上拿起一瓶用于保养旧书封皮的挥发性溶剂,用手帕浸湿后死死捂住我的口鼻。那溶剂的味道,与其说是刺鼻,不如说是一种冰冷的、化学的“暴力”,强行驱逐了毒气的甜腻,但也同样灼烧着我的鼻腔黏膜,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火焰般的刺痛。 我被迫依赖着这份痛苦活下来,就像一个溺水者,死死抱住了一块满是尖刺的浮木。 逃回我们临时的安全屋后,同样吸入少量气体的厉骁脸色惨白如纸,他靠在墙上,双眼紧闭,却在半昏迷中,下意识地死死抓住了我的手,用一种嘶哑的、几乎破碎的声音呢喃着:“不……不能再失去你了……”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句嘶哑的呢喃不是子弹,更像一根滚烫的探针,精准地找到了我仇恨盔甲下的那条旧裂缝,然后蛮横地、毫不留情地钻了进去,在我胸腔里搅动起一片灼热的、陌生的疼痛。 我的理智疯狂地尖叫着,告诉我这或许是另一个骗局,是他博取同情的手段。 但我的感官却无法否认,他此刻流露出的脆弱是如此真实。那只抓着我的手,冰冷、汗湿,却带着一种不容挣脱的、属于溺水者的力量。 我所认定的那个冷血的、漠视生命的“怪物”形象,第一次出现了裂痕。这个念头刚一升起,林凯苍白的脸就猛地浮现在我眼前。一股混杂着愤怒的自我憎恶冲上心头。苏晚,你这个蠢货!你忘了林凯是怎么躺在病床上的吗? 你竟然对这个骗子、这个间接的凶手产生了动摇,这简直是对挚友最无耻的背叛! 我看着他抓住我的那只手,冰冷、汗湿,却带着不容挣脱的力量——就是这只手,刚刚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而我的脑海里,却猛地浮现出林凯躺在病床上的那只空荡荡的右手。获救的我和残疾的他,救我的仇人和我恨的他……这两个画面在我脑中疯狂地撕扯、碰撞,几乎要将我的头骨从内部撑裂。最终,我没有甩开他的手,也没有回应。我只是静静地坐着,任由他抓着。从这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必须重新评估厉骁。 他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定义为“恶”的符号,而是一个更复杂的、充满了矛盾与秘密的谜。 我的目标,从单纯的“破案”,增加了一个新的、更迫切的维度:我必须弄清楚,他那句“再”一次,究竟指的是谁。4我需要冷静,需要让我的大脑重新被事实和逻辑占领,而不是被他那该死的脆弱所动摇。我抽出手,几乎是逃避似的将注意力埋进那堆从档案室带出的混乱资料里。 只有冰冷的文字和泛黄的纸张,才能让我找回一丝掌控感。在一叠陈旧的庄园维护记录底下,我翻出了一本厚重的家庭相册。我翻开它,几乎立刻就在一张家庭聚会的合照中,看到了厉瑶。她笑靥如花,脖子上戴着一枚造型独特的银质挂坠盒,那挂坠盒的表面雕刻着某种藤蔓花纹,在照片陈旧的色调中依旧清晰可见。 我的心脏无端地漏跳了一拍。就在这时,靠在墙边的厉骁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抬起,紧紧攥住了胸口处、藏在衬衫下的某个硬物。随着他这个动作,一截银色的链子从他松散的领口晃动了一下,露出了链扣和一个挂坠的顶端——那银质的链扣,那挂坠盒独特的弧线和形状,与照片里厉瑶脖子上的,一模一样。储藏室里仿佛瞬间被抽干了空气。 我拿着相册的手指开始发冷,几乎要握不住那厚重的纸板。我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状似无意地合上相册,用最平稳的语气问他:“你好像很在意胸口的东西,是项链吗? ”厉骁的身体瞬间绷紧,他睁开眼,那双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窥破秘密的惊惶。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回答,而是用手掌更用力地捂住了胸口的位置,一个纯粹的、下意识的保护性动作。他的视线极快地从我的脸,扫向我手边的相册,再猛地收回。然后,那张冷漠的面具才重新回到他脸上,他将挂坠盒塞回衣领深处,声音沙哑地回答:“我妹妹的遗物。”“妹妹”——这个词像针一样刺入我的大脑。 我脑中瞬间闪过那份被我背得滚瓜熟熟的、关于他的绝密档案,上面一行冰冷的文字如同烙印般清晰:主体:厉骁。社会关系:孤儿,无任何已知直系亲属。谎言。这个拙劣的谎言像一桶冰水,将我上一秒因他救命之恩而升起的一丝动摇与暖意彻底浇灭。他不仅在骗我,他还在侮辱我,侮辱我的专业,侮辱我的判断力!他觉得我蠢到会相信这种漏洞百出的鬼话! 那份因救命之恩而升起的动摇,此刻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我的脸上。我没有再追问,只是低下头,假装继续翻阅资料,指甲却已深深嵌入掌心,用疼痛来惩罚自己的愚蠢。 他眼神闪躲的谎言,将我们之间那点脆弱得可笑的信任,彻底碾成了齑粉。 我决定不再被动地等待他吐露真相。既然言语是谎言,那我就要寻找无法辩驳的物证。 从这一刻起,我的首要任务改变了。这不仅仅是为了破案,更是为了夺回我被他动摇的主动权。我必须在他不察觉的情况下,搜查他的私人物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清楚他真实的目的,以及他和厉瑶之间真正的秘密。 我要亲手撕开他所有的谎言。5机会稍纵即逝。 在厉骁以“探查逃生路线”为由消失在门后的一分钟内,我已经动手了。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滚烫的耻辱感。我想起林凯躺在病床上,还笑着对我说:“晚晚,你得连我的份一起,做个干干净净的好警察。”而现在,我却像个卑劣的小偷,在翻检我“同伴”的私人物品。为了那个毁掉林凯的人,我正在亲手玷污我们曾共同守护的一切。他的东西极少,只有一个背包。而在背包的最底层,我摸到了那个伪装成精装版《词典》的金属保险盒。我用从档案室带出的工具撬开锁芯,发出一声轻微但足以让我心脏骤停的“咔”响。盒盖弹开,里面没有武器,没有情报,只有一封泛黄的信,和静静躺在信旁的一个黑色U盘。我颤抖着抽出信纸,开头的四个字映入眼帘。那一瞬间,没有爆炸,没有天旋地转。 只有一种极致的、被抽入真空般的死寂。我肺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周围的一切声音、光线、甚至时间感,都向内坍缩,最终只剩下那四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视网膜上——“赠吾妻瑶”。底下龙飞凤舞的落款是:“永远爱你的夫,骁。 ”我所有的判断,所有动摇与戒备,全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笑话。我不是他的同伴,我甚至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他复仇棋局上,一枚被精心布置的、随时可以牺牲的诱饵! 一股滚烫的、几乎要将我焚毁的职业羞耻感猛地冲上我的大脑。指尖一麻,那张承载着惊天谎言的信纸,就这么轻飘飘地从我手中滑落。信纸飘落在保险盒旁,露出了它刚刚一直压着的东西——那个黑色的U盘。上面用极小的白色标签贴着一行字,那行字像一枚冰锥,瞬间刺穿了我燃烧的愤怒,将我的心脏彻底冻结——“林凯康复计划”。 林凯。林凯。我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瘫坐在地。信纸和U盘就在我眼前,一个代表着最极致的背叛,一个代表着最隐秘的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