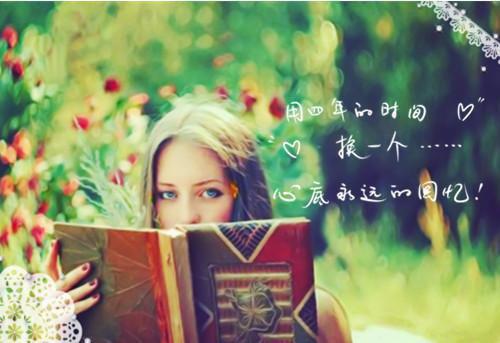《假如我拥有两个智子》苏晓林默已完结小说_假如我拥有两个智子(苏晓林默)经典小说
|
大学生活像个巨大的粒子加速器,把来自天南地北的我们这些“粒子”轰进来,各自沿着看不见的路径飞驰、碰撞。 大多数碰撞无声无息,湮灭于尘埃。 但对我来说,有一个“粒子”的出现,却像在暗物质区引爆了超新星,照亮了我几乎只有公式和数据的轨道图。 她叫苏晓。
我坐在前排,啃着哈密顿原理,皱着眉头在笔记上划拉着拉格朗日量,像在和宇宙真理较劲。 教室里嗡嗡的,大部分人在摸鱼、走神。 首到教授抛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关于非完整约束下的运动积分。 教室里一片死寂,连空气都冻住了。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正要举手。 一个清亮的声音就从我右后方响了起来。 那声音不高,但清晰得像冰玉相击,把我脑海中高速运转的计算噪音都给盖了下去。 “教授,我觉得可以用罗斯方程来处理这个多体耦合约束的……”我猛地回头。 视线穿过好几排人,定格在她身上。 说实话,她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让人惊艳得挪不开视线的类型。 长长的黑发简单地扎着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鼻梁挺秀,但最大的亮点是那双眼睛。 清澈,专注,带着一种理科生特有的、洞穿表象的锐利感。 她微微皱着眉,一边说,一边在草稿纸上流畅地推演,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她在讨论罗斯方程。 用一口流利的专业术语,推导着耦合约束下的运动积分。 逻辑清晰得像一道完美的洛伦兹变换。 我像被什么击中了,愣在那里。 不是因为漂亮——虽然她确实耐看——而是因为那种深藏在专业表达背后的、对物理世界的纯粹好奇和掌控感。 那种感觉,和我自己在演算时获得的纯粹理性上的快感产生了共鸣,却又多了点什么…一种难以言喻的引力。 教授赞许地点头,她坐下,抿了抿嘴,低头继续演算。 我呆呆地把头转回来,笔记本上的哈密顿原理符号都模糊了。 那一刻,我觉得《理论力学》枯燥的公式背后,似乎也有了几何般奇妙的美感。 嗯,物理之美似乎有了具体的代言人。 后来我才知道,苏晓是隔壁信息学院的,但选修了我们系的课。 她物理学得极好,绝不是为了刷学分那种。 更重要的是,她和我不一样。 她是那种能将深奥理论讲得浅显易懂的人,像拥有一个能将粒子轨迹可视化的内部模型。 而我,只会埋头苦算,然后对着自己完美的推导过程自我感动。 很快我就体会到了这种“不一样”带来的冲击。 一次《量子力学》的小组作业讨论,我和她分到了一组。 课题是“隧穿效应在超晶格中的反常行为”。 我提前准备好了一大堆模型和计算,憋着劲想露一手。 然而小组一碰头,我这个理论自嗨王者就露了怯。 我习惯性地一头扎进薛定谔方程的推导细节里,把小组其他几个物理没那么精深的同学听得云里雾里,眼神飘忽。 我浑然不觉,还在试图解释多粒子势垒穿透的概率密度矩阵…就在这时,苏晓轻轻敲了敲桌子:“林默,能暂停一下吗?” 我像卡壳的录音机,停住了。 她微笑着,眼神扫过有点懵圈的同学,说:“我们可以不用急着陷入方程。 从最首观的物理图像开始。 想象一下,电子像一道概率波的溪流,面对一堵能量墙…”她拿起笔,在一张废纸上画了一条起伏的线代表势垒,又画了一些小波浪代表波函数。 “这些能量墙很薄,在某些特殊的材料结构(超晶格)里,波虽然能量不足,却可以像穿山隧道一样,以可观测的概率‘渗’过去,这就是隧穿。 而我们要研究的‘反常行为’,就发生在波隧穿这种特殊材料结构时,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的,嗯…怎么形容呢? 一种‘不走寻常路’的震荡?” 她画了几个更复杂的波峰波谷叠加图。 “哦!” “原来是这样!” 几个同学恍然大悟,甚至有人笑出声。 我看着她那张涂鸦似的纸和她脸上那种干净明亮的神情,再对比我那堆精密却让人望而生畏的推导草稿,第一次对自己的“强”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她不动声色地解了我的围,把讨论引向了大家都能理解的轨道。 而且,她画的那些潦草的波浪线,竟然异常精妙地展示了那个复杂体系里波函数相位叠加的关键点。 自那次之后,我就有点…怕和她讨论。 总觉得在她面前,我像个扛着沉重真理大锤的莽夫,而她却是那个能用丝线精准操纵蝴蝶的操偶师。 怕归怕,靠近的冲动却像被施了魔法的行星轨道,无法抵抗地向“太阳”偏移。 我成了小组讨论里最沉默又最专注的存在,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黏在她身上。 看她眉头微蹙思考的样子,看她讲到关键处眼中闪烁的光(那种光,比光电效应产生的光电子还要动人),看她手指翻书时指关节透出的淡粉色…我甚至记住了她总用的那款蓝黑色中性笔的牌子。 有一次,我们在物理系那个巨大的、堆满了过期期刊的图书馆里查资料,一起熬到闭馆。 外面的暴雨敲打着老旧的玻璃窗。 我们各自抱着一摞厚厚的书准备走人。 我的那摞明显高得多,摇摇欲坠。 我刚想调整姿势硬扛,她忽然伸过手来,毫不费力地从我快要崩塌的书塔顶端抽走了最厚的那本《凝聚态物理中的拓扑效应》。 “你抱那几本电动力学就好,这本重的我来。” 她语气平常得像在讨论一道习题答案。 雨点打在屋顶的嘈杂声里,她清亮的声音却穿透过来。 我抱着剩下的书,手臂忽然空了一大截,心却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 那本书的分量仿佛转移到了我的胸口。 窗外的路灯透过湿漉漉的玻璃,在她头发上晕开了一圈模糊的光晕。 我清晰地闻到了她头发上很淡很淡的,像是雨前青草混着柠檬皮的味道,或者只是图书馆老木头和纸张散发的陈旧气味? 我分不清了。 我张了张嘴,喉结滚动。 脑子里瞬间闪过薛定谔方程的各种解,甚至冒出用玻恩-卡曼边界条件来推算心跳频率这种荒谬念头。 最终的结果是,在我那发达的、能处理超复杂张量微积分的大脑皮层下达指令之前,我的发声系统果断死机。 我只发出了一个模糊的音节,大概是“呃…好”。 然后像机器人一样,僵硬地转身,抱着我怀里的书一头扎进雨里,甚至忘了该把她送到宿舍楼下。 她一定觉得我很奇怪。 或者,根本就懒得去想。 这就是我大学期间和苏晓最接近的距离。 能一起讨论艰深的课题,能看她那双专注的眼睛,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呼吸同一片混合着灰尘、油墨和她发梢淡淡气息的空气,就足以让我那被物理挤得满满当当的心脏,泛起一圈又一圈奇怪的涟漪。 那涟漪扩散开去,公式的骨架仿佛都柔和了边界。 我用尽全身力气,也仅限于此。 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生怕这小心翼翼的平衡会被打破,让她眼中那种纯粹的、对物理的好奇光芒,掺杂上哪怕一丝对我本人笨拙无措的困惑或嘲笑。 我把那份隐秘的、带着粒子自旋般微小悸动的引力,深深锁进了我那只有公式和模型的世界里,如同锁进薛定谔的盒子,不敢去观测它的结局。 她的存在,成了我单调物理宇宙里一个特别的常数。 一个我能感测到、甚至计算出其强度,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其波函数塌缩方向的奇异叠加态。 毕业的钟声像是强行轰开了那个盒子——她保研去了更高殿堂,而我,像一颗失去约束的粒子,被弹射出原有的轨道,独自坠向名为“社会现实”的、完全未知的低能态深渊。 西年物理赋予我的知识,解释不了苏晓带给我的那些混乱信号。 就像它同样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个能用理论预测遥远星系行为的“未来天文学家”,此刻连份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
精选图文
 慕黛傅竣小说无弹窗(慕黛傅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慕黛傅竣)慕黛傅竣最新章节列表(慕黛傅竣)
慕黛傅竣小说无弹窗(慕黛傅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慕黛傅竣)慕黛傅竣最新章节列表(慕黛傅竣) 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宋知宜陆远肆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最新章节列表(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
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宋知宜陆远肆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最新章节列表(宋知宜陆远肆小说:宋知宜陆远肆) 林枳陆云霄小说无弹窗(林枳陆云霄)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枳陆云霄)林枳陆云霄最新章节列表(林枳陆云霄)
林枳陆云霄小说无弹窗(林枳陆云霄)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枳陆云霄)林枳陆云霄最新章节列表(林枳陆云霄) 华蒹梁羽廷小说:华蒹梁羽廷(华蒹梁羽廷)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华蒹梁羽廷)华蒹梁羽廷小说:华蒹梁羽廷最新章节列表(华蒹梁羽廷)
华蒹梁羽廷小说:华蒹梁羽廷(华蒹梁羽廷)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华蒹梁羽廷)华蒹梁羽廷小说:华蒹梁羽廷最新章节列表(华蒹梁羽廷) 宋芷依陆白屿(宋芷依陆白屿小说)全文免费宋芷依陆白屿读无弹窗大结局_(宋芷依陆白屿宋芷依陆白屿小说免费宋芷依陆白屿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宋芷依陆白屿)
宋芷依陆白屿(宋芷依陆白屿小说)全文免费宋芷依陆白屿读无弹窗大结局_(宋芷依陆白屿宋芷依陆白屿小说免费宋芷依陆白屿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宋芷依陆白屿) 薛丹珍邹墨寒全文(薛丹珍邹墨寒)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薛丹珍邹墨寒)薛丹珍邹墨寒最新章节列表(薛丹珍邹墨寒)
薛丹珍邹墨寒全文(薛丹珍邹墨寒)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薛丹珍邹墨寒)薛丹珍邹墨寒最新章节列表(薛丹珍邹墨寒) 这一场她自以为是的坚持,到此也该结束了:沈怀宁裴湛(沈怀宁裴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这一场她自以为是的坚持,到此也该结束了:沈怀宁裴湛最新章节列表(沈怀宁裴湛)
这一场她自以为是的坚持,到此也该结束了:沈怀宁裴湛(沈怀宁裴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这一场她自以为是的坚持,到此也该结束了:沈怀宁裴湛最新章节列表(沈怀宁裴湛) 纪清妩程明川小说:纪清妩程明川:最新章节(纪清妩程明川)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纪清妩程明川免费阅读(纪清妩程明川小说:纪清妩程明川)
纪清妩程明川小说:纪清妩程明川:最新章节(纪清妩程明川)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纪清妩程明川免费阅读(纪清妩程明川小说:纪清妩程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