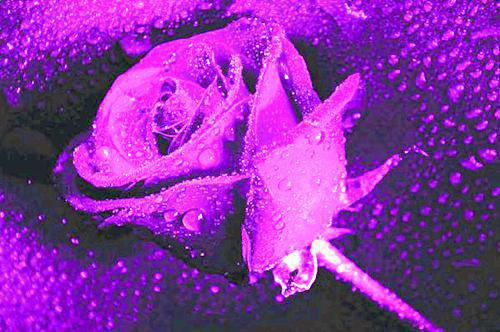一束麦芒,映两世暖阳李默丫丫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一束麦芒,映两世暖阳》精彩小说
|
1 寒夜的句号与异世的枷锁出租屋的窗户蒙着两层灰,冬夜的月光像被揉碎的碎银,勉强在玻璃上晕开一点冷光,却连窗台那盆枯了半载的绿萝都照不亮。 李默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椅上,指节因为用力捏着安眠药瓶泛出青白,瓶身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滑,标签上的 “安眠药” 三个字晕成一片模糊的白,像他三十三年人生里所有看不清的希望。桌角堆着三天前的泡面盒,汤汁顺着桌腿淌到地上,在水泥缝里凝成深褐色的印子,涸后硬得像一道道结痂的伤口 —— 这就是他的人生注脚:孤儿院的铁栏杆拦过他的童年,初中辍学后,工地的水泥灰、餐馆的油烟、流水线的轰鸣声,把他的力气榨成了褶皱的零钞,却没换来半分安稳。“活着到底图什么?”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低语,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裹着化不开的疲惫。昨天工地老板卷款跑路时,他追了三条街,寒风灌进喉咙像吞了冰碴,最后只抓住满手冰凉的空气;今早房东摔门催租的声音还在耳边炸响,“再交不出钱,就把你那堆破行李扔去巷口喂狗!” 他摸了摸口袋,只剩三个皱巴巴的硬币,指尖捏着硬币边缘的棱角,连买瓶最便宜的白酒麻痹自己都不够。瓶塞 “啵” 地弹开,白色药片滚落在掌心,像撒了一把刚落的碎雪,凉得刺手。他仰头就要吞下去,突然一阵天旋地转,胸口像被巨石压住,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仿佛五脏六腑都被搅成了一团。耳边炸开嘈杂的嘶吼,有鞭子抽在皮肉上的脆响,像枯树枝被折断;有女人压抑的哭嚎,混着绝望的抽气声;还有人在喊 “打死这个敢顶嘴的奴隶”—— 再睁眼时,他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左手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伤口的血把粗麻布染成黑红色,黏在皮肤上,冷得像冰。“还敢装死?” 一只沾着泥的靴子踩在他的背上,力道重得要把他的肋骨踩断。李默疼得眼前发黑,生理性的泪水涌了上来,模糊中看见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手里甩着牛皮鞭,鞭梢上还挂着几缕血丝,像极了他小时候在屠宰场见过的、沾着猪毛的刀。周围站着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个个面黄肌瘦,颧骨高高凸起,眼神空洞得像枯井,没人敢抬头看他,连呼吸都放得极轻,仿佛多说一句话都会招来灾祸。“奴隶……” 李默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飞。他曾在工棚里看过几本穿越小说,以为穿越是解脱,是金手指、富贵命,是摆脱这烂透人生的捷径,可没想到,自己掉进了更黑的深渊。 现代的苦是穷,是累,可至少他能走在阳光下,能决定今天吃泡面还是啃馒头,能在出租屋里蜷着睡够八个小时;可现在,他连自己的命都不属于自己,左手断了,浑身是伤,像条被丢弃在寒冬里的野狗,连哀嚎的资格都没有。鞭子又抽了过来,落在他的胳膊上,火辣辣的疼直往骨头里钻,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给老子起来! 周老爷的麦子还等着收割,你要是敢耽误,直接拖去喂狗!” 男人的吼声震得他耳膜疼,震得他脑子里的嗡嗡声更响了。李默想反抗,可身体软得像没骨头,刚撑起身就重重摔下去,左手的剧痛让他忍不住闷哼出声,那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却还是被男人听了去。“废物! ” 男人啐了一口,唾沫星子溅在他的脸上,又要挥鞭。这时,有人扯了扯他的裤脚,力道轻得像片羽毛。李默偏过头,看见个小女孩,看着只有七八岁,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裙,领口磨得发亮,头发剪得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脸上抹着厚厚的泥,大概是怕被人认出,只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浸在水里的星星,此刻正怯生生地仰着头:“张管事,他…… 他快不行了,我替他去割麦子好不好?
我割得快,不耽误事,我昨天还多割了一垄呢。”张管事瞪了她一眼,抬脚把她踹得坐在地上,泥溅了她一身。“丫丫你个小贱种,也敢替主子做主?再多嘴,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他的声音里满是恶意,像毒蛇吐信。丫丫爬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泥,动作轻得像怕弄坏什么宝贝,却还是固执地挡在李默面前,小小的身子绷得笔直,像棵倔强的小草:“我不嘴碎,我多割两垄,补上他的份,您别打他了,他的手…… 都断了。”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一股不肯退让的劲儿。 “滚!” 张管事不耐烦地挥挥手,“赶紧把他拖回奴隶房,要是死了,你也别想活! ”丫丫连忙点头,小步跑到李默身边,吃力地扶起他。她的胳膊细得像麻杆,李默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胳膊上突出的骨头,可她却用尽全身力气架着他的胳膊,一步一步往远处的土坯房挪。李默垂着头,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霉味,还有泥土的腥气,可不知为什么,这味道竟比出租屋的泡面味还让他心安些 —— 至少此刻,有人没把他当成随时能丢弃的垃圾,有人愿意伸出手,拉他一把。 奴隶房在庄园最偏僻的角落,四壁漏风,风灌进来时 “呜呜” 地响,像鬼哭;屋顶的茅草稀得能看见天,晚上躺着就能数星星,前提是没被冻僵。 里面挤着十几个奴隶,都躺在铺着干草的地上,有的断了腿,裤管空荡荡的;有的瞎了眼,脸上蒙着块破布,没人说话,只有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像破旧的风箱在拉。 丫丫把李默扶到最里面的角落,那里铺着一层稍微厚点的干草,还带着点体温,应该是她平时睡的地方。“爹,你躺好,我给你找草药。” 丫丫说着,从草堆里翻出个破布包,布包上缝着好几块补丁,里面裹着些晒干的野草,叶片上还沾着泥,却被叠得整整齐齐。李默愣了愣,才反应过来 “爹” 是在叫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大概就是这女孩的父亲。可他不是,他只是个外来者,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逃兵,一个在现代社会活不下去、想靠安眠药结束生命的懦夫。“我不是你爹。” 他声音很轻,却带着拒人千里的冷漠,他怕自己给不了她任何希望,怕自己这副样子,连她最后一点温暖都会夺走。丫丫的手顿了顿,眼里的光暗了暗,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可她还是把草药放在石头上捣烂,动作轻得像在处理什么易碎品,然后小心翼翼地敷在他的左手伤口上:“爹,我知道你疼,你别生气。 上次你替我挡了周老爷的鞭子,才被打断手的,我…… 我知道你难受,可你别不要我。 ”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带着哭腔,像羽毛轻轻挠在李默的心上。李默没再说话。 他闭上眼,满脑子都是现代的绝望和眼前的痛苦。左手的疼、背上的疼、心里的疼,像无数根针在扎他,扎得他连呼吸都觉得费力。他想,要是刚才那鞭子直接把他打死就好了,至少不用再受这份罪,不用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不用面对这个把他当成父亲的小女孩 —— 他不配。丫丫敷完药,又从怀里掏出个黑乎乎的窝头,窝头硬得像石头,边缘都发了霉,还带着股酸味。 她递到李默嘴边,眼神里满是期待:“爹,你吃点吧,这是我昨天省下来的。 你要是不吃东西,身体好不了,身体不好,就不能…… 就不能陪我了。”李默偏过头,没接。他现在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啃下这么硬的窝头。死意像潮水般涌上来,比在出租屋时更汹涌 —— 在这里,连死都是种奢望,可他还是想试试,想彻底摆脱这无边无际的痛苦。丫丫见他不吃,也不勉强。她坐在旁边,把窝头放在他手边,然后安静地搓着草绳,手指被草绳勒出了红印。奴隶房里很静,只有外面偶尔传来的鞭子声和嘶吼声。李默能感觉到丫丫的目光时不时落在他身上,那目光里没有怨怼,只有担忧,像极了小时候孤儿院阿姨看他的眼神 —— 那时候阿姨会摸他的头,说 “李默要好好长大”,可那眼神早就随着他初中辍学、离开孤儿院消失了,再也没人那样看过他。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天彻底黑了。张管事的吼声渐渐远了,奴隶房里的人也都睡着了,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咳嗽声。李默还是没睡着,他盯着漏风的屋顶,脑子里反复想着怎么死才痛快。是趁夜里跑出去跳进井里? 井水应该很冷,说不定很快就能失去意识;还是明天故意惹怒张管事,让他一鞭子把自己打死?那样至少能少受点折磨。就在他想得入神时,感觉有人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力道轻得像片叶子落在身上。是丫丫,她把自己的薄被子盖在了他身上,被子上满是补丁,还带着股淡淡的霉味,却很暖和。 然后她蜷缩在他旁边,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小声说:“爹,夜里冷,你盖着被子,别冻着了。我不冷,我火力壮,小时候阿姨说我是小火炉呢。”被子上带着丫丫的体温,还有股淡淡的皂角味 —— 大概是她偷偷在河边洗过,用了最省皂角的方式。 李默的心猛地颤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撞得他鼻子发酸。在现代,他从来没被人这么惦记过:工地老板只会催他干活,房东只会催他交租,连一起住过的工友,也只是偶尔一起吃碗泡面,从没人会把仅有的被子让给他,没人会怕他冻着。在这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却把她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他睁开眼,借着微弱的月光,看见丫丫蜷缩成一团,小小的身子在发抖,牙齿都在轻轻打颤,却还在强撑着,怕他担心。 死意似乎被这一丝温暖冲淡了些,可也只是一丝而已。他想,明天醒来,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该受的苦还是要受。或许,再等等,等他攒够了勇气,就彻底解脱 —— 只是,他有点舍不得这床带着体温的被子,舍不得这个怕他冻着的小女孩。2 窒息的白昼与微弱的光天还没亮,奴隶房的门就被一脚踹开,“哐当” 一声巨响,吓得所有人都一哆嗦。张管事拿着鞭子,在屋里狠狠抽了一下,鞭子抽在地上,溅起几片干草,他嘶吼道:“都给老子起来! 赶紧去割麦子!谁要是敢偷懒,今天就别想吃饭!”奴隶们像受惊的兔子,连忙爬起来,有的连鞋子都顾不上穿,光着脚就往外跑,生怕慢一步就挨鞭子。李默也被惊醒了,他想爬起来,可左手一用力,就疼得钻心,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的粗麻布。 丫丫已经穿好了衣服,她动作麻利地帮李默理了理衣襟,然后扶着他的胳膊,小声说:“爹,你慢点,我扶着你,别着急。”李默没说话,任由丫丫扶着他往外走。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像被一块脏抹布盖着,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疼得厉害,刮得耳朵都失去了知觉。 田地里已经站满了奴隶,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镰刀,低着头,机械地割着麦子,动作整齐得像木偶。周老爷站在田埂上,穿着厚厚的棉袄,领口还围着狐裘,手里拿着个暖炉,时不时呵斥几句干活慢的奴隶,声音里满是不屑。“快点!都给老子快点! ” 张管事的鞭子在人群里甩来甩去,时不时落在某个奴隶的背上,留下一道鲜红的血痕,血珠渗出来,很快又被寒风冻住。“今天要是割不完这片麦子,你们都别想睡觉! 周老爷说了,谁耽误了进度,就卸谁的胳膊!”李默拿着镰刀,艰难地弯下腰。 他的左手不能用力,只能用右手一点一点地割麦子,速度比其他人慢了一大截。镰刀很钝,割麦子时要费很大的劲,没过多久,他的后背就被汗水浸湿了,冷风一吹,冻得他直打哆嗦,牙齿不停地打颤。“你他妈能不能快点?” 张管事注意到了他,拿着鞭子走了过来,一鞭子抽在他的背上,疼得他浑身一颤,镰刀差点掉在地上。“周老爷花钱买你们来,是让你们干活的,不是让你们来偷懒的!你以为你是谁?还敢磨磨蹭蹭! ”李默疼得眼前发黑,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他想抬头反驳,想说 “我的手断了”,可看到张管事眼里的凶光,那目光像要把他生吞活剥,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在这里,奴隶没有反驳的权利,只有服从,反抗只会招来更重的打骂,他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丫丫在旁边看到了,连忙加快速度,她的小手紧紧握着镰刀,因为用力,指节都泛了白。 她把自己割的麦子往李默这边挪了挪,小声说:“爹,我帮你割,你慢点,别累着了,你的手还没好呢。”李默看着丫丫小小的身影,心里一阵发酸,酸得他眼睛都红了。 她这么小,本该是在爹娘怀里撒娇的年纪,本该是拿着糖葫芦在街上跑的年纪,却要在这里干这么重的活,还要担心他这个 “冒牌爹”。可他还是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加快了手里的速度。他不想欠这个小女孩太多,他们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他怕自己还不起,怕自己最后还是会丢下她。太阳慢慢升起来了,温度却没怎么升高,阳光照在身上,像隔着一层冰,没有丝毫暖意。田地里的麦子一望无际,黄灿灿的一片,却像一座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山。割了一上午,才割了一小片,李默的腰早就酸得直不起来了,每弯一次腰,都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奴隶们连口水都没喝上,张管事还在不停地催促:“快点!都给老子快点!中午只有半个窝头,谁要是干活慢,连窝头都别想吃!”李默的肚子早就饿了,昨天晚上就没吃东西,现在更是饿得发慌,胃里 “咕噜咕噜” 地叫,像有只小猫在抓。他感觉自己的力气越来越少,手里的镰刀也越来越重,重得像灌了铅。他想停下来歇一会儿,哪怕只歇一分钟,可一想到张管事的鞭子,想到那半个可能吃不上的窝头,还是咬着牙坚持着 —— 他不能饿肚子,饿肚子就没力气干活,没力气干活就会挨鞭子,他已经受够了疼痛。中午的时候,张管事终于喊了停。奴隶们排着队,每个人领了半个黑乎乎的窝头,窝头硬得能硌掉牙,还带着股酸味。丫丫领了窝头,连忙跑到李默身边,把自己的窝头递给他,眼神里满是急切:“爹,你吃我的,我不饿,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偷偷吃了点野菜。”“我不吃,你自己吃。” 李默把窝头推了回去。 他知道,丫丫也饿了,这半个窝头可能是她一天的口粮,她早上根本没吃什么野菜,他昨晚亲眼看到她把仅有的一点野菜煮了水,还想分给他喝。丫丫却把窝头又塞回了他手里,小手紧紧地攥着他的手,生怕他再推回去:“爹,你一定要吃,你要是饿坏了,下午就没力气干活了,没力气干活就会挨鞭子,我不想看你挨鞭子。我真的不饿,我还能挺住。”李默看着丫丫真诚的眼神,那眼神里满是担忧,像清澈的泉水,洗着他心里的污垢。他心里的防线似乎松动了些,像被阳光照化的冰雪。他接过窝头,咬了一口,硬得硌牙,还带着股酸味,可他却觉得这是他穿越过来后吃的最好吃的东西 —— 因为这窝头里,裹着一个小女孩的心意,裹着他许久没感受到的温暖。下午的太阳更毒了,虽然是冬天,可阳光晒在身上还是火辣辣的,晒得皮肤生疼。奴隶们的速度越来越慢,每个人都像被抽走了魂魄,只剩下机械的动作。张管事的鞭子也抽得越来越频繁,每一次鞭子落下,都伴随着一声压抑的痛呼。李默的后背已经被鞭子抽了好几下,旧伤叠新伤,血渗出来,把粗麻布都染红了,疼得他直冒冷汗,每动一下,都牵扯着伤口,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眼前开始发黑,耳朵里也嗡嗡作响,死意又一次涌了上来 —— 倒下去吧,倒下去就不用再受这份罪了,倒下去就能彻底解脱了。他甚至开始故意放慢速度,手指松了松,镰刀割麦子的动作越来越慢,他想让张管事注意到他,想让张管事的鞭子把自己打死,这样至少能少受点折磨。就在这时,“哎哟” 一声轻呼传来。李默心里一紧,猛地抬头,看见丫丫摔倒在地上,手里的镰刀掉在旁边,割破了她的裤子,腿上流出了血,鲜红的血珠滴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格外刺眼。李默几乎是下意识地跑了过去,蹲下身扶起她,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你怎么样?疼不疼?”这是他穿越过来后,第一次主动关心丫丫。丫丫愣了愣,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没想到他会这么问,然后摇了摇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的疼却藏不住:“爹,我没事,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你别担心,我还能干活,不会耽误进度的。”李默看着她腿上的伤口,血还在流,顺着小腿往下淌,染红了她的裤脚。他心里一阵疼,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疼得他呼吸都变得急促。他从怀里掏出丫丫早上给他的草药 —— 早上他没舍得用,想留着给她应急,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他小心翼翼地把草药敷在她的伤口上,动作轻得像在处理易碎的珍宝:“别干了,歇一会儿,伤口得处理好,不然会发炎的。 ”“不行,要是被张管事看到了,会打你的。” 丫丫说着,就要站起来,可刚一用力,腿就疼得她皱起了眉。李默按住她的肩膀,力道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没事,有我呢。我替你干活,不会耽误进度的,张管事不会说什么的。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或许是看到丫丫受伤时的慌乱,或许是这几天丫丫的关心像温水一样,慢慢融化了他心里的冰。他只知道,他不能让这个小女孩再受伤害,不能让她因为自己而挨鞭子。张管事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拿着鞭子快步走了过来,脸上满是怒气:“你们在干什么?还敢偷懒?是不是想挨鞭子了? ”李默站起来,挡在丫丫面前,像一堵小小的墙。他的后背还在疼,左手也隐隐作痛,可他却挺直了腰板,看着张管事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她受伤了,腿流血了,不能干活。 我替她干活,她的活我一起干,不耽误今天的进度,你别打她。”张管事愣了愣,大概没想到这个一直死气沉沉、连头都不敢抬的奴隶会主动说话,还敢跟他讨价还价。 他打量了李默一眼,又看了看地上的丫丫,眼神里满是怀疑,可最后还是冷哼一声:“算你识相。要是耽误了进度,我连你一起打,到时候可别喊疼! ” 说完,便转身走了,鞭子甩在手里,发出 “啪啪” 的声响。李默松了口气,后背的汗湿得更厉害了,刚才跟张管事说话时,他的心跳得飞快,生怕张管事不同意,还要打丫丫。他扶着丫丫坐在田埂上,又把自己的粗麻布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腿上,挡住伤口:“你在这里歇着,别乱动,我去干活,很快就好。”丫丫看着李默的背影,他的后背满是鞭痕,粗麻布被血染红了一大片,可他却还是拿着镰刀,弯着腰,一点一点地割着麦子。丫丫的眼里泛起了泪光,她知道,爹好像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什么都不在乎了。爹开始关心她,开始保护她了,就像真正的爹一样。 李默拿着镰刀,重新回到田里。他的力气还是很少,每割一刀都要费很大的劲,后背的伤口疼得他直冒冷汗,可他却觉得心里有了一丝支撑,像在黑暗里找到了一根蜡烛。 他想,至少现在,他不能死,他还要照顾这个小女孩,他不能让她一个人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活着,不能让她再受欺负。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可在这个世界里,她是唯一给过他温暖的人,是唯一把他当成亲人的人。夕阳西下的时候,麦子终于割完了。金色的阳光洒在田地里,把麦子的秸秆染成了金黄色。 奴隶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慢地往奴隶房走,每个人都像散了架一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
精选图文
 祝纾妍魏子宸(祝纾妍魏子宸)全文免费祝纾妍魏子宸读无弹窗大结局_ 祝纾妍魏子宸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
祝纾妍魏子宸(祝纾妍魏子宸)全文免费祝纾妍魏子宸读无弹窗大结局_ 祝纾妍魏子宸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 祝纾妍魏子宸小说(祝纾妍魏子宸)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祝纾妍魏子宸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祝纾妍魏子宸)
祝纾妍魏子宸小说(祝纾妍魏子宸)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祝纾妍魏子宸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祝纾妍魏子宸) 闻总快追,楼秘书身价三千亿(楼藏月闻延舟)免费小说-楼藏月闻延舟全文阅读目录
闻总快追,楼秘书身价三千亿(楼藏月闻延舟)免费小说-楼藏月闻延舟全文阅读目录 闻总快追,楼秘书身价三千亿正版小说最新章节在线阅读-小说楼藏月闻延舟闻总快追,楼秘书身价三千亿已完结全集大结局
闻总快追,楼秘书身价三千亿正版小说最新章节在线阅读-小说楼藏月闻延舟闻总快追,楼秘书身价三千亿已完结全集大结局 高质量惊!权贵大佬们都在等着她休夫小说推荐 沈时好李屿恒全文阅读(完整版)
高质量惊!权贵大佬们都在等着她休夫小说推荐 沈时好李屿恒全文阅读(完整版) 精选好书桑泞岑衍深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_桑泞岑衍深(桑泞岑衍深)完整版在线赏析
精选好书桑泞岑衍深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_桑泞岑衍深(桑泞岑衍深)完整版在线赏析 傅子理夏诗染夏诗染傅子理(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傅子理夏诗染夏诗染傅子理(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苏婉容陆远亭后续免费阅读全文全文小说免费_苏婉容陆远亭精彩阅读
苏婉容陆远亭后续免费阅读全文全文小说免费_苏婉容陆远亭精彩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