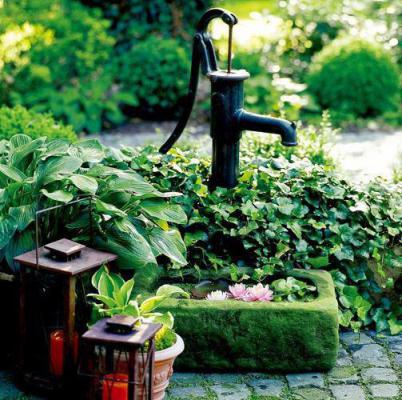父母卷款润国外,十年后我拒养外国公民(欠条冰冷)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父母卷款润国外,十年后我拒养外国公民(欠条冰冷)
|
十年前他们用我的大学学费换了两张单程机票,在登机口扔给我一只塞满欠条的破书包,养老?等我们在自由国度成功了,你别来沾光!十年间我睡过天桥捡过垃圾,却始终留着那只书包。如今他们拖着病体归来,在记者镜头前哭诉中国子女不孝。 我默默打开书包,将欠条雪花般撒向空中:二位外国公民,请先偿还这3650顿百家饭。 1窗外的北风像野狗一样啃咬着烂尾楼裸露的水泥边沿,发出呜呜的哀嚎。 屋里能冻僵骨头缝的寒气,和门外那两道被楼道昏黄灯光拉得忽长忽短、喋喋不休的影子,是同时抵达的。我正对着桌上那碗清可见底的稀饭,手里半块干硬的馒头刚咬了一口,噎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十年了啊!十年!我们含辛茹苦,在外国打拼,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现在回来了,孩子居然连门都不让进!这还有天理吗?”女人的声音,刻意拔高,带着一种被生活碾碎后又强行拼接起来的沙哑,穿透薄薄的铁门板。 这声音有一种奇异的陌生,却又蛮横地撬动着记忆深处某些早已锈死的角落。“记者同志,你们给评评理!天下哪有这样的子女?我们生他养他,老了病了,求他给口饭吃,求他带我们看看病,这不过分吧?他的心是铁打的啊!”男人的声音跟随着,更沉,更苦情,像浸透了陈年的油污,黏腻地糊在门板上。摄像机的镜头大概正对准他们,记录下这“悲情”的一幕,冰冷的机器运转声是这出催泪大戏的最佳配乐。几声压抑的抽噎,配合着敲门声,一下,又一下,不重,却精准地敲打在这间破屋和它主人的脊梁骨上。
邻居的议论像潮湿角落里滋生的霉菌,窸窸窣窣地蔓延。“真不认了? 好歹是爹妈……”“看着是怪可怜的,病怏怏的……”“十年没见,一回来就闹这么大……”我放下馒头。那口噎着的碎屑剌得喉咙生疼。 胃里那点可怜的稀饭开始翻腾,泛着酸水。十年。整整十年。冰冷的恨意像毒蛇的信子,悄无声息地舔舐着胸腔内壁。可奇怪的是,竟没有想象中的暴怒或撕裂般的痛苦,只是一种巨大的、近乎麻木的空洞。那空洞里,回荡着十年前机场广播冰冷机械的登机提示,回荡着那只塞得鼓鼓囊囊、猝然塞进我怀里的破书包粗糙的触感,回荡着那句随着高跟鞋和皮鞋声远去、斩断一切后路的冷笑——养老? 等我们在自由国度成功了,你别来沾光!记忆的闸门被这拙劣的哭诉悍然冲开,带着机场特有的消毒水和焦虑气味,汹涌而至。那一年,我刚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烫金的字体映着一家三口最后那点虚假的荣光。家里的气氛已经不对很久了,某种隐秘的、躁动的兴奋感在他们之间流动,唯独将我排除在外。他们频繁地窃窃私语,深夜接听国际长途,家里那些稍微值钱的字画、瓷器悄无声息地消失。直到那个清晨,他们起得出奇的早,衣冠楚楚,两个簇新的行李箱立在客厅中央,像两座沉默的墓碑,祭奠着我即将死亡的世界。“小默,”母亲脸上堆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璀璨的笑,弧度完美却冰冷,“爸爸妈妈要出一趟远门,很长很长的远门。 去一个真正自由的、能实现我们人生价值的地方。”父亲在一旁,不耐烦地瞥着腕表,接口道:“家里以后就靠你自己了。你是大人了。”我的心跳骤然失序,一股冰冷的恐慌攥紧喉咙:“远门?去哪里?我的学费……下个月就要交了……”“学费? ”母亲像是听到了一个极其可笑又微不足道的词,她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短促的笑,弯腰,从沙发底下拖出一只磨破了边的旧帆布书包,粗暴地塞进我怀里,“喏,你的学费,还有我们的生活费,全在这里面了。省着点花。”那书包沉得惊人,一股劣质帆布和灰尘的味道冲入鼻腔。我下意识地拉开拉链——里面没有一分钱。 只有密密麻麻、叠得乱七八糟的纸。我抽出一张,是欠条。再抽出一张,还是。粮油店的,房东的,水电公司的,甚至还有邻居张奶奶的……每一张都按着鲜红的手印,写着触目惊心的金额和还款日期。我的血液瞬间冻成了冰碴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机场广播在催促他们的航班最后一次登机。 父亲一把抓过行李箱的拉杆,眼神里没有丝毫温度,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奔向新世界的决绝:“意思就是,我们自由了。这些债务,就当你提前尽孝了。”母亲最后拍了拍我的脸,指尖冰凉:“记住,等我们在那边站稳脚跟,成功了,发达了,你千万别来沾光。我们会有全新的、配得上我们的高级生活。 至于这些……”她嫌恶地瞥了一眼那包欠条,“这些过去的耻辱,你自己处理干净。”说完,他们决绝地转身,高跟鞋和皮鞋敲打着光洁的地砖,清脆,急促,没有丝毫留恋,汇入安检口涌动的人流,消失不见。没有回头。一次都没有。 我抱着那只塞满了“耻辱”和巨额债务的破书包,像一棵被雷劈焦的树,孤零零地杵在喧嚣的机场。周围是重逢的欢笑、离别的泪水、奔向各自目的的匆忙脚步。 世界如此巨大,却没有任何一个方向,告诉我该去哪里。 那两张用我的大学学费、我的未来、我这个儿子换来的单程机票,带着他们飞向了理想的自由国度。2而我,一个刚刚成年的“书香门第”之后,抱着一书包的欠条,站在人潮里,瞬间成了孤儿。“开门啊!儿子!我是妈妈! 你开门看看妈妈啊!”门外的哭嚎将我从冰冷的回忆里拽出,那声音变得尖厉,开始用力拍打门板,哐哐作响,“你真要眼睁睁看我们死在外面吗?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孝道呢!良心呢!”邻居的议论声变大了,掺杂着劝解。 “小默,要不先开开门?总得说清楚……”“是啊,这大冷天的,老人家身体看着不行了……”我缓缓站起身。四肢百骸像是生了锈,每动一下都发出艰涩的呻吟。胃里的酸水翻涌得更厉害,那十年里无数个饥寒交迫的日夜,化作冰冷的重量,沉甸甸地坠在脚下。我走到门边,没有立刻开门。目光落在墙角。 那只破旧的帆布书包,静静地躺在那里,蒙着厚厚的灰尘。十年了。我睡过天桥洞,挤过漏风的工棚,捡过别人扔掉的剩饭,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餐馆后厨洗过堆积如山的油污碗碟……我扔掉了几乎所有从那个“家”带出来的东西,唯独它,像一道丑陋的疮疤,像一具刻满诅咒的枷锁,我一直留着。 不知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自虐般的恨意,或许只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如何被抛弃,如何从“书香门第”的幻象里,一头栽进这泥泞污糟的现实。门外,记者似乎在进行现场播报,语气凝重,强调着“赡养老人是传统美德,亦是法律义务”。 我父母,不,那对外国公民的哭泣声愈发凄惨悲切,仿佛承受了全世界最深的委屈。我弯腰,捡起那只书包。灰尘扑簌簌地落下,呛入肺管。拉链有些卡顿,我用力一扯——“刺啦——”一声钝响,仿佛撕裂了十年时光糊上的封条。里面,是密密麻麻、泛黄发脆、字迹却依然清晰的欠条。它们拥挤着,散发着陈旧的纸张和绝望的气息。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混杂着灰尘和门外表演气息的空气,猛地拉开了门。“吱呀——”老旧的合页发出刺耳的呻吟。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 所有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摄像机镜头黑洞洞地对准我,闪着无情的红光。楼道里挤满了人,邻居,看热闹的陌生人,以及被围在正中央的——那两个人。十年光阴是一把残酷的刻刀。 记忆中那个总是精致得体、带着几分文人清高和优越感的母亲,此刻裹在一件颜色俗艳、明显不合身的旧棉袄里,头发干枯灰白,脸上刻满了深重的皱纹和某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戾气与憔悴。曾经那双挑剔又明亮的眼睛,此刻浑浊不堪,写满了算计和疲惫,只有在我出现的瞬间,迸发出一种抓住救命稻草般的、贪婪的光。 旁边那个曾经身材挺拔、谈吐间总爱引经据典的父亲,佝偻得像一只被烤熟的虾米,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蜡黄,眼窝深陷,不住地咳嗽着,瘦得脱了形,依靠在一根破旧的拐杖上。他看到我,眼神躲闪了一下,随即被更浓的哀求和理直气壮覆盖。 他们身后,是两个脏兮兮的、瘪塌塌的行李袋,与当年那两只簇新的行李箱隔着十年的落魄两两相望。记者是一名年轻女子,话筒上的台标醒目,她立刻将话筒递到我面前,语气带着职业性的探究与轻微的谴责:“先生,您就是刘默吧? 您的父母声称您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请问情况是否属实? 您是否考虑到二老目前的健康状况……”母亲像是瞬间被注入了表演的能量,猛地扑上来,想要抓我的胳膊,被我侧身避开。她就势瘫坐在地上,拍打着地面,嚎啕起来:“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十年不见,心肠硬得像石头啊! 我们做父母的就算有千错万错,生养之恩大过天啊! 他现在一个人住着她显然把这破屋想象成了什么好地方,却让我们两个一身病的老人流落街头!天理何在啊!”父亲配合着剧烈咳嗽,咳得撕心裂肺,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小默……爸……爸知道对不起你……可爸真的要死了……你就忍心……”邻居们鸦雀无声,看着这场面,眼神复杂。摄像机贪婪地记录着这一切。我看着他们,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拙劣的马戏表演。胃里的那点稀饭终于彻底变成了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坠在腹腔里。喉咙里那口干馒头碎屑,剌得生疼。记者又把话筒往前递了递,语气加重:“刘先生,请您正面回应。根据我国法律,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您这样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也会受到社会的谴责。”3我缓缓抬起眼,目光掠过记者,掠过镜头,最终落在那两个表演得声泪俱下的“父母”身上。楼道里昏黄的灯光打在我脸上,probably毫无血色。我举起了手中那只破旧不堪、沾满灰尘的帆布书包。 所有人的目光,包括摄像机的镜头,都疑惑地聚焦在这只与此情此景格格不入的破包上。 母亲哭声一顿,父亲咳嗽也停了一瞬,眼里闪过一丝不解和莫名的不安。我没有说话,只是将手深深探入书包内袋,摸到了那厚厚一叠、冰冷粗糙的纸张。然后,猛地向外一扬——哗——仿佛一场压抑了十年之久的暴雪,骤然降临在这狭窄、肮脏的楼道里。无数张泛黄、破损、字迹不一的纸条,从破书包里倾泻而出,被门缝里钻出的冷风一吹,纷纷扬扬,旋转着,跳跃着,像无数只挣扎了十年终于获得自由的枯叶蝶,铺天盖地地洒落。 它们落在记者惊讶抬起的脸上,落在摄像机冰冷的镜头上,落在邻居们目瞪口呆的肩头,更多更多的,飘洒在那两个瘫坐在地、瞬间僵住的人身上,头上,脸上。一张欠条,正好盖在母亲大张着的、忘了哭嚎的嘴上。另一张,晃晃悠悠,贴在了父亲因惊愕而忘记咳嗽的额头。粮油店老王:今欠大米叁拾斤,食用油伍升,合计人民币伍佰元整。立据人:刘XX鲜红指印房东李阿姨:欠三个月房租,共计人民币肆仟伍佰元整。下月不交滚蛋!刘XX指印水电公司催缴单:欠费停机通知。 金额:柒佰叁拾贰元捌角。张奶奶:小默孩子可怜,借给孩子两百块钱吃饭。 刘家大人回来务必还来。张素芬。……密密麻麻。一张又一张。3650张。一顿饭一张。 一天一张。吃了整整十年。楼道里死寂无声。只有纸张飘落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以及窗外北风永无止境的呜咽。所有的表演,所有的哭诉,所有的质问和谴责,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沉默的“雪”面前,彻底失声。记者张着嘴,看着满天的纸条,职业性的冷静面具碎裂,露出完全的错愕。邻居们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些飘到眼前的具体数字和债主姓名,窃窃私语变成了倒抽冷气的声音,看向那两人的目光,从之前的同情怜悯,瞬间转变为震惊、鄙夷和愤怒。那两个人,我的父母,彻底懵了。他们坐在冰冷的、撒满欠条的地上,像是两尊突然被泼了满头满脸污秽的泥塑,僵硬,狼狈,难以置信。 母亲下意识地抓下贴在嘴上的那张纸,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手指剧烈地颤抖起来。父亲试图扯下额头那张,动作却僵在半空,浑浊的眼睛里,那点伪装的可怜和理直气壮被击得粉碎,只剩下巨大的恐慌和一种被当众剥皮抽筋的羞耻。 我站在门口,站在这一场由他们亲手写就的“雪”中,声音不大,却像冰锥一样,清晰地凿进这死寂的空气里,每一个字都冒着森森的寒气:“二位外国公民,”这个称呼让所有人一怔,包括他们。他们猛地抬头看我,眼神惊骇。我继续说着,目光死死钉在他们脸上:“请先偿还清这3650顿百家饭,”顿了顿,我加重了语气,吐出最后三个字:4“以及利息。”风卷起几张欠条,打着旋儿,贴在他们灰败的脸上,像是甩过去的耳光。母亲像是被这三个字烫伤了灵魂,猛地一个哆嗦,嘴唇嗫嚅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父亲试图拄着拐杖站起来,却踉跄一下,更深的佝偻下去,只剩下粗重破碎的喘息。那3650张纸片,每一张都是一个饥饿的夜晚,一个被嘲笑的白天,一双施舍的援手,一道刻在少年脊背上的伤疤。它们无声地飘落,覆盖了精心编排的哭诉,掩埋了虚伪的眼泪,将这十年不堪回首的重重时光,冰冷地、具象地,砸回给他们。记者手中的话筒缓缓垂了下去,摄像机镜头迟疑着,不再对准我,而是扫过满地狼藉的纸张,扫过邻居们愤慨的脸,最后定格在那两张煞白、惊恐、无处遁形的面孔上。楼道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窗外北风永恒的呜咽,像为一场迟来了十年的审判,奏着苍凉的背景乐。雪,还在下。 那场由欠条组成的、下了十年的雪,终于落回了它的源头。时间仿佛被这满天的纸片冻结了。 几秒钟的死寂之后,是轰然炸开的喧嚣。邻居们不再是窃窃私语,而是愤怒的指点和毫不避讳的议论。“我的老天爷!这么多欠条! 他们当年是把能借的都借遍了啊!”“看!那张是老王粮油店的!老王前年脑溢血走了,他老婆现在还在捡瓶子还债呢!”“还有李阿姨的房租!李阿姨心软,看孩子可怜没真赶他走,自己贴了多少年房贷!”“张奶奶那两百块!老太太临死前还念叨,说孩子要是过不下去,这钱就算了……他们居然!他们居然真干得出来! ”“卷了所有钱跑国外享受,把债全甩给刚成年的孩子?这还是人吗?!”“呸! 还有脸回来哭诉!还有脸要儿子养老!脸皮比城墙还厚!”镜头不再对准我,而是疯狂地捕捉着满地欠条的特写,捕捉着邻居们激愤的脸,最后死死锁定在那两个瘫坐在纸堆里、面无人色的人身上。 记者脸上的职业性同情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欺骗后的恼怒和强烈的新闻亢奋。 她几乎是抢过话筒,声音都变了调,不再是追问我,而是厉声质问那两人:“刘先生,王女士我随母姓,请你们解释一下!这些欠条是怎么回事?!你们十年前离开,并非所谓‘出国打拼’,而是卷款潜逃,并将巨额债务留给刚刚成年的儿子?! 请问你们在所谓的‘自由国度’享受生活时,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儿子在国内靠着百家饭和欠条活命?!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母亲像是被毒蜂蜇了,猛地弹了一下,手忙脚乱地想把身上的欠条拂开,仿佛那些纸片是烧红的烙铁。 她的哭嚎变成了神经质的、破碎的辩解,“是……是他!是他不成器! 肯定是他胡乱欠下的债!我们走的时候明明……”“明明什么?”我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把冰冷的刀子,精准地切断了她的话。 我从地上捡起一张最为破旧、边缘都磨毛了的纸条,那是张奶奶的笔迹,上面还有一小块暗色的油渍,大概是当年包着馒头递给我时沾上的。“粮油店的欠条,日期是你们走前三天。房东的催缴单,截止日期是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张奶奶这两百块,”我把那张纸条举到摄像机前,让那苍老而慈祥的笔迹清晰可见,“是我在你们走后的第七天,饿得实在受不了,在楼下垃圾桶边捡东西吃,被她老人家看见,硬塞给我的。她怕伤我自尊,还说是我妈之前寄放在她那儿的。”我的声音平稳得可怕,没有哽咽,没有激动,只是在陈述一个冰冷的事实。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更砸在那对男女的脸上。“需要我把每一张欠条的时间、缘由,都念给你们听吗?十年,3650天,我吃了多少顿,欠了多少张,每一张我都记得。 需要我帮你们回忆一下,你们‘自由的’、‘成功的’人生起点,是用什么换来的吗? ”父亲剧烈地咳嗽起来,不是装的,是真的喘不上气,脸憋得紫红,手指颤抖地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是一种被当众扒皮抽筋后,极致的羞耻和恐慌。 母亲猛地抬起头,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此刻充满了困兽般的疯狂和怨毒,她尖叫道:“那是你欠我们的!是你欠我们的!生你养你不需要花钱吗?! |
精选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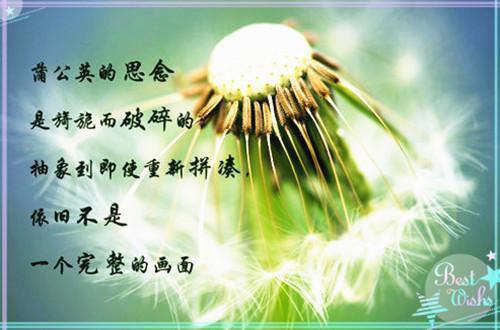 纪妙妙纪远泽(纪妙妙纪远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纪妙妙纪远泽小说免费阅读:纪妙妙纪远泽最新章节列表(纪妙妙纪远泽)
纪妙妙纪远泽(纪妙妙纪远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纪妙妙纪远泽小说免费阅读:纪妙妙纪远泽最新章节列表(纪妙妙纪远泽) 神豪系统(王小帅)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王小帅最新章节列表(王小帅)
神豪系统(王小帅)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王小帅最新章节列表(王小帅) 俞朝朝俞远泽小说无弹窗(俞朝朝俞远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俞朝朝俞远泽)俞朝朝俞远泽最新章节列表(俞朝朝俞远泽)
俞朝朝俞远泽小说无弹窗(俞朝朝俞远泽)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俞朝朝俞远泽)俞朝朝俞远泽最新章节列表(俞朝朝俞远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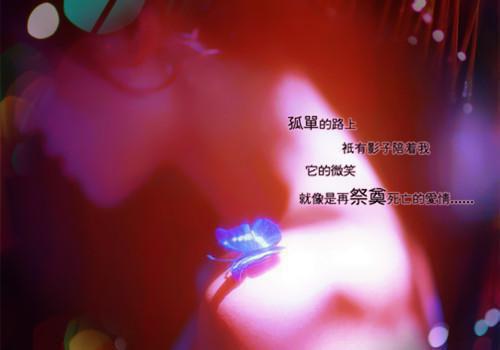 伊小卿墨琛小说: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小说)伊小卿墨琛小说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伊小卿墨琛)
伊小卿墨琛小说: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小说)伊小卿墨琛小说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伊小卿墨琛) 岑声声萧郁(岑声声萧郁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岑声声萧郁)岑声声萧郁小说最新章节列表(岑声声萧郁小说)
岑声声萧郁(岑声声萧郁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岑声声萧郁)岑声声萧郁小说最新章节列表(岑声声萧郁小说) 黎慕星顾绍渊全文(黎慕星顾绍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黎慕星顾绍渊)黎慕星顾绍渊最新章节列表(黎慕星顾绍渊)
黎慕星顾绍渊全文(黎慕星顾绍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黎慕星顾绍渊)黎慕星顾绍渊最新章节列表(黎慕星顾绍渊) 阮棠楚穆的小说免费阅读全文(阮棠楚穆)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棠楚穆最新章节列表(阮棠楚穆)
阮棠楚穆的小说免费阅读全文(阮棠楚穆)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棠楚穆最新章节列表(阮棠楚穆) 重生归来,真千金她摆烂了全文免费阅读(重生归来,真千金她摆烂了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重生归来,真千金她摆烂了)
重生归来,真千金她摆烂了全文免费阅读(重生归来,真千金她摆烂了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重生归来,真千金她摆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