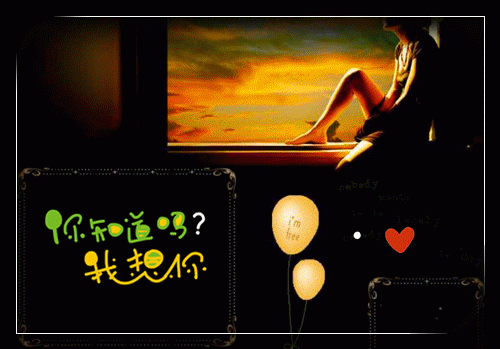国殃次试炼一种热门免费小说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国殃次试炼一种
|
第一部分:深院初入(一)暮春的雨,细密如针,无声地浸湿了青石板路,也浸湿了轿夫们的肩头和那顶略显简朴的花轿。轿子里的沈清辞,指尖微微蜷缩,握着一方素净的帕子,大红盖头下的世界一片混沌的暗红,唯有轿身规律的晃动和窗外淅沥的雨声提醒着她,她正被送往一个全然陌生的命运。 她的人生,前十八年虽家道渐落,却也宁静。父亲是个不大不小的官,母亲早逝,家中虽无泼天富贵,却也诗书传家,给了她一方小小的天地和满腹无法言说的细腻心思。 如今,这方天地被彻底抽离,只因家族需要倚仗侯府之势,而她,沈清辞,成了那根最微不足道、却也必要的纽带。花轿从侧门抬入,并未有想象中的喧天锣鼓。 侯府深似海,连纳新妇都显得如此沉寂而克制。流程繁琐却高效,像演练过无数遍。 喜婆的嗓音带着职业性的喜庆,却透不出多少真心。拜堂,行礼,一切都在一种近乎肃穆的氛围中完成。她甚至没能清晰地感受到身旁那位夫君的存在,只依稀瞥见一抹挺拔的红色身影,以及那双扶着她的手,稳定,却冰凉,没有丝毫温度。
新房倒是宽敞华丽,雕梁画栋,陈设精美,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侯府的底蕴与规矩。 红烛高燃,映照着满室的喜庆红色,却奇异地驱不散那股子沁入骨髓的冷清。 丫鬟们屏息静气,动作轻巧地伺候她卸下繁重的头冠服饰,换上柔软的寝衣。 她们称她“夫人”,语气恭敬,眼神却带着不易察觉的审视与距离。 她独自坐在铺着大红鸳鸯被的床沿,听着更漏一声声滴答,时间变得格外漫长。 盖头早已被取下,她得以打量这间将可能囚禁她一生的牢笼——精致,却毫无生气。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门被推开,带着一丝微凉的夜气和淡淡的酒气。 他来了。沈清辞的心下意识地揪紧,垂着眼,不敢直视。谢允之走了进来。他已换下喜服,穿着一身暗纹常服,更显得身姿颀长,面容俊朗。只是他的眼神过于平静,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映不出半点新婚该有的涟漪。他走到她面前,停下,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审视一件新得的、却并非急切想要的物件。“累了就安置吧。 ”他的声音低沉悦耳,却如同他的眼神一般,没有情绪。没有温存的话语,没有对新妇的好奇,甚至没有一句客套的关怀。仿佛这只是一项必须完成的程序。 沈清辞轻轻“嗯”了一声,声音细若蚊蚋。接下来的事情,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场模糊而令人不适的梦。他吹熄了大部分蜡烛,只留远处一盏昏暗的灯盏。 帐幔落下,隔绝了外界微光。他的动作并不粗暴,甚至可以说是循规蹈矩,却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和机械。她像一朵被骤雨打湿的花,僵硬地承受着,指尖死死攥着身下的锦被,感受不到丝毫属于新婚夜的缱绻与温暖,只有一种被侵入的屈辱和漫无边际的孤独。他似乎只是为了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完成后便起身,自行清理,重新披上外衫。“明日还需向母亲请安,早些歇息。 ”他留下这句话,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便转身离开了新房。门被轻轻合上,室内重归死寂,只剩下她一个人,以及空气中残留的、属于他的冷淡气息。红烛泪尽,黑暗彻底吞噬了她。 沈清辞蜷缩起来,眼泪无声地滑落,浸湿了鸳鸯枕畔。这就是她的新婚,她的夫君。 她仿佛已经能看到未来无数个冷寂日夜的影子。(二)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丫鬟便准时来唤她起身。身子有些不适,心里更是空落落的,但她不敢有丝毫怠慢。 仔细梳妆打扮,换上符合身份的端庄衣裙,在丫鬟的引路下,前往婆婆谢母所居的“颐福堂”。侯府庭院深深,回廊曲折,一路所见皆是规整的景致和垂首敛目的下人,秩序井然,却也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谢母已是端坐堂上,衣着华贵,发髻一丝不苟,面容严肃,眼神锐利。她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并未立刻看向请安的清辞。“儿媳沈氏,给母亲请安。”清辞依着规矩,盈盈下拜,姿态放得极低。谢母这才放下茶盏,目光如实质般在她身上扫过,从头发丝到脚底,细细打量了一番。“起来吧。”声音冷淡,“既入了谢家的门,往后便要谨守谢家的规矩。 晨昏定省,不可懈怠。言行举止,皆需符合身份,莫要失了侯府的体面。”“是,儿媳谨记母亲教诲。”清辞低声应道。“允之肩挑家族重担,事务繁忙,你身为正室,要贤良淑德,打理好内院,为他分忧,更要早日为谢家开枝散叶,延绵子嗣,这才是你的本分。”谢母的话语直白而功利,将她存在的意义定义得清清楚楚。接着,便是冗长的关于府中规矩的训导,事无巨细,包括用餐礼仪、如何管理下人、如何接待宾客等等。清辞垂首静听,一一应下,只觉得肩膀上的枷锁又沉了几分。请安完毕,谢母便让她退下,并无多余的话家常的意思。 回到自己居住的“漱玉院”,清辞稍稍松了口气,但这院子同样冷清。 她尝试着询问丫鬟一些关于府中的事务,丫鬟的回答虽恭敬,却透着疏远,只挑些不打紧的说,显然并未真正将她视作可效忠的主子。午膳时,谢允之并未回来。 她独自对着满桌精致的菜肴,食不知味。饭后,她试着想找些事情做,却发现并无真正需要她插手的事务。中馈之权显然牢牢握在谢母手中,她这个新妇,暂时只需做个摆设。她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栽种的一株玉兰树,花期已过,只剩下郁郁葱葱的叶子。天空被四方的屋檐切割成规整的形状,如同她此刻的人生。下午,她找了本带来的诗集,靠在窗边软榻上翻阅。字句虽美,却难以投入。 心思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昨晚那个冷漠的身影,以及未来漫长而似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傍晚时分,谢允之回来了。他直接去了书房处理公务,直至晚膳时分才出现。餐桌上,气氛沉默得令人窒息。他吃得很快,举止优雅却毫无暖意。清辞试图找些话题,声音轻柔地问:“夫君今日公务可还顺利?”他抬眸看了她一眼,似乎有些意外她会开口,只淡淡回了句:“尚可。”便再无下文。她鼓起勇气,又试探着问:“不知……府中可有什么需要妾身帮忙的地方?”谢允之放下筷子,用餐巾拭了拭嘴角,道:“内院之事自有母亲掌管,你若有心,便多去母亲跟前聆听教诲,学着些。暂无他事需你劳神。”他的话堵死了她所有试图融入和贡献的可能,将她彻底边缘化。用完膳,他漱了口,便起身道:“我还有些文书要看,你自行歇息吧。 ”说完,他便又离开了,方向依旧是书房。清辞独自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几乎没动几口的菜肴,心里一片冰凉。她就像一个误入他人世界的旁观者,不被需要,不被看见。夜晚,她独自躺在宽大的床上,听着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什么是深宅寂寞。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过,平淡得像一潭死水。沈清辞严格遵循着规矩,每日晨昏定省,从无缺席。谢母对她的挑剔却并未减少,有时是仪态,有时是衣着,有时甚至只是因为她请安时声音稍微轻了些,都能引来一番训诫。她愈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谢允之依旧忙碌,很少在漱玉院停留。他偶尔会过来用膳,偶尔会宿在她这里,但每一次都如同例行公事。结束后要么离开,要么背对她睡下,仿佛身边只是躺着一个没有温度的枕头。清辞从最初的紧张、羞涩、甚至残存着一丝幻想,逐渐变得麻木。她学会了在他来时放空自己,在他离开后蜷缩入睡。 她试图在自己的小院里寻找一点寄托。她精心打理窗台上的几盆兰花,每日对着它们说话;她绣花,将无人可诉的心事一针一线绣进繁复的花纹里;她看书,却常常对着某一页发呆良久。府里的下人对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礼貌的距离。 她曾无意中听到两个小丫鬟在廊下低语,议论她不得世子欢心,怕是位置坐不稳。 她默默走开,心口像被细针扎了一下,细细密密的疼。有时,她会远远看到谢允之与其他族人交谈,或是与幕僚商议事情。那时的他,虽然依旧不算热络,但眼神是专注的,言语间自有运筹帷幄的气度。那是一个她完全接触不到的世界,而他,也从不会将那个世界里的任何情绪带给她分毫。一次家宴,她坐在他身侧,为他布菜斟酒,扮演着端庄得体的世子夫人。他与叔伯兄弟谈论朝局时事,言笑间从容不迫。 有人打趣他们新婚,他只是淡淡一笑,举杯饮尽,并未看她一眼,也未接话。 她就像他桌案上一件精美的摆设,必要时刻在场,却从不被纳入视线焦点。宴席散后,他微醺,她扶他回房。这是他第一次允许她如此靠近。他身上有酒气和淡淡的墨香,手臂的温度透过衣料传来,让她有一瞬间的恍惚。她小心翼翼地伺候他躺下,为他擦拭额头。 他忽然抓住她的手腕,力道不重,却让她心跳漏了一拍。他半阖着眼,眸光有些迷离,望着她,似乎想说什么。清辞的心提了起来,一丝微弱的、几乎被她自己掐灭的希望火苗,竟然又怯生生地重新燃起。但他只是皱了皱眉,模糊地嘟囔了一句:“……茶……”原来只是要喝茶。那点火苗瞬间熄灭,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烬。她默默地倒了茶,喂他喝下。他很快沉沉睡去,呼吸均匀。而她,睁着眼看着帐顶,一夜无眠。希望是最残忍的东西,它让你在绝望的深渊里,偶尔看到一丝虚幻的光亮,然后更重地跌落。她开始学着不去期待。 庭院里的玉兰花落了又开,开了又落。转眼间,她嫁入侯府已近一年。四季轮回,景物依旧,而她的心,却在日复一日的冷漠和孤寂中,慢慢沉静下来,或者说,慢慢死去。 第二部分:细碎磋磨(一)暑气渐消,秋意染黄了漱玉院中的那株老银杏。 金灿灿的叶子落了满地,像是铺了一层寂寥的华毯。沈清辞坐在窗边,看着小丫鬟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将那绚烂的金黄扫拢、运走,露出底下青灰冰冷的石板地。 如同她心底那些微不足道的、对温情的渴望,也早已被日复一日的漠然扫荡干净。 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摆,精准而重复地摆动。晨起,梳妆,前往颐福堂请安,聆听婆婆谢母或明或暗的敲打与训导,然后回到自己的院子,对着四方天空,刺绣、看书、侍弄花草,等待或许会来、或许不会来的夫君,再用漫长的夜晚消化白日的孤寂。谢母的压力日益具体化。最初只是笼统的规矩和子嗣,如今已变得尖锐而直接。这日请安时,谢母并未像往常一样让她立刻离去,而是慢悠悠地拨着茶盖,目光锐利地落在她依旧平坦的小腹上。“你入府也快一年了。 ”谢母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千斤重压,“肚子至今还没个动静。允之虽忙,却也不是全然未在你房中留宿。可是身子有什么不妥?”清辞指尖一颤,低垂着头,脸颊泛起一丝窘迫的红晕,声音细弱:“回母亲,儿媳……身子并无不适。”“既无不妥,便是缘分未到,或是你不够尽心。”谢母语气冷淡,“侯府子嗣乃是头等大事,延续香火是你身为正室的首要职责。平日里饮食起居要多注意,那些寒凉之物少碰,多调养身子。我也会让厨房定期给你送些滋补的汤药,你需按时服用。”“是,谢母亲关怀。 ”清辞应道,心里却一片苦涩。汤药?仿佛她是一件需要修理的器物,唯一的价值便是产出子嗣。她的感受、她的尊严,在“开枝散叶”这四个字面前,轻如尘埃。 从颐福堂出来,秋风吹在身上,带着透骨的凉意。她拢了拢衣襟,只觉得那沉重的压力如影随形。每一次谢允之来她房里,原本就已如同完成任务,如今更添了一层明确的功利色彩,让她倍感屈辱和难堪。而他,似乎对此毫无察觉,或许即便察觉,也并不在意。(二)谢允之的冷漠,已渗透进每一个细微的日常角落,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磋磨。清辞记得他生辰前,她耗费了半月心血,精心绣了一个香囊。 料子用的是他常穿的月白云锦,图案是雅致的青竹暗纹,里面填了她悄悄配的安神香料,一针一线都藏着她无法宣之于口的、卑微的期盼。他生辰那日晚间,难得过来用膳。 她踌躇良久,在他用完茶后,才鼓起勇气将香囊取出,双手奉上,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夫君,这是妾身……一点心意。”谢允之接过去,目光在香囊上停留了片刻。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有心了。”他语气平淡,随手将香囊放在了桌上,转而拿起一旁侍从刚送来的公文,“下次不必费这些功夫,府中不缺这些物件。”那一刻,清辞只觉得脸上血色尽褪,所有精心准备的话语和期待都碎成了齑粉。他甚至没有多看一眼那细致的纹路,没有闻到那清雅的香气。她的心意,在他眼中,与府中库房里任何一件闲置物品并无区别,甚至可能还是多余的。那香囊后来不知所踪,或许被他随手赏了下人,或许遗落在了某个角落,覆上了灰尘。她再也没有问起,也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还有一次,秋雨连绵,她不慎感染了风寒,头重脚轻,咳嗽不止。丫鬟请了府医来看,开了药。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身体难受,心里却莫名生出一丝脆弱的依赖感。 她想着,他若是知道,或许会来看一眼?哪怕只是一句客套的问候?晚间歇息时,谢允之过来了。他显然刚从外面回来,带着一身湿冷的寒气。见到她病恹恹地靠在床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病了?”他问。“嗯,些许风寒,不碍事。”她忍着咳嗽回答,心底那点微弱的火苗又闪烁起来。“既病了就好好歇着,按时服药。”他语气如常,听不出关切,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甚至没有走近床边,只是站在屏风处交代了一句:“近日雨水多,莫要贪凉。明日我让管事再送些银炭过来。 ”然后,他便转身离开了,说是书房还有事,今夜便不过来了。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清辞望着空荡荡的门口,只觉得那点刚刚升起的暖意被更深的寒冷取代。 他给了实际的物资银炭,却吝啬于一丝一毫的情感慰藉。或许在他看来,生病只需要药物治疗和物质保障,至于病人是否需要陪伴和安慰,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者说,不在他给予她的范围之内。她蜷缩进被子里,剧烈的咳嗽声在空寂的房间里回荡,像是在嘲笑她方才那可笑的期待。(三)在这深宅里,孤独是常态,但最刺骨的孤独,来自于对比。谢允之并非天生冷情之人,清辞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他的温和、他的关注,从不会浪费在她身上。一次,她去花园散心,远远看见谢允之和他的一位堂弟在亭中下棋。他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意,眼神专注地看着棋盘,偶尔会与堂弟交谈几句,气氛融洽自然。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松弛状态下的他。还有一次,谢母头疼旧疾复发,谢允之亲自在一旁侍奉汤药,眉头紧锁,语气虽依旧沉稳,却透着显而易见的担忧。 他仔细询问府医情况,叮嘱下人小心伺候。那一刻,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更让她心头刺痛的,是那位姓柳的姨娘的存在。柳姨娘是谢允之成婚前就在房里的老人,性子安静,并不张扬跋扈。清辞偶尔会在请安时或园中遇到她。 谢允之去柳姨娘房中的次数似乎并不比来她这里多多少,但态度却微有不同。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谢允之和柳姨娘在廊下说话。柳姨娘似乎在回禀什么事情,谢允之听着,偶尔点头,神色虽谈不上亲密,却有一种经年累月形成的、自然而然的熟稔。 他甚至随手将一本看起来像是账册的东西交给了柳姨娘,吩咐了几句。柳姨娘恭敬应下,眼神里带着一种清辞从未在谢允之身边见过的、放松的依赖感。原来,他也是可以这样与人正常交流的。原来,他并非对所有人都像对她这般,隔着千山万水。 清辞默默地退开了。她忽然明白,自己在这个府里的位置有多么尴尬。她是明媒正娶的正室,地位尊崇,却得不到丈夫丝毫的另眼相看,甚至连他身边一个旧人都不如。他们之间,除了冰冷的礼法和义务,空无一物。她像是一个被硬塞进这个家庭的、多余的存在,格格不入。婆婆的苛责,丈夫的冷漠,妾室的存在……这一切都像细密的砂纸,一日日、一遍遍打磨着她的心。最初的刺痛和委屈渐渐变得麻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和虚无感。她的话变得更少了,笑容几乎从脸上消失。 每日除了必要的请安和应答,她更愿意待在自己的漱玉院里,对着那几盆不会说话的兰花,或者对着窗外那片四方的天空发呆。她开始失眠,夜晚变得格外漫长。听着更漏声,数着更次,眼睁睁看着窗纸从漆黑变为灰白。身体也渐渐消瘦下去,原本就纤细的身姿,如今更显得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华丽的衣裙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衬得她脸色愈发苍白。丫鬟似乎有些担忧,试探着问:“夫人,您近日气色不佳,可要再请府医来看看?”清辞只是轻轻摇头:“无妨,只是夜里睡得浅些。 ”她还能说什么呢?她的病,不在身体,而在心里。而心药,这侯府上下,无人能予,也无人愿予。秋深了,漱玉院中的花草大多凋零,只剩下一簇晚菊,在冷风中瑟瑟地开着,颜色黯淡。清辞坐在廊下,看着那残菊,觉得自己与它何其相似。无人欣赏,独自开放,然后悄无声息地零落成泥。希望这个词,对她来说已经太过奢侈。她不再期待谢允之的垂怜,不再幻想举案齐眉。她只是活着,按照既定的轨迹,一日日地熬下去。 像一颗被嵌入固定位置的棋子,动弹不得,只能静静等待着命运或许早已安排好的、寂寥的终局。 第三部分:希望微光与幻灭(一)入了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将侯府层层叠叠的屋檐、凋零的枝桠都覆上了一层洁净的银白,暂时掩盖了所有的棱角与寂寥。漱玉院里,那株老银杏早已落光了叶子,黑色的枝干擎着雪,像一幅疏淡的水墨画。沈清辞拥着一件半旧的狐裘,坐在烧着银炭的暖阁里,手里拿着一卷书,却许久未翻一页。炭盆偶尔爆出一两声轻微的“噼啪”响,是这寂静房间里唯一的热闹。她的心,似乎也随着天气一起冻住了,不再轻易为那些细碎的磋磨而疼痛,只剩下一片麻木的平静。谢母送的汤药,她每日按时喝着,那苦味从舌尖蔓延到心里,成了日常的一部分。谢允之依旧忙碌,来她这里的次数并无增减,来了,也依旧是那样例行公事。她已学会在他来时,将自己的神思抽离,像个木偶般配合,然后在他离开后,继续自己的枯坐。年关将近,府里渐渐忙碌起来,准备祭祀、年礼、宴请。这种忙碌却与清辞无关,她依旧被排除在核心事务之外,只需在需要她出现的场合,穿戴整齐地做个安静的背景。 腊月二十三,小年。侯府设家宴,族中亲近的几房人都来了。宴席设在大花厅里,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一时间人声喧沸,似乎驱散了些许冬日的冷清。清辞作为世子夫人,自然坐在谢允之身侧。她保持着得体的微笑,为他布菜、斟酒,应对着族人的寒暄,举止无可挑剔。席间,一位颇有权势的叔公多喝了几杯,言语间对谢允之颇为推崇,又半开玩笑地提起朝中一件棘手的事务,言语间有试探之意。谢允之应对得体,既不居功自傲,也不露丝毫怯懦,分寸拿捏得极好。那叔公似乎存心要考较他,话头一转,竟直接问起了清辞的父亲——那位官职不高、家道中落的沈父近日经办的一件小事,语气带着几分轻慢。一时间,席间目光若有若无地投向清辞。她父亲官职低微,在侯府这样的门第前,本就是难以启齿的短板。清辞脸颊微热,指尖蜷缩,感到一阵难堪。 就在这时,谢允之却淡然开口,他并未直接反驳那位叔公,而是巧妙地接话,三言两语将话题引回那件朝中事务,并顺势提及了与沈父所办之事相关的另一条政令,客观地分析了其利弊,言语间不经意地抬高了沈父所经办事务的层面和重要性,既全了叔公的面子,又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清辞的尴尬。他的声音平稳冷静,逻辑清晰,仿佛只是在就事论事。但清辞却愣住了。她清晰地听到,他在提及她父亲时,用了“岳丈”二字。虽然语气公事公办,但在这公开场合,这是一种明确的身份认可和维护。 那一刻,她沉寂已久的心湖,像是被投入了一颗极小极小的石子,漾开了一圈微不可见的涟漪。她下意识地侧头看向他。他正举杯与叔公对饮,侧脸线条依旧冷硬,但在晃动的烛光下,似乎有那么一瞬间,显得不那么遥不可及。 他……这是在维护她吗?哪怕只是出于世子夫人的体面,出于他自身的骄傲不容他人轻视他的岳家?一股极其微弱、几乎被她自己判定为荒谬的希望,如同风中残烛般,怯生生地重新闪烁起来。或许……他并非完全无视她? 或许在他那冰封的表象之下,也藏着一丝极其细微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关切? (二)这场家宴之后,清辞的心境发生了一丝极其微妙的变化。 那点微弱的火苗虽然摇摇欲坠,却顽固地不肯熄灭。 她开始不由自主地留意起谢允之的言行举止,试图从中寻找哪怕一丁点能够佐证她那荒谬期待的痕迹。她发现他近来似乎格外忙碌,有时深夜书房的灯还亮着。她想起家宴上他们提及的朝中事务,猜想他或许遇到了难题。 鬼使神差地,她吩咐小厨房炖了一盅安神补气的汤品。夜色深沉,她亲自提着食盒,踏着清冷的月光,走向前院书房。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去寻他。一路上,心绪不宁,既期待又害怕。期待能借此机会稍稍靠近他,害怕得到的依旧是冰冷的拒绝。 书房外守着的小厮见她来了,有些惊讶,但还是进去通传了。片刻后,小厮出来,躬身道:“夫人,世子爷请您进去。”清辞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檀香。谢允之正坐在宽大的书案后,面前堆着高高的文书。 烛光映照着他略显疲惫的眉眼,但他依旧坐得笔直。见到她进来,他抬起眼,目光里带着一丝询问。“夫君,”清辞将食盒放在一旁的茶几上,声音轻柔,“夜深了,见书房灯还亮着,炖了盏汤,您用一些再忙吧。”谢允之的目光扫过食盒,又落回她脸上,停顿了片刻。他的眼神似乎比平时柔和了些许,或许是因为疲惫,或许是因为那盏汤来得恰好。“有劳了。”他淡淡道,并未立刻去用,而是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吧。”清辞依言坐下,心跳得有些快。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烛火偶尔跳跃的轻微声响和他翻动纸张的声音。她不敢打扰他,只安静地坐着,目光悄悄打量这间属于他的领地。书卷气很浓,陈设简洁而冷硬,一如他本人。过了一会儿, |
精选图文
 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抖音近期热门小说-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完结版在线阅读
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抖音近期热门小说-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完结版在线阅读 热文推荐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 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小说无弹窗大结局
热文推荐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 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萧嫣小说无弹窗大结局 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免费完结小说-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在线阅读全文(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
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免费完结小说-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在线阅读全文(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 (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阅读无弹窗)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小说章节列表
(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阅读无弹窗)我在末世开度假酒店许意小说章节列表 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小说(萧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小说(萧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萧嫣长篇免费小说 今日热搜好文分享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
萧嫣长篇免费小说 今日热搜好文分享重生后,七个兄长跪着求原谅 高质量小说丑妃成凰后,战神王爷高攀不起了 蓝若初楚夜宸推荐阅读
高质量小说丑妃成凰后,战神王爷高攀不起了 蓝若初楚夜宸推荐阅读 沈依宁长愠全文(沈依宁长愠)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沈依宁长愠全文无弹窗完整版阅读
沈依宁长愠全文(沈依宁长愠)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沈依宁长愠全文无弹窗完整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