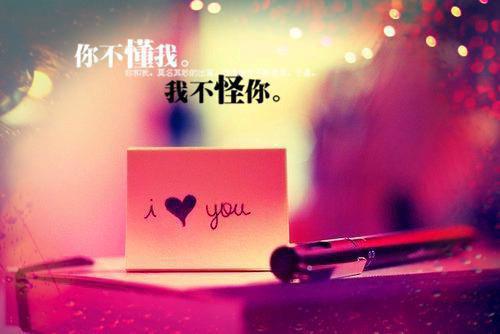水磨遗韵丹新梦牡丹新免费小说全集_小说免费完结水磨遗韵丹新梦牡丹新
|
1 最后一盏灯苏州平江路的夜色总是带着几分湿漉漉的诗意,青石板路在细雨初停后泛着幽光,两旁的白墙黛瓦在红灯笼的映照下忽明忽暗。 已是深夜十一点,大多数店铺早已打烊,唯有一处不起眼的小院还亮着灯。 院门上挂着一块老旧的木牌,上面用娟秀的楷书写着“沁兰昆剧传习社”。推门而入,院内别有洞天——约摸五十平米的空间被改造成一个小小的舞台,台下摆放着二十余张座椅,台上垂着暗红色的幕布,幕布一角微微掀起,露出后面挂着的各式戏服。 沈雪衣站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中央,水袖垂地,眼神空洞。“师父,都清点好了。 ”年轻助手小陈从后台走出来,声音低沉,“后天...文化局的人就会来接收这里。
”雪衣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她的目光落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央的那个位置——五年来,每个周六晚上七点,总会有一位白发老者坐在那里,闭目聆听,指节轻轻叩着扶手,和着节拍。直到三个月前,他再也没有出现。那是她的师父,昆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顾砚秋。传习社是师父毕生的心血,不为盈利,只为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昆曲这门有着六百年历史的艺术。然而随着老人离世,经费中断,学员稀少,这个小小的传承基地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沈老师,有您的快递。 ”快递员在门外喊道,打破了院中的沉寂。小陈赶忙出去签收,不一会儿抱着一个方正的木匣子进来:“奇怪,没有寄件人信息。”雪衣终于转过身来。 那木匣做工精致,表面刻着缠枝莲纹,锁孔处镶嵌着一小块白玉,一看便知不是寻常物件。 她轻轻打开匣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照片和几本手抄工尺谱,最上面放着一封信。信纸展开,是师父熟悉的笔迹:“雪衣吾徒:若见此信,想必传习社已至危难之际。余一生守护昆曲,临终唯一憾事,乃未能寻得《牡丹新梦》全本。此剧为民国初年昆曲大家俞沁兰绝笔之作,融传统昆腔与现代叙事于一炉,堪称艺术巅峰,然战乱中散佚,仅存残谱断章。 余穷半生之力寻访,终无所获。今将此愿托付于你,若得全本,不仅传习社可存,昆曲复兴或亦有望...”信末附着一串地址和一个名字:梅素心,西山镇梧桐路17号。 雪衣的手微微颤抖。《牡丹新梦》?她从未听师父提起过这部戏。作为顾砚秋的关门弟子,她以为自己已经继承了师父所有的技艺和知识,没想到老人心中还藏着这样的秘密。“小陈,帮我订一张去西山镇的车票。”雪衣突然道,眼神重新燃起了光芒,“在文化局来人之前,我们还有一天时间。”“可是沈老师,明天您还要去文化和旅游局办交接手续...”“那就后天一早出发。 ”雪衣的语气不容置疑,“传习社可以关门,但师父的遗愿不能辜负。”夜深了,雪衣独自留在传习社。她打开师父留下的木匣,仔细翻看里面的物品——几张黑白照片上是一位身着戏服的女子,身段婀娜,眼波流转,照片背面写着“俞沁兰,民国廿五年”;几本手抄谱子字迹娟秀,记录的却是她从未听过的曲牌;最底下是一份旧报纸 clipping,日期是1937年8月,标题模糊可辨:“名伶俞沁兰告别舞台,携《牡丹新梦》全本隐退”。雪衣的手指轻抚过报纸上那张模糊的面容,忽然觉得这女子有几分面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窗外,最后一家店铺的灯也熄灭了,平江路陷入沉睡,只有传习社的灯还亮着,如同黑夜里孤独的守望者。她不知道,这盏灯照亮的不只是今夜的平江路,更是一段被时光尘封了八十年的传奇。 2 西山梅宅西山镇距苏州市区不过六十公里,却仿佛隔了一个时代。 这里没有平江路的喧嚣,只有小桥流水,古树老宅,时间在这里流淌得格外缓慢。按照地址,雪衣找到了梧桐路17号——一座临水而建的老式宅院,白墙已有些斑驳,黑瓦间生长着顽强的瓦松,木门上的朱漆剥落大半,唯有一对铜环还算光亮。 门楣上悬着一块匾额,上书“梅庐”二字,笔力遒劲,颇有风骨。雪衣叩响门环,许久,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探出身来。她看上去七十多岁,穿着素雅的棉麻旗袍,颈间挂着一副老花镜,眼神锐利而警惕。“找谁? ”老人的声音沙哑却清晰。“请问是梅素心女士吗?我是顾砚秋先生的徒弟沈雪衣。 ”雪衣恭敬地递上师父的信件,“师父临终前嘱托我来找您。”听到“顾砚秋”三个字,老人的眼神微微波动,她接过信纸,仔细阅读起来。随着阅读,她的手开始轻微颤抖,眼角泛起泪光。“砚秋他...走了?”梅素心抬起头,声音哽咽。 雪衣沉重地点点头:“三个月前。师父走得很安详,在睡梦中离去的。”老人长叹一声,推开大门:“进来吧,我等你很久了。”梅宅内部比外观更加古雅,庭院不大却布置精巧,假山盆景一应俱全,廊下挂着一排鸟笼,几只画眉轻声鸣叫。 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墙边的一整排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戏曲相关的书籍和唱片。 正堂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雪衣一眼认出那是俞沁兰的舞台剧照——不同于匣中照片,这幅照片中的俞沁兰身着杜丽娘戏装,正在花园中“游园惊梦”,眼神凄婉动人。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沁兰姊惠存,梅兰芳赠,民国廿六年春”。 “梅兰芳先生赠的照片?”雪衣惊讶地问。梅素心正在沏茶,闻言抬头看了一眼照片:“是啊,先父与梅先生是故交。事实上,我们梅家与俞家是世交,俞沁兰是我的姑母。”雪衣震惊不已。俞沁兰若是梅素心的姑母,那么眼前这位老人至少已经...“我今年九十二了。”梅素心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微微一笑,“不像?昆曲养人,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行当。”她将茶杯递给雪衣,“你师父在信中说,你想找《牡丹新梦》的全本? ”雪衣急切地点头:“师父说这部戏可能关系到昆曲在现代的复兴。 传习社快要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能够找到全本并排演,或许...”梅素心摇摇头打断她:“年轻人,寻找《牡丹新梦》不是为了救一个传习社那么简单。这部戏背后,藏着昆曲传承中最重要却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踱步到窗前,望着院中一角青竹,“姑母生前曾说,《牡丹新梦》是她艺术生命的巅峰,也是她对昆曲未来的全部寄托。 可惜生不逢时,戏成之日,正值山河破碎,哪还有人静心听戏? ”“那全本手稿...”雪衣小心翼翼地问。“姑母临终前,将手稿一分为三,交给了三个最信任的人。”梅素心转身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本发黄的笔记,翻到某一页,“第一部分‘惊梦’,她交给了自己的琴师程雪初;第二部分‘寻梦’,交给了编剧和词作者苏慕云;最后一部分‘圆梦’,则交给了当时最年轻的传承人,也就是你的师祖——顾砚秋的师父,林雪斋。 ”雪衣恍然大悟:“所以师父继承的只是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梅素心神色凝重,“战乱中,三位保管人天各一方。程雪初南下香港,苏慕云远赴台湾,唯有林雪斋留在大陆。 数十年来,海峡阻隔,这部杰作再也无人得见全貌。 ”“那三位保管人现在...”“程雪初和苏慕云恐怕早已作古,他们的后人是否知道手稿的价值,也未可知。”梅素心合上笔记,“你师父穷半生之力寻找,始终没有结果。如今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你,可见对你寄予厚望。”雪衣感到肩头沉甸甸的。 跨越八十年的时间,跨越海峡的阻隔,寻找三部散佚的手稿,这简直是大海捞针。 “不过...”梅素心忽然语气一转,“你师父不知道的是,姑母当年还留下了线索。 ”她从颈间取下一枚小巧的银钥匙,“这是姑母首饰盒的钥匙,里面或许有寻找手稿的提示。 我年事已高,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了。如今把它交给你,希望你能实现姑母的遗愿,让《牡丹新梦》重见天日。”雪衣接过那枚温热的钥匙,感觉接过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我会尽力而为,梅婆婆。” “不是尽力,而是必须。”梅素心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你知道吗? 近年来有不少人也在打听《牡丹新梦》的下落,其中有些人...目的不纯。 一部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昆曲杰作,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雪衣忽然想起最近几个月,确实有几拨人以“学术研究”为名来传习社打听过师父收藏的剧本资料,当时她并未在意。 离开梅宅时,夕阳西下,为西山镇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雪衣回头望去,梅素心站在门口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她握紧手中的银钥匙,知道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3 首饰盒的秘密回到苏州市区已是华灯初上。雪衣没有回传习社,而是直接去了师父故居——一处藏在巷弄深处的老房子,自从师父去世后,她每周都会来打扫一次。书房还保持着老人生前的样子:靠墙一排书架上摆满了戏曲文献,窗边的书桌上笔墨纸砚井然有序,墙上挂着各种剧照和字画。 雪衣记得师父有一个老式的首饰盒,就放在书架顶层,但她从未见师父打开过。踩着凳子,她取下了那个积着薄尘的红木盒子。盒子不大,却做工精致,表面雕刻着蝶恋花纹样,锁孔与梅素心给的钥匙正好匹配。心跳不由得加快,雪衣深吸一口气,将钥匙插入锁孔。 轻轻转动,“咔哒”一声,盒盖弹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师父顾砚秋年轻时与一位女子的合影。两人身着戏装,似乎是刚演完《牡丹亭》的“惊梦”一折,师父扮柳梦梅,女子扮杜丽娘,眼角眉梢都是笑意。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砚秋与沁兰姊弟子慕云于丙申年春”。 雪衣愣住了。慕云?难道就是《牡丹新梦》的编剧苏慕云?师父从未提起过认识苏慕云,更别说合影了。而且“沁兰姊弟子”这个称呼...她继续翻看盒中之物:几件简单的首饰,一枚象牙章,一绺用红绳系着的青丝,还有一封信札。展开信纸,是女性娟秀的笔迹:“砚秋君如晤: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今苏州沦陷在即,吾随剧团南下避祸,前路未卜。蒙沁兰师厚爱,托付《牡丹新梦》之‘圆梦’篇与君,盼有朝一日,四海清平,此剧得见天日。另,慕云师妹已赴台岛,音讯杳然。 雪初兄携‘惊梦’篇赴港,地址如附。若得重逢,全本可期。珍重珍重。雪斋手书,民国廿六年冬。”雪衣的手微微颤抖。林雪斋——她的师祖,师父的恩师,原来就是照片中那位扮演杜丽娘的女子!而且从信中看,与师父之间的关系似乎不仅仅是师徒那么简单...更令她震惊的是附在信后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香港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382号 程氏琴行。七十年过去了,这个地址还会存在吗?程雪初的后人还在那里吗?雪衣立即打开笔记本电脑查询。 令人惊讶的是,九龙弥敦道382号确实有一家“程氏琴行”,而且还在营业,专营民族乐器和戏曲音像制品。看了眼时间,晚上八点十分,香港与内地没有时差。 她犹豫片刻,还是按照网站上找到的号码拨通了电话。铃音响了很久,就在雪衣准备挂断时,电话被接起了:“喂,程氏琴行。”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带着港式普通话的软糯腔调。 “您好,我来自苏州,想咨询一些关于昆曲资料的事情...”雪衣小心措辞。 对方沉默片刻,突然改用流利的普通话:“您是为了《牡丹新梦》而来的吧? ”雪衣几乎握不住电话:“您...怎么知道?”“三个月来,您是第四位打听这部戏的人。 ”男子的声音带着几分警惕,“前几位都声称自己是学者或收藏家,但连最基本的昆曲知识都不懂。您能说出《牡丹新梦》与《牡丹亭》的区别吗? ”雪衣定了定神,从容应答:“《牡丹亭》是汤显祖的古典名作,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之恋;而《牡丹新梦》是俞沁兰在民国时期改编创新的作品,虽然基于原著,但融入了现代视角和表演手法,据说在音乐和唱腔上也有重大突破。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后语气缓和了许多:“看来您是懂行的人。不瞒您说,先祖父程雪初临终前确实交代过,若有一天有内地懂昆曲的人来寻《牡丹新梦》,便将一份手稿交予对方。但必须确认来者确是俞派传人。”“如何确认? ”“两个方法:一是出示俞沁兰信物,二是唱一段《牡丹新梦》的‘皂罗袍’。 ”男子顿了顿,“先祖父留下了曲谱,但我无人传授,只能按谱验证。”雪衣犯难了。 俞沁兰的信物在梅素心那里,而《牡丹新梦》的唱腔她根本不会。 “能不能...请您把曲谱传真或者拍照发给我?我学习后再唱给您听?”雪衣提议道。 男子轻笑一声:“您倒是聪明。这样吧,我先把曲谱发您邮箱,您练习好了再联系我。 不过要快,最近有些人也在打听这份手稿,我不确定能保管多久。”挂断电话后不久,雪衣的邮箱就收到了一封来自“程氏琴行”的邮件。 附件是一张发黄曲谱的照片——《牡丹新梦》中的“皂罗袍”选段。雪衣仔细研究曲谱,发现它与传统“皂罗袍”曲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诸多创新。工尺谱旁还有细小注解,提示演唱时的情感处理和表演要点。夜深人静,她站在师父故居的庭院中,按照曲谱轻声试唱。起初有些生涩,但很快就找到了感觉——这唱腔既保留了昆曲水磨腔的婉转缠绵,又加入了更为丰富的情感表达,更加贴合现代人的审美。突然,她注意到谱子边缘有一行几乎褪色的小字:“慕云注:此處當如驚鴻乍現,轉音若即若離,似夢非夢。”慕云!苏慕云!这部戏的编剧竟然亲自为唱腔做了注解!雪衣一遍遍练习,直到东方既白。她感受到这部戏的非凡之处——它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却又完美保持了昆曲的精髓。难怪师父说它可能引领昆曲的复兴。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庭院时,雪衣再次拨通了香港的电话。她没有伴奏,清唱了那段“皂罗袍”。唱毕,电话那头久久无声。“先生?您还在吗?”雪衣不安地问。 对方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激动:“太像了...先祖父留下的老唱片里,俞沁兰的唱腔就是这样的!您一定是真正的传人。请来香港吧,我把‘惊梦’篇手稿交给您。 ”雪衣松了口气,随即又想起一个问题:“冒昧问一下,您说的前几位打听《牡丹新梦》的人,有什么特征吗? ”男子沉吟片刻:“最奇怪的是一位自称日本大学教授的人,汉语很流利,但对昆曲的了解明显是临时恶补的。还有一位女士,声音很冷,问了很多关于手稿价值的问题。最后一位是内地口音,说是要做非遗研究,但连水磨腔是什么都说不清楚。”雪衣心中警铃大作。看来梅婆婆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多方人马在寻找《牡丹新梦》。她当即订了最早飞香港的机票。不管前方有什么困难,她必须拿到“惊梦”篇——这不仅是为了完成师父的遗愿,更是为了守护昆曲的宝贵遗产。 离开师父故居时,雪衣最后回望了一眼书房。晨光中,墙上那张师祖林雪斋的剧照仿佛活了过来,眼神中满是期待与嘱托。“我会找到全本的,师祖。一定。”雪衣轻声发誓。4 九龙琴踪香港九龙弥敦道382号,程氏琴行。 与周围光鲜亮丽的商铺相比,这家琴行显得格外古旧。 橱窗里陈列着竹笛、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店内飘出若有若无的檀香味。推开玻璃门,门楣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个年轻男子从柜台后抬起头来。他约摸二十七八岁,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简约的灰色衬衫,气质文雅。“您是...沈小姐? ”男子用略带港腔的普通话问道。雪衣点头:“您是程先生?我们通过电话。”“程枫。 ”男子伸出手来,“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握手时,雪衣注意到程枫的手指修长,指尖有薄茧,显然是常年练习乐器留下的痕迹。“程先生也精通乐器?”“略懂古琴和笛箫,比不上先祖父。”程枫谦虚地笑笑,引雪衣进入店内,“程氏琴行创办于1948年,先祖父程雪初来港后白手起家建立的。他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回到苏州,没能看到《牡丹新梦》全本重现舞台。”店内空间不大,却别有洞天。 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民族乐器,柜台后是一整排关于戏曲音乐的书籍和老唱片。 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正堂中央的一幅水墨画——画中一位青衣琴师正在月下抚琴,题款是“雪初兄雅赏,沁兰甲申年冬”。“俞沁兰女士的亲笔?”雪衣惊讶地问。 程枫点头:“先祖父曾是俞女士的专职琴师,两人合作十余年。 《牡丹新梦》的音乐部分大多出自先祖父之手,俞女士亲自题画相赠。 ”他小心地从柜台下取出一只长条形的木匣:“这就是‘惊梦’篇的手稿。 先祖父临终前嘱咐,一定要交给真正的俞派传人。”雪衣深吸一口气,轻轻打开木匣。 里面是一卷已经发黄的宣纸,小心翼翼展开后,露出用工整小楷誊写的曲谱和唱词,页边还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修改痕迹。正是《牡丹新梦》的“惊梦”篇! 雪衣的手指轻抚过那些音符和文字,仿佛能感受到创作者的心血和温度。 她注意到谱中有许多创新之处——传统曲牌被巧妙改造,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但又不失昆曲本色。“太精湛了...”她由衷感叹,“这不仅仅是改编,简直是艺术再创造。”程枫微笑:“先祖父曾说,俞女士的野心不是简单地重排《牡丹亭》,而是要创造一部属于新时代的昆曲杰作。可惜...”他摇摇头,“生不逢时啊。 ”就在这时,琴行的门被推开了,铜铃急促地响起来。进来的是两位西装革履的男子,走在前面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气质精明的日籍男士,跟随着一位年轻得多的华人助理。 “请问是程先生吗?”助理上前开口,日语口音很重,“这位是东京大学的松本教授,专程来港拜访您。”程枫与雪衣交换了一个警惕的眼神。“请问有何贵干? ”程枫用英语问道。松本教授微微一笑,递上名片:“久闻程氏琴行大名,特别是关于昆曲大师俞沁兰的收藏。我正在做一个关于东亚传统表演艺术比较研究的课题,希望能观摩贵店收藏的《牡丹新梦》手稿。”雪衣心中一紧。来的果然是他们! 程枫不动声色:“抱歉,本店确实有一些戏曲资料,但没有什么《牡丹新梦》手稿。 您可能信息有误。”松本的脸色微微一沉,随即又恢复笑容:“程先生,我愿意出高价购买。 二十万港币,如何?这只是首期报价,我们可以再商量。”“不是价格问题,是我根本没有这件东西。”程枫冷静地回答。松本向助理使了个眼色,助理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程先生,我们有确凿证据表明程雪初先生确实保管着《牡丹新梦》的‘惊梦’篇。事实上,我们还知道另外两部手稿的下落。如果能够合集出版,将是学术界的盛事。 ”雪衣的心跳几乎停止。他们还知道另外两部手稿的下落? 难道台湾那边的苏慕云后人他们也...程枫依然摇头:“对不起,我帮不了您。 ”松本的笑容终于消失了,眼神变得冷厉:“程先生,这份手稿的价值远超你的想象。 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文化史的重要见证。留在你这里,只会随着时间腐朽。交给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保存和研究。”“香港是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化遗产自然会得到最好的保护。”程枫不卑不亢地回答,“二位请回吧。 ”松本冷冷地看了程枫和雪衣一眼,最终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们就不打扰了。 不过请再考虑一下,我还会再来。”两人离开后,琴行内的气氛一时凝重。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雪衣担忧地说。程枫叹了口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月就有人试图夜间闯入,幸好警报系统及时报警。”他沉思片刻,突然说,“沈小姐,我觉得手稿放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您既然是顾砚秋先生的传人,不如就由您保管吧。 着他:“可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先祖父的遗愿就是让它回到真正的传人手中,重现舞台。”程枫坚定地说,“我相信您就是那个人选。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我有一个请求。”“请讲。”“我希望能够参与《牡丹新梦》的复原工作。 |
精选图文
 阮南夏傅闻升免费阅读无弹窗阮南夏傅闻升(阮南夏傅闻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南夏傅闻升)阮南夏傅闻升最新章节列表(阮南夏傅闻升)
阮南夏傅闻升免费阅读无弹窗阮南夏傅闻升(阮南夏傅闻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南夏傅闻升)阮南夏傅闻升最新章节列表(阮南夏傅闻升) 黎慕星顾绍渊免费阅读无弹窗黎慕星顾绍渊(黎慕星顾绍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黎慕星顾绍渊)黎慕星顾绍渊最新章节列表(黎慕星顾绍渊)
黎慕星顾绍渊免费阅读无弹窗黎慕星顾绍渊(黎慕星顾绍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黎慕星顾绍渊)黎慕星顾绍渊最新章节列表(黎慕星顾绍渊) 伊小卿墨琛免费阅读无弹窗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最新章节列表(伊小卿墨琛)
伊小卿墨琛免费阅读无弹窗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伊小卿墨琛)伊小卿墨琛最新章节列表(伊小卿墨琛) (伊小卿墨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墨琛伊小卿阅读无弹窗)伊小卿墨琛最新章节列表(墨琛伊小卿)
(伊小卿墨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墨琛伊小卿阅读无弹窗)伊小卿墨琛最新章节列表(墨琛伊小卿) 伊小卿墨琛(墨琛伊小卿)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墨琛伊小卿)伊小卿墨琛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墨琛伊小卿)
伊小卿墨琛(墨琛伊小卿)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墨琛伊小卿)伊小卿墨琛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墨琛伊小卿) 纪远泽纪妙妙纪妙妙纪远泽(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纪远泽纪妙妙纪妙妙纪远泽(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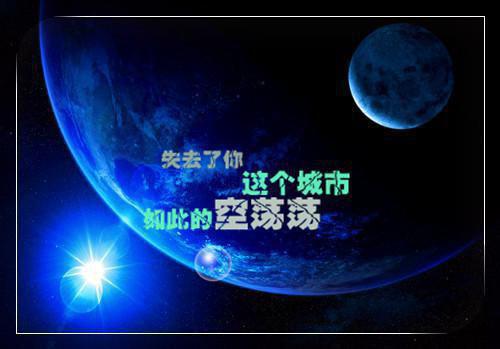 君照临慕容阀我渡佛子向红尘(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君照临慕容阀我渡佛子向红尘(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纪远泽纪妙妙纪妙妙纪远泽txt(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纪远泽纪妙妙纪妙妙纪远泽txt(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