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时空阅读网时空小说素王府的小团子娘亲,爹又来讨债了(萧彻沈青梧)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素王府的小团子娘亲,爹又来讨债了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萧彻沈青梧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素王府的小团子娘亲,爹又来讨债了)素王府的小团子娘亲,爹又来讨债了(萧彻沈青梧)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素王府的小团子娘亲,爹又来讨债了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萧彻沈青梧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素王府的小团子娘亲,爹又来讨债了)
|
透析机规律而低沉的嗡鸣声填充着整个房间。空气里弥漫着那股永远散不掉的消毒水味,混着一点若有若无的血腥气。五年了,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我像一棵强行被嫁接在机器上的植物,血液被抽离、过滤、再塞回这具日渐衰败的躯壳。 手臂上,动静脉内瘘在皮肤下虬结凸起,摸上去是温热的、搏动的,带着一种不祥的生命力。 护士熟练的消毒、穿刺,尖锐的刺痛早已麻木,只是身体深处那熟悉的、沉甸甸的疲惫感,又一次如潮水般漫上来。15:23,距离结束还有一小时三十七分钟。头有些发沉,像灌满了铅,胃里也隐隐的翻搅起来,大概是中午没有吃好。 对面床的两个阿姨正在相互抱怨着什么。我努力想听清她们在说什么,分散一下注意力,可声音飘过来,又模糊的散开,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突然,一阵剧烈的恶心毫无预兆的顶了上来,喉咙口瞬间被酸涩的液体堵住。眼前一阵发黑,无数细碎的金星在视野里乱窜,冷汗瞬间浸透了身下的床单。“小婷?小婷你怎么了? ”旁边陈姐焦急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护士!护士!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眩晕感如同实质的漩涡,要把我整个人都吞噬进去。 在彻底失去意识前,我下意识地、几乎是本能地,蜷缩起身体,一只冰凉的手紧紧护在自己的小腹上。……消毒水的气味更浓了,刺得鼻子发酸。 眼皮沉重得像坠了石头,我费力地掀开一条缝。白得晃眼的天花板,是急诊观察室。 身上盖着医院的薄被子,手臂上还连着输液管,冰凉的液体正一点点渗入血管。 主治医生杨大夫站在床边,眉头拧成一个深刻的“川”字,手里捏着一份报告单。 他身后跟着两个住院医生,表情同样凝重。“醒了?”杨大夫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他往前一步,把那份报告单递到我眼前,指尖点在几个关键的数字上,指尖有些发白。“李婷,你怀孕了。HCG值很高,孕酮也显示妊娠状态。根据末次月经推算,大概八周左右。”怀孕?这两个字像两颗子弹,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在混沌的脑子里炸开一片刺目的空白。我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巨大的荒谬感攫住了我。 一个透析了五年、肾脏功能几乎耗尽、靠机器维系着最低限度生存的人,怎么可能怀孕? 这具身体,早已被无数次的穿刺、药物的侵蚀和毒素的累积掏空了生机,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成了需要小心翼翼避免的负担,怎么可能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这……不可能……”我听到自己嘶哑的声音,虚弱得像蚊蚋。“检查结果不会说谎。 ”杨大夫的声音斩钉截铁,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直直刺向我。“但李婷,我必须告诉你,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怀孕是极其危险,不,是致命的!”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愤怒的焦灼:“你的肾脏残余功能不足10%!严重贫血!血压控制困难! 电解质紊乱是常态!怀孕会带来巨大的生理负担,血容量剧增,代谢废物翻倍,高血压随时会诱发子痫!你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它会像一座彻底垮塌的堤坝! 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他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仿佛说出那个字都需要极大的力气:“你会死!一尸两命!这个孩子也绝对保不住! ”“杨大夫……”我艰难地开口,试图辩解,却被他毫不留情地打断。“没有但是! ”他猛地挥手,那份报告单在他手中哗啦作响,“这已经不是医学问题,是基本的生存问题! 你必须立刻终止妊娠!这是唯一的、也是对你最负责任的选择!他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瞬间冻结了我心头刚刚燃起的那一丝微弱的、连自己都不敢深究的悸动。 刚刚得知怀孕时那瞬间的、连自己都不敢细想的奇异感觉,被这冰冷的宣判彻底碾碎。 我躺在那里,手脚冰凉,只觉得床旁监护仪那单调的嗡鸣声变得无比刺耳,像是为这场荒谬宣判敲响的丧钟。冰冷的绝望,比手上输的液更迅速地渗透了四肢百骸。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是闻讯赶来的陈默——那个对我“不抛弃、不放弃”的伴侣。 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脸上带着下班后的疲惫,但看到我醒了,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笑:“老婆,感觉怎么样?我熬了点小米粥,你……”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目光落在我惨白的脸上,还有我手中紧攥着的那份孕检报告单上。病房里死寂一片。 床旁的心电监护仪规律的嗡鸣声此刻听来格外刺耳。陈默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慢慢褪去,只剩下惊疑和茫然。他一步步挪到床边,眼睛死死盯着那张纸,像是要把它烧穿。 “这……这是什么?”他的声音干涩发紧,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迎上他惊恐的目光。“陈默,我……怀孕了。”“怀孕?! ”这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劈中了他。他猛地后退一步,撞在旁边的椅子上,发出刺耳的刮擦声。 保温桶从他手里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盖子摔开,温热的米汤溅了一地,甜腻的米香瞬间弥漫开来,却驱不散病房里陡然降临的寒意。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脸色瞬间变得比我还要灰败。“你……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你的身体……”他语无伦次,手指神经质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杨大夫怎么说?他肯定让你打掉!必须打掉!”猛地扑到床边,双手死死抓住我的肩膀,手指因为用力而骨节发白,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 他眼睛里布满了骇人的红血丝,恐惧和绝望像两股汹涌的浪潮在里面疯狂冲撞。“小婷! 你看着我!你想想清楚!我们好不容易才……才熬过这五年!透析!吃药!住院! 花了多少钱?遭了多少罪?我们好不容易才……才把你这条命捡回来一点! ”他的声音哽咽了,带着哭腔,“你现在跟我说你要生孩子?那是要你的命啊!你死了,我怎么办?这个孩子怎么办?他生下来就没有妈吗?啊?!”他剧烈地摇晃着我,仿佛要把这个疯狂的念头从我脑子里彻底摇出去。眼泪终于从他通红的眼眶里滚落,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得吓人。“求你了,小婷……求你了……别这样……”他的声音陡然低下去,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嘶哑,“我不能……我不能再失去你了……一次都不行……” 他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高大的身躯猛地矮了下去,膝盖重重地砸在冰冷坚硬的水磨石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跪在那一滩狼藉的米汤旁边,双手死死抱住我的腿,额头抵着我的膝盖,像个走投无路的孩童般嚎啕大哭起来,肩膀剧烈地抽动着,你……打掉吧……我们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活着……求你……”他的哭声,绝望而破碎,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地上的米汤慢慢冷却,那股甜腻的香气变得粘稠而令人窒息。我低下头,看着丈夫在我脚下蜷缩成痛苦的一团,听着他字字泣血的哀求。周大夫冰冷的宣判犹在耳边,每一个字都带着死亡的寒气。 理智像一块沉重的磐石,拖拽着我向那唯一的、被所有人认可的“生路”沉沦。是啊,打掉它。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荒谬。回到那熟悉的、虽然痛苦但至少还能喘息的透析轨道上。 对陈默,对父母,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可就在这一片冰冷的绝望和震耳欲聋的哭求声中,我的手下意识地、轻轻地、覆上了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那里,似乎传来了一丝微弱到几乎无法感知的悸动。是幻觉吗?还是血管在指尖下的搏动?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掌心贴上那片肌肤的瞬间,一种难以言喻的、极其微弱却无比坚韧的暖流,极其缓慢地,极其艰难地,从心底最幽暗冰冷的废墟深处,挣扎着渗透出来一丝。那感觉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像被遗忘在冻土之下的一粒种子,在死亡的严寒中,极其微弱地,顶开了一线缝隙。 病房的日光灯管发出恒定的、苍白的光。空气中消毒水依旧浓重。 陈默崩溃的哭声渐渐变成了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噎。我缓缓地抬起头,目光越过他颤抖的肩膀,投向窗外。天已经彻底黑透了,玻璃窗上映出室内惨白的灯光和几张模糊的病床轮廓。这间小小的、被死亡气息包围的屋子,和外面那个灯火通明、充满生机的世界,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却像隔着无法逾越的深渊。 我的指尖,还停留在小腹的位置。那里依旧平坦,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一个新生命的存在。 只有那份冰冷的报告单,还有杨大夫和陈默绝望的宣判。可心底那一丝微弱却固执的暖意,却像风中残烛的火苗,无论如何也不肯熄灭。它告诉我,深渊之下,或许还有别的路,一条布满荆棘、通向未知、甚至可能通向毁灭的路。但我,想试一试。这个念头一旦清晰,就像野草遇到了春雨,疯狂地滋长蔓延,瞬间盖过了所有的恐惧和绝望。我要试一试!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对抗谁,只是……只是因为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让我这具被机器和药物填满的身体,感受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始而蓬勃的力量。 “陈默,”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却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陌生的平静和力量。 我轻轻推了推他依旧埋在我腿上的头,“起来。”他猛地抬起头,脸上泪痕交错,眼睛里还残留着巨大的恐惧和一丝微弱的、不敢置信的期盼。“我要留下他。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陈默眼中的那点微光瞬间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惊骇和一种被彻底背叛的痛楚。“你疯了!你真的疯了! 大夫的话你没听见吗?你会死的!”他猛地站起身,因为跪得太久踉跄了一下,双手激动地在空中挥舞着,声音尖锐刺耳,“你就这么想死? 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的东西,你要丢下我?丢下爸妈?丢下所有的一切?你自私! 你太自私了!”“我不是自私!”一股莫名的火气冲了上来,我撑着虚弱的身体坐直,声音也拔高了,“陈默,你看看我!你看看这五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猛地拉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和凸起的、蚯蚓般的动静脉瘘管,“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 像块烂肉一样被绑在透析机!我的血被抽出来,过滤,再灌回去!五年!一千八百多个小时!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等着下一次透析吗?就是为了在这消毒水味里慢慢烂掉吗? ”我的胸口剧烈起伏着,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一种积压了太久太久的愤怒和委屈。“是!我身体是烂透了!我可能明天就死了! 但至少现在!至少现在……”我用力按住自己的小腹,指甲隔着薄薄的病号服掐进了掌心,“这里!这里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是我身体里长出来的!他不是机器!不是药片! 不是你们嘴里说的‘那个东西’!他是我的孩子!是我李婷的孩子! 他是我这五年……这五年灰色透顶的日子里,唯一透进来的一束光!你懂不懂?!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在狭小的病房里回荡,震得耳朵嗡嗡作响。吼完这一通,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我瘫软在枕头上,大口喘着气,胸口火辣辣地疼。 陈默被我突如其来的爆发惊呆了,他怔怔地站在原地,脸上的愤怒和指责凝固了,只剩下一种深重的茫然和痛苦。他看着我,又看看我护着小腹的手,嘴唇哆嗦着,最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病房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还有监护仪那永不疲倦的、规律而冰冷的嗡鸣。……几天后,我回到那个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透析室。空气里消毒水和血的混合气味一如既往地浓重。 机器规律的嗡鸣,针头刺入内瘘时的微痛,血液在透明管路里奔流的景象……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彻底不一样了。护士刚给我扎完针,旁边床的陈姐扭过头悄声的问我:““小婷,听说……有‘情况’了?” 她刻意压低了“情况”两个字。”陈姐是个直肠子,五十多岁,胖胖的,透析了七年,是这里的“元老”。问我话的时候她没看我,眼睛盯着对面墙上贴着的“注意卫生”宣传画。我的心猛地一跳,攥紧了拳头。 陈姐怎么知道的?杨大夫?护士?还是陈默……没等我回答,旁边床的老刘,一个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退休教师,也慢悠悠地开了腔,眼睛依旧看着手里的报纸:“老话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抖了抖报纸,翻过一页,“可这‘福’啊,有时候看着,也忒吓人了点。”语气平淡,听不出褒贬。 斜对面一个做透析的年轻女孩,小雅,才二十出头,突然放下手机,转过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好奇和莽撞:“婷姐,是真的吗? 你要生宝宝啦?天啊!那……那他她在里面,会不会也……也怕这机器啊? ”她指了指旁边正在运转的透析机。“胡说什么呢!”护士长正巧过来检查我的参数,板着脸训斥了小雅一句,然后转向我,动作麻利地调整着透析的各种参数。她没看我眼睛,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公式化的关切:“李婷啊,杨主任特别交代了,你现在情况特殊,透析方案要调整,时间可能更长点,血流量也不能太大,怕你心脏受不了,也怕影响……呃,胎儿供血。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有没有特别不舒服?头晕?心慌? 恶心厉害吗?”透析机规律地嗡鸣着,像一只冰冷的巨兽伏在床边呼吸。 冰凉的血浆在管子里循环,带走毒素,也似乎抽走我残存的力气。小雅的问题像一根细针,出其不意地扎进紧绷的神经。怕这机器?我的手下意识地覆上小腹,隔着薄薄的病号服和底下更薄的皮肤。那里依旧平坦,安静,像一个安静的谜。“他? ”我低头看着自己微微起伏的小腹,那里被透析机冰冷的声音笼罩着。一瞬间,某个念头清晰地闪过脑海——它被羊水温柔地托举着,轻轻摆动着小小的身体。“不,”我抬起头,目光掠过一张张或担忧、或好奇、或麻木的脸,最终停在护士长温和的侧脸上,声音虚弱却带着一种奇异的肯定,像在浑浊的水里点亮一盏微弱的灯。 “他……大概是在游泳吧。”我自己也被这个脱口而出的比喻惊了一下,眼前仿佛真的晃过一条小鱼,在幽暗温暖的水里,懵懂而轻盈地摆着尾巴,全然不知身外世界的冰冷喧嚣。“游泳?”小雅睁大了眼,像是听到了最不可思议的童话。 护士长调整参数的手指顿了一瞬,她终于侧过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像幽深的潭水,有惊异,有深重的忧虑,或许还有一丝难以捕捉的……触动。 她没有说话,只是更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管路,然后轻轻拍了拍我扎着针的手臂外侧,很轻的一下,像一片羽毛落下。“…好好游。”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随即转身走向下一个病床,白色护士鞋踩在光洁的地面上,没有一丝声响。陈姐猛地扭过头,胖胖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小婷!你……”“在羊水里游泳呢,”老刘慢条斯理地翻过一版报纸,头也没抬地接了一句,混浊的语调里辨不出情绪, |
精选图文
 陆皎皎季晏礼免费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陆皎皎季晏礼小说免费阅读)陆皎皎季晏礼最新章节阅读
陆皎皎季晏礼免费阅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陆皎皎季晏礼小说免费阅读)陆皎皎季晏礼最新章节阅读 热门小说推荐陆皎皎季晏礼 陆皎皎季晏礼在哪免费看
热门小说推荐陆皎皎季晏礼 陆皎皎季晏礼在哪免费看 陆皎皎季晏礼新书陆皎皎季晏礼看全文小说-陆皎皎季晏礼小说资源阅读陆皎皎季晏礼
陆皎皎季晏礼新书陆皎皎季晏礼看全文小说-陆皎皎季晏礼小说资源阅读陆皎皎季晏礼 梁沐荞江鹤时是什么小说-梁沐荞江鹤时免费小说在线阅读
梁沐荞江鹤时是什么小说-梁沐荞江鹤时免费小说在线阅读 梁沐荞江鹤时小说全文完整版 梁沐荞江鹤时免费阅读
梁沐荞江鹤时小说全文完整版 梁沐荞江鹤时免费阅读 陆皎皎季晏礼全文(陆皎皎季晏礼免费小说-完整版-陆皎皎季晏礼在线赏析)最新章节已更新版
陆皎皎季晏礼全文(陆皎皎季晏礼免费小说-完整版-陆皎皎季晏礼在线赏析)最新章节已更新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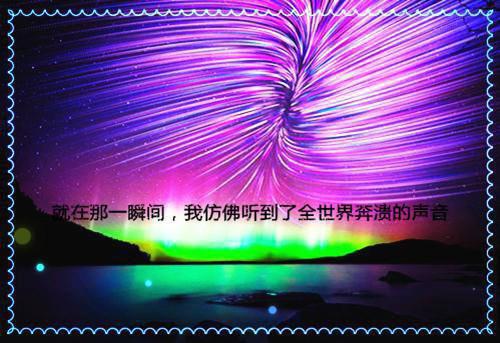 【新书】许溪蒋震霆全文全章节免费阅读-退婚后,八零肥妻被糙汉娇宠了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新书】许溪蒋震霆全文全章节免费阅读-退婚后,八零肥妻被糙汉娇宠了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楚小梨萧淮小说(楚小梨萧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楚小梨萧淮小说小说楚小梨萧淮小说列表(楚小梨萧淮)
楚小梨萧淮小说(楚小梨萧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楚小梨萧淮小说小说楚小梨萧淮小说列表(楚小梨萧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