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强林美娜(邻居假孕让全楼关WIFI我怒了)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邻居假孕让全楼关WIFI我怒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
|
林婉兮再睁眼,是铺天盖地的红。猩红的嫁衣、猩红的被褥、猩红的“囍”字,像谁拿一桶滚烫的血,兜头泼下。她条件反射地坐起,额角抽疼,一段陌生记忆猛兽般闯进脑海——原主,同名同姓,礼部侍郎林府的嫡长女。 今日奉旨嫁入摄政王府,给那位传言“夜眠枕剑、醒握生死”的摄政王萧景行冲喜。 花轿进门才一炷香,原主便被人“不慎”推入莲池,捞上来时早已气绝。而现在,她这缕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社畜幽魂,鸠占鹊巢。“小姐——”丫鬟春杏扑到床前,泪如雨下,“您可算醒了!方才池边只有二小姐跟您站着,一定是她——”话音未落,门外脚步声细碎,环佩叮当。林婉兮抬头,正见一名素衣少女被嬷嬷搀着踏进内室。少女小脸苍白,杏眼噙泪,走三步咳一声,柔弱得仿佛风再大一点就能吹成纸蝶。林晚晴——原主同父异母的庶妹,也是这本书里笑到最后的“替身白月光”。书中情节电闪雷鸣般掠过:林晚晴先夺嫡姐的婚,再夺嫡姐的命,最后顶着一张“神似先皇后”的脸,被新帝纳入中宫,荣宠一生。 林婉兮眯眼,掌心不自觉攥紧。下一秒,她耳边忽然炸开一道嗓音——姐姐最好再晕半日,误了吉时,摄政王怪罪,这桩婚事才能黄了。届时我哭一哭,姨母再求一求,皇后懿旨指不定就落到我头上。那声音轻软甜腻,与林晚晴满脸关切完美重合,却分明是少女肚里蛔虫,字字阴毒。林婉兮心跳骤停——谁在说话?“姐姐,你冷不冷? ”林晚晴俯身,小手探向她额头,袖口散出淡淡茉莉粉香。啧,命真硬,这样都淹不死。
算了,先让她躺着,夜里再送一碗“驱寒汤”下去,明早便是暴毙,谁也查不出。 林婉兮后背瞬间爬满冰碴。她确定——自己听见了林晚晴的心声!“妹妹有心。 ”她压下惊涛骇浪,学着大家闺秀的腔调,柔柔开口,“只是方才落水,脑子进了水,听人说话总带着回音,怕惊了贵客。”林晚晴眼中闪过一丝狐疑,旋即笑出一对梨涡:“姐姐说笑了,哪有什么回音。”蠢货,怕不是吓得幻听?也好,省得我多费唇舌。林婉兮低眉,盖住眼底冷意。幻听?那便幻听到底——“春杏,扶我起来。”她嗓音轻,却不容拒绝,“今日大婚,误了吉时,摄政王怪罪,林府吃罪不起。 ”春杏愣住,林晚晴也愣住。按照计划,这位“怯懦长姐”应卧床不起,最好高烧惊厥,让喜娘直接回禀“八字不合,婚事作废”。她竟敢起身?!林晚晴急了,伸手去拦:“姐姐脸色太差,王爷若知晓,定会怜惜——”“怜惜?”林婉兮抬眸,第一次直视这位白莲妹妹。她眼尾微翘,带着久病未愈的水红,却凉得吓人,“妹妹莫非忘了,王爷枕边枕剑,最厌晦气。我若病恹恹拜堂,才是真的罪该万死。 ”她怎么突然牙尖嘴利?林晚晴心头一跳,嘴角僵硬:“妹妹只是担心姐姐身子……”“担心?”林婉兮忽然伸手,握住林晚晴腕子,指尖冰凉,“那便请妹妹陪我一同梳妆。我若晕厥,妹妹也好即刻接手,莫让喜事变丧事。 ”她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让满屋仆妇听个真切。众人脸色瞬间精彩——嫡小姐这话,等于当众扒掉二小姐最后一块遮羞布。林晚晴脸色青白交错,挣了挣,竟没挣开。 林婉兮指骨纤细,却像铁箍,掐得她生疼。疯子!她想拉我陪葬?林婉兮笑而不语,只觉脑海“叮”一声,仿佛某根弦被拨动——半径五米内,无数嘈杂蜂拥而至:二小姐这回要栽了……大姑娘平时闷不吭声,原来是个狠角色。 快去看热闹,据说摄政王已至前厅,那张脸比阎王还冷!林婉兮闭眼,深呼吸。 原来这就是“读心”,像把一把双刃剑,瞬息剖开所有皮囊,露出底下蛆虫般的算计。 她压下胃底翻涌,借春杏的力起身,脚跟虚浮,却步步稳健。“走,去梳妆。”铜镜前,喜娘战战兢兢替她净面。林婉兮抬眼,镜面女子黛眉纤纤,一双鹿眼却沉如寒潭。 她指腹摩挲鬓角,无声盘算——按书中时间线,今夜“她”会在婚房暴毙,摄政王连她衣角都没碰,便披麻戴孝,成了全京城最年轻、最俊的“鳏夫”。 林晚晴趁虚而入,三个月后在皇后寿宴上“意外”与王爷同困一室,自此青云直上。如今,炮灰长姐换了芯,还想让她乖乖当垫脚石?做梦。一刻钟后,林婉兮着大红翟衣,戴九翚四凤冠,沉甸甸的金口箍得她头皮发麻。她站在廊下,远远瞧见前厅那道玄色身影。 男人背对人群,负手立于丹墀,肩背挺拔,像一柄收鞘的剑,冷冽、锋利、不见血不归。 似是察觉视线,他微微侧首,日光在他脸上劈出半明半暗的线,高鼻、薄唇、深目,每一寸都像刀凿,冷得惊心。——摄政王萧景行。林婉兮心口莫名一紧,耳边却再度捕捉到一道极低的嗓音,不同于任何人:林家嫡女?竟没淹死。 那声音磁而凉,像雪夜划过的刀锋,带着淡淡血腥气。她骇然——这是萧景行的心声? 可两人相距足有十丈,远超五米!她不确定地往前一步,声音果然更清晰:命硬些也好,省得本王再背一条克妻名声。林婉兮脚下一顿,差点崴了。克妻? 原来外界传他“天煞孤星”,并非空穴来风。她稳住身形,再抬眸,正对上萧景行扫来的目光。男人眸色极黑,像两片冰湖,浮着细碎冷光。他淡淡打量她,似在评估一件货物是否合格。半息,他收回视线,心声亦跟着敛去,再不可闻。 林婉兮掌心渗出潮汗。她确定,自己能听见萧景行的心声,且距离限制对他无效——为什么? 因为他是男主?还是别的?她来不及细想,喜娘已扬起嗓音:“吉时到——”鼓乐齐鸣,林婉兮被簇拥着前行。跨过火盆时,她故意踉跄,袖中指尖轻弹,一抹香粉无声洒落。 那粉末遇火即燃,幽蓝火苗“噗”地窜起,燎着林晚晴拖地的裙角。 “哎呀——”林晚晴尖叫,慌不择路去踩,却越踩越燃,一时间焦糊味四溢,宾客哗然。 她顾不得形象,双手扑打,露出雪白小腿,哪有半分闺秀模样?林婉兮回头,冲她“关切”一笑,无声吐字:“妹妹,别急,火要旺,才显得热闹。”贱人! 她一定是故意!林晚晴心声尖利,几乎破音。林婉兮听得清清楚楚,却愈发从容,转身,将手放入萧景行掌心。男人指尖冰凉,掌心却有厚茧,像一把鞘中藏刃的剑。他低眸看她,眸底无波,心声却再次响起——林家嫡女,似乎比传闻有趣。林婉兮垂眸,唇角微弯。 有趣?那就拭目以待。拜天地、入洞房,整套流程下来,林婉兮脊椎几乎断成三截。 喜房门窗紧闭,红烛高烧,她端坐在百子千孙帐下,屏息凝神——小姐,药已下在交杯酒,只要一口,明早便暴毙。是春杏的声音?不,是春杏的心!那丫头低眉顺眼,手捧鎏金鸳鸯壶,指尖却微颤。林婉兮抬眼,恰对上她闪躲的眸。 原来连原主贴身丫鬟都被收买。她心底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接过酒杯,指尖在杯沿轻轻一抹——“王爷还未至,我口干,先润润。”她仰头,将酒含在口中,袖口掩面,实则暗吐于帕。下一秒,她手一抖,“不慎”打翻另一杯,酒水溅湿春杏裙摆。 “奴婢该死!”春杏扑通跪下,脸色惨白。林婉兮弯腰去扶,借位遮掩,飞快将两杯酒调包。 “无妨,再斟便是。”她温声劝,亲手递回一杯。春杏心虚,哪敢再劝,颤着手退出内室。 门扉阖上,红烛爆了个灯花。林婉兮长舒口气,正欲起身,忽听“咔哒”一声——窗棂被推开,一道玄黑身影翻窗而入,轻得像猫。男人背光而立,腰间佩剑冷光流转,正是萧景行。林婉兮呼吸滞住。按规矩,新郎应于前厅敬酒,三鼓后入房。此刻不过二鼓,他怎就来了?萧景行扫她一眼,似笑非笑:“本王不喜热闹,提前散席。”顿了顿,他心声悠然响起——林晚晴派人在酒里下毒,本王懒得陪她演。 倒是这位嫡女,不知能否给本王惊喜。林婉兮指尖收紧。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却故意袖手旁观。她抬眸,弯出温婉弧度:“王爷既知酒有问题,不如——”她取过酒壶,将残酒倒入花盆,动作优雅,“我们换一壶?”萧景行挑眉,深眸里终于浮上一丝真切的兴味。他缓步走近,俯身,嗓音低哑:“合作愉快,王妃。 ”烛火“啪”地炸开,映得两人影子交叠,像一柄并蒂的刃,寒光潋滟。窗外,夜色正浓,一场更大的火,才刚点燃。红烛高烧,喜房静得能听见烛芯吸油的“咝咝”声。林婉兮抬眼,咫尺之外,男人玄袍未解,冷白指骨托着鎏金杯,杯壁映出他狭长眼尾,像一弯薄刃,随时割喉。“合作愉快,王妃。”萧景行声音极轻,却惊得她后颈寒毛倒竖。她稳住呼吸,取过另一只空杯,斟入清茶,推到他面前:“王爷既求合作,先表诚意——毒酒我已倒掉,接下来该您了。”萧景行低笑一声,指尖在桌面轻敲,心声顺着节奏钻进她耳膜——林家嫡女,胆子比池水大。她若真能与本王互利用,留她一命又何妨。林婉兮心下微松,面上却不动声色:“王爷所求,不过三件事:一,查清母妃薨逝真相;二,稳住朝局;三,解自身奇毒。巧了,我所求也三件:一,活下去;二,护住我生母嫁妆;三,让林晚晴母女血债血偿。目标不冲突,可以结盟。 ”她语速极快,逻辑分明,像在会议室做PPT汇报。萧景行听完,眼底兴味更浓,忽然俯身,薄唇贴着她耳廓,用仅两人能闻的声音道:“本王再加一条——一年之内,不许让本王背上‘克妻’之名。”灼热呼吸拂过,林婉兮耳尖瞬间红透,却硬生生忍住后退的冲动,抬眸与他平视:“成交。一年之内,我若暴毙,算我违约;王爷若先毒发,也算违约。”“好。”男人退开半步,拾起桌上茶杯,以茶代酒,与她轻碰。瓷杯相击,“叮”一声脆响,像无形的契约落章。窗外打更声恰好掠过,二鼓过半。林婉兮放下杯,正欲开口,忽听廊下传来细碎脚步——再探一探,若已毒发,便报二小姐;若还喘气,再补一刀。是林晚晴的乳母陈嬷嬷!她眸色一冷,朝萧景行比了个“噤声”手势,快步走到门边,指尖沾湿窗纸,捅出小孔——陈嬷嬷佝偻着背,袖中寒光一闪,分明攥着把薄如柳叶的匕首。林婉兮回头,用口型道:“王爷,借剑一用。”萧景行挑眉,解下腰间佩剑“听雪”,连鞘递给她。 剑一入手,她腕间陡沉,险些坠地——好重!这男人平日怎么做到单手杀人的? 她咬牙双手抱剑,深吸一口气,忽然“哗啦”拉开门,冲外头软软唤:“陈嬷嬷,可是妹妹不放心我?进来吧。”陈嬷嬷没料到她主动开门,愣了半息,立刻堆出慈祥褶子:“老奴给王妃送醒酒汤。”“辛苦。”林婉兮侧身让路,背对烛火,脸埋在阴影里,笑得阴恻恻。陈嬷嬷前脚跨过门槛,后脚还未落地,猛地察觉房中另有呼吸。 她抬头,撞进一双幽黑冷眸——萧景行!?王爷怎么在?!心神俱裂的一瞬,林婉兮抡起听雪,用尽全力砸向她后颈。剑鞘裹着铜片,重击之下,陈嬷嬷连哼都没哼,软绵绵倒地,匕首“当啷”滑出袖口。林婉兮喘了口气,第一次干“背后敲人”的勾当,掌心震得发麻。她抬头,见萧景行正单手托腮,懒洋洋看戏,心声愉悦——力道差些,准头尚可,像只刚长牙的小豹子。林婉兮:“……”她蹲身探陈嬷嬷鼻息,确定只晕过去,才抬头:“得把她拖走,明日我回门,正好送她一份大礼。”萧景行抬手击掌,暗处立刻掠出两名玄衣侍卫,像影子一样贴地出现,无声无息把人抬走,连地板血迹都擦得干干净净。林婉兮眼皮直跳——这就是权力巅峰的可怕,杀人灭口只需抬抬手指。“吓到了?”萧景行走近,语气竟有一丝安抚。林婉兮摇头,站起身,拍了拍裙角:“只是感叹,王爷的刀快,我的刀也得磨快点,免得拖您后腿。 ”萧景行低笑,忽地伸手,指腹拂过她鬓边——那里溅了一滴陈嬷嬷的血,猩红刺目。 “夜已深,安置吧。”他自然地收手,仿佛方才的暧昧只是错觉,转身走向屏风后的小榻,“本王睡外间,王妃自便。”林婉兮愣住:“王爷不睡床?”“本王惜命,怕半夜有人再送毒酒。”他半真半假地回了句,人已合衣躺下,呼吸瞬间绵长。 林婉兮:“……”她环顾喜房,大红锦被,鸳鸯绣枕,百子千孙帐飘啊飘,活像讽刺。 谁能想到,洞房花烛,夫妻各守一榻,中间还横着条“同盟”刀?她无声吐了口气,和衣上床,放下罗帐,却不敢深眠,竖着耳朵数更。四更鼓过,窗外忽有夜枭啼叫,短促三声。萧景行心声立刻在她脑海响起——来了。林婉兮秒醒,刚坐起,便见窗纸被竹管捅破,一缕淡青烟雾蜿蜒而入。“迷香?”她无声用口型问。 萧景行已闪至窗边,两指夹住竹管,反向吹了一口,外头立刻传来闷哼。他打开窗,拎小鸡一样拎进一名黑衣人,顺手卸了下巴、卸了四肢,全程不超过三息。 林婉兮看得目瞪口呆,心里飞快记下——这男人武力值天花板,得抱紧。“问吗? ”她指黑衣人。“不必,死士。”萧景行淡淡道,抬手就要拧断对方脖子。“等等! ”林婉兮急叫,跳下床,蹲到黑衣人面前,盯着他眼睛,凝神——任务失败,咬毒……她刚捕捉到心声,黑衣人已经唇角黑血溢出,头一歪,死了。 萧景行挑眉:“你能问魂?”林婉兮心知露馅,飞快思索,半真半假:“妾身幼遭头疾,偶有幻听,方才似闻他欲咬毒,才出声阻止,不想还是晚了。”萧景行深深看她一眼,没追问,只道:“本王会派人查尸源,你早些睡。”说罢,将尸体裹进黑布袋,扔出窗外,自有暗卫接手。林婉兮回到床上,却再也睡不着。短短半夜,两条人命从她眼前掠过,而始作俑者连面都没露。她意识到,自己穿进的并非单纯宅斗副本,而是朝堂与后宅交织的修罗场。林晚晴、三皇子、甚至深宫那位太后,都想拿她当投石问路的石子。而她唯一的外挂,是“读心”,以及——榻边那把“听雪”。 天蒙蒙亮,她起身,走到小榻前,俯身,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道:“王爷,合作愉快的第一步,回门之日,借我十名暗卫,三名账房,再借‘听雪’一用。 ”萧景行睁眼,黑眸清醒得像从未入睡,半晌,薄唇轻启:“准。”本王倒要看看,这只小豹子,如何撕碎第一头猎物。林婉兮笑得眉眼弯弯,退后一步,拱手:“妾身定不负王爷……看戏的钱。”窗外,曙色破晓,第一缕晨光穿过雕花窗棂,落在她脚边,像一柄刚刚出鞘的刀,寒光四溢。辰时三刻,摄政王府正门洞开。 朱漆铜钉大门左右列戟,十名玄衣暗卫鱼贯而出,雁翅般排开。中间一人,玄袍玉带,腰悬听雪,身形挺拔如剑——正是萧景行。林婉兮随后踏出,一袭绛红织金对襟长裙,裙摆以银线暗绣星斗,行走间寒光点点。她发间只簪一支羊脂玉簪,通身无多余珠翠,却衬得肤色胜雪,眉目沉静,与昨日喜房执剑敲人的模样判若两人。今日回门,她竟不戴凤冠?萧景行侧眸,心声低低掠过耳畔。林婉兮勾唇,同样以心声“回敬”——她知晓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却听不见内容,于是用只有彼此明了的默契,抬手轻抚他佩剑,指尖在剑鞘敲出极轻的三下:借我。 男人眼尾微挑,似笑非笑,翻身上马。车队启行,暗卫三人易作账房先生,七人扮小厮,悄无声息混入林府随行仆从。车轱辘碾过朱雀大街,百姓远远避让,却忍不住探头——“摄政王亲自陪王妃回门?不是说这位王妃活不过三日? ”“嘘——命硬着呢!听闻昨夜王府抬出两具黑衣尸,王爷却连眼都没眨。 ”议论声顺着风钻进马车,春杏跪在车厢角,脸色惨白。林婉兮斜倚绣墩,翻着一本空白账簿,笔尖蘸朱砂,慢悠悠在封面写下两个篆字——“索命”。……林府正门。 林侍郎林德庸率阖府女眷立于阶下,远远望见摄政王仪仗,腿肚打颤。林晚晴立于人后,一身素月纱裙,鬓边白兰轻颤,弱柳扶风,仿佛风一吹就要为长姐哭丧。车帘挑起,林婉兮探身而出,目光掠过众人,最后停在林晚晴脸上,微微一笑。 林晚晴心口猛地一跳——她怎么没病没痛?陈嬷嬷昨夜未归,难道失手? 林婉兮踩着矮凳下车,指尖在袖内轻弹。下一瞬,两名暗卫押着被捆成粽子的陈嬷嬷,重重扔在林府门前!“哎呀——”女眷惊叫四散。陈嬷嬷嘴被破布堵住,额头磕破,血糊了半张脸,挣扎着望向林晚晴,眼里全是求救。林德庸吓得魂飞魄散:“王爷,这……这是何意?”萧景行负手而立,声音淡漠:“本王家奴,夜闯主院,被当场拿下。 念其乃林府旧仆,特送回交由岳翁发落。”“旧仆”二字,像两记耳光,扇得林德庸老脸通红。他一脚踹向陈嬷嬷:“恶奴!摄政王殿下面前也敢造次! ”林婉兮缓步上前,弯腰,亲手扯出陈嬷嬷口中破布,温温柔柔:“嬷嬷,别怕,父亲会给你做主。昨夜你说二小姐指使你给我送‘驱寒汤’,汤里加了什么,再复述一遍即可。”陈嬷嬷浑身一抖,下意识看向林晚晴。林晚晴“扑通”跪倒,泪如雨下:“姐姐明鉴!晚晴万万不知嬷嬷竟包藏祸心!她定是被人收买,想离间我们姐妹! ”老东西,若敢攀咬我,你孙儿性命不保!她心声尖利,林婉兮听得一清二楚,面上却叹口气:“妹妹说得是,一个奴才罢了,怎敢随意攀扯主子?”她抬眸,望向林德庸:“父亲,陈嬷嬷私闯王府,按律当杖八十,流放三千里。可她年过半百,怕是熬不过三十棍。女儿念其奶过妹妹一场,愿网开一面——只打二十棍,撵出京城,永不得回,可好?”林德庸哪敢说不好,连连点头:“王妃仁善!”暗卫得令,当众将陈嬷嬷按在长凳上,水火棍抡圆——“啪!”第一棍下去,皮开肉绽,陈嬷嬷惨叫划破长空。林晚晴脸色煞白,指甲掐进掌心,却听林婉兮用仅她可闻的声音低笑:“妹妹,别急,这才第一棍。二十棍后,她若还有气,我会让大夫吊着她的命,送去岭南——你外祖家地盘,路上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对么? ”林晚晴猛地抬头,正对长姐含笑的眼睛,那眸子冷而亮,像冬夜悬刀,瞬间割破她所有伪装。她心跳失序,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她知道了! 她什么都知道!棍棒声里,林婉兮转身,扶住林德庸手臂,声音哽咽:“父亲,咱们进去吧,女儿有体己话同您说。”林德庸早已冷汗涔涔,连声称好,引着摄政王与女儿入府。女眷们簇拥跟随,再无人敢看林晚晴一眼。……正堂。 萧景行高居主位,林德庸陪坐下首,林婉兮立于堂中,抬手——三名账房先生抱着厚厚账册而入,一一摊开。“父亲,母亲早逝,女儿出嫁前未能尽孝,如今回来,只想拿回母亲留下的嫁妆,好让她老人家在九泉安心。 ”林德庸脸色一僵。林府账面早被林夫人柳氏掏空,原主生母顾氏百万嫁妆,十之七八填了林府亏空,剩下的换成田庄、店铺,全写在林晚晴名下! 林婉兮似笑非笑:“怎么?父亲为难?可女儿手上有母亲当年嫁妆清单,加盖礼部印鉴, |
精选图文
 程小枫魏昭全文(程小枫魏昭)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程小枫魏昭全文最新章节列表(程小枫魏昭)
程小枫魏昭全文(程小枫魏昭)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程小枫魏昭全文最新章节列表(程小枫魏昭) 容砚礼温芸兰(温芸兰容砚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容砚礼温芸兰)
容砚礼温芸兰(温芸兰容砚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容砚礼温芸兰) 许清矜梁鹤珣(许清矜梁鹤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清矜梁鹤珣小说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许清矜梁鹤珣小说)
许清矜梁鹤珣(许清矜梁鹤珣)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清矜梁鹤珣小说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许清矜梁鹤珣小说) 萧辞姜小卿(萧辞姜小卿知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萧辞姜小卿无弹窗)
萧辞姜小卿(萧辞姜小卿知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萧辞姜小卿无弹窗) 温芸兰容砚礼(温芸兰容砚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芸兰容砚礼小说最新章节列表(温芸兰容砚礼)
温芸兰容砚礼(温芸兰容砚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芸兰容砚礼小说最新章节列表(温芸兰容砚礼) 2023年精选热门小说苍凌隐越念(越念苍凌隐)-(越念苍凌隐)越念苍凌隐免费阅读
2023年精选热门小说苍凌隐越念(越念苍凌隐)-(越念苍凌隐)越念苍凌隐免费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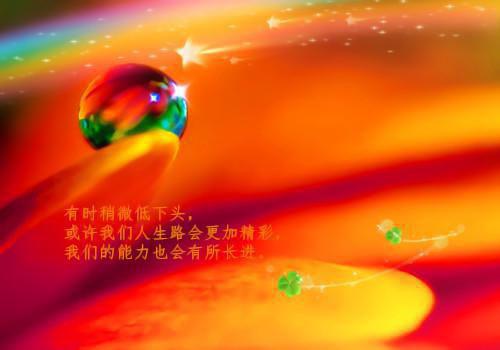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洛枝梁君泽)许洛枝梁君泽最新章节列表(许洛枝梁君泽)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洛枝梁君泽)许洛枝梁君泽最新章节列表(许洛枝梁君泽) 《顾云汐君夜玄TXT》年代好文分享阅读_《顾云汐君夜玄TXT》宝藏文学书荒必读分享
《顾云汐君夜玄TXT》年代好文分享阅读_《顾云汐君夜玄TXT》宝藏文学书荒必读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