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抢我功法给师妹,可功法假的(裴砚之叶蓁)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_最新小说全文阅读相公抢我功法给师妹,可功法假的裴砚之叶蓁
|
梅雨落不停。江湖在滴血。九大派,玄枢盟约,纸包不住火。我爹死在那夜,剑谱未交。 我嫁入青锋门,是联姻,也是棋子。裴砚之,温润如玉,执剑时眉都不皱。他待我敬重,却总望着叶蓁笑。那个他亲手带回的孤女。寒山剑派的残卷,我没全交。留一手,是活路。 可他剑尖抵我咽喉那夜——我才知道,敬重,不等于爱。功法给他。心,碎了。和离书,我亲自写。后来他跪着求我回来。晚了。这江湖,该换个人执剑了。1江南六月,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檐角的水珠一滴一滴砸在青石板上,像针,扎进我心里。我坐在婚房里,凤冠还戴在头上,红嫁衣也没换。烛火跳了三寸,门才响。裴砚之进来了。他一身墨青长衫,眉眼清俊,是外人嘴里常说的“玉面剑郎”。他看了我一眼,点头,便走到窗前,站定,目光穿雨而出,落在院子中央那个练剑的人影上。叶蓁。青锋门收养的孤女,十七岁,长得干净,眸子像雨后的溪水,清得能照见人心。初见她时,我觉得她怯,低着头,手指绞着袖角,像只淋湿的雀儿。可她练剑的样子,不像雀儿。她出剑极快,身形轻巧,雨水在她剑尖上炸开,像碎玉飞溅。转折处,手腕一压,剑势微顿——那一瞬,我心头一紧。 那是“断雪式”的起手。寒山秘传,外人绝不可能会。我坐在原地,没动。 手却慢慢攥紧了袖中的素银簪。冰凉的簪尾硌着掌心,提醒我还醒着。这不是巧合。
父亲死前,血溅宗祠,我躲在梁上,看着九大派围杀他。他们要《九章剑谱》,父亲说:“剑可断,谱不可辱。”头颅落地时,他眼睛还睁着。我活下来,不是为了哭。 现在我嫁进青锋门,成了裴砚之的妻子。这婚事是盟约,不是姻缘。我不求爱,只求一线活路,一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可新婚夜,他看都不看我,只看着别人练剑。 我整了整衣袖,起身,缓步走到窗边。烛光映在窗纸上,照出庭院的倒影。我借着那层薄影,盯着叶蓁的剑路。她又使了一次“断雪式”,这次更明显,是第二式“断雪拂柳”。 我轻咳一声。裴砚之回过头。他眼底还有未散的光,像是刚从什么深境里拔出来。看见我,那光淡了。“夜深了。”他说,“歇下吧。”我没应。他也没再看我,转身进了内室。 门合上,屋里只剩我和烛火。我站着,没动。雨水顺着瓦片滑下,在窗纸上画出歪斜的线。 这一夜,还没完。第二天清晨,我换了素色衣裙,去执事长老那儿领门务。我是少夫人,理内务名正言顺。长老年迈,说话慢,递给我一摞账册时,眼神有点躲。 “叶蓁姑娘的供养名册,也在这儿?”我问。他顿了顿,“她……是少主亲自照料的,日常用度另记。”“可她是门中人。”我低头翻册子,“我既管事,总得知道每一个人的来处。”他犹豫片刻,还是抽出一本薄册递来。我道谢,带回房。夜里,我点灯翻查。叶蓁入门前的记录被烧过,只剩半页。上面写着:“拾于寒山道北,年约六岁,无名无籍。”寒山道北?那是寒山剑派后山,当年我父亲遇袭的地方。我指尖一颤。继续翻。 账册夹着一张练功日志,是裴砚之的笔迹:“蓁儿今日悟性极佳,断雪三式已通其二。 此子若成,青锋有望。”断雪三式。我父亲亲传,连我都是十二岁后才开始学。 叶蓁一个外人,十六岁就通了两式?我合上册子,心沉到底。不是她天资过人。是有人教。 而教她的人,批了这行字。我盯着那页纸,直到烛芯“啪”地炸开。第三天清晨,我等在裴砚之练剑归来的路上。他收剑入鞘,额上带汗,看见我,脚步微顿。 我捧着茶盏上前,声音轻:“昨夜雨大,叶蓁还在练剑,我远远瞧了一眼。她剑法灵动,竟有些寒山风骨,是我眼花?”他抬眼,目光沉了沉。我没低头,也没躲。半晌,他道:“她天资过人,我不过点拨一二。”说完,绕过我,走了。茶盏在我手里,慢慢凉透。 我站在原地,没追,也没喊。我知道了。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愿说。而那沉默,比刀还利。 我回房,取下素银簪,放在案上。簪子很旧,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东西。我没戴金玉,只戴它,像带着一把藏在发间的剑。我翻开《青锋门规》,一页页看下去。 内务、账目、弟子名录、孤女安置——我一条条记,一笔笔理。第三天傍晚,我去了练武场。 叶蓁正在练剑。她看见我,收剑行礼,动作标准,语气柔:“少夫人。”我点头,“练得勤。 ”“不敢懈怠。”她低头,“少主说,剑不离手,心才不乱。”我笑了笑,“你跟少主学了多久?”“五年了。”她声音轻,“他待我如妹。”“那真是你的福气。 ”我说。她抬头看我,眼里还是那副干净模样。可我看得清楚——她握剑的手,虎口有茧,是长期发力的痕迹。但她的步伐,太稳,太熟,像是从小就在寒山后山练过无数次。 我转身离开。回房后,我写了一张单子:近五年门中所有外出采买、药草记录、孤女衣物尺寸、膳食清单。明天,我要去库房。我要知道,一个“孤女”,五年间,到底花了多少银子。晚上,雨又下了。 我坐在窗前,听着檐下滴水声。父亲的声音又浮上来:“剑可断,谱不可辱。”我闭了闭眼。 我不是来当少夫人的。我是来活命的。也是来查清一切的。叶蓁不该会“断雪式”。 裴砚之不该沉默。一个在雨中练剑的孤女,一个眼神飘忽的少主,一场注定无爱的婚姻——这局,从第一夜就开始了。而我,不能再当那个躲在梁上、只会看的人。我起身,吹灭烛火。黑暗里,我摸了摸袖中的银簪。 很凉。也很利。雨还在下。可我已经醒了。这一夜,我没睡。天快亮时,我写下三个名字:叶蓁、裴砚之、寒山道北。下面画了一条线。线头,指向“断雪式”。 我知道,从今往后,每一步都得算准。他们以为我是棋子。可棋子不会记账,不会翻册,不会在茶凉之前问出那一句“是我眼花?”我会。所以我不是棋子。我是开始织网的人。 雨没停。局已开。我坐在案前,等天亮。等下一个破绽。2天刚擦黑,雨又落下来。 我翻出旧账本,指尖在“叶蓁”二字上停了停。三月来,她夜出十七次,十三次走后园小径,时间都在子时三刻前后。枯井旁那条路,荒草过膝,夜里连巡夜弟子都避着走。 我换上灰青布裙,发髻用旧布条缠紧,素银簪插在袖中。这簪子我戴了十年,空心,能藏东西。现在它更重了——昨夜我熬了半宿,用特制药水将残卷拓在薄如蝉翼的蚕丝纸上,卷成细条塞进簪身,蜡封严实。我把它握在手里,冰凉。戌时末,我溜出房门,绕到后园。 雨不大,但风斜着吹,打在脸上像细针。老槐树离枯井不远,枝干横斜,我攀上去,蜷在分叉处,背靠树皮,视线正对小径入口。雷声闷闷滚过,远处钟楼敲了两响。子时三刻。 我屏住呼吸。小径尽头,一道纤细身影走来。叶蓁穿着月白练功服,外罩油衣,手里提着个油纸包。她脚步轻,走得稳,不像练夜功的人,倒像赴约。她在枯井边停下,左右看了看,抬手将油纸包放在井沿一块凸石上。片刻,墙外翻进一人。黑衣,蒙面,左肩比右肩低半寸,走路时微微一跛。他取走油纸包,低声说:“少主令,残卷三日内必归影阁。”叶蓁点头:“裴郎已信我,沈芜不足惧。 ”那人又道:“寒山旧部还有人活着,若她查到当年事,恐生变数。 ”“她只是个守旧规的寡妇。”叶蓁冷笑,“父亲死了,门派散了,她连剑都握不稳。 我学断雪式时,她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黑衣人没再说话,转身跃上墙头,一晃没了影。 叶蓁站在原地没动,雨打湿了她的发梢。她忽然抬头,目光扫过树冠。我贴紧树干,一动不动。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脚步依旧轻快。我等了半炷香才下来。手心全是汗,攥着的簪子几乎滑脱。我把它塞回袖中,指甲掐了掐掌心,提醒自己别抖。她叫它“残卷”。 不是“练功心得”,不是“旧谱残页”,是“残卷”。和我藏的那本一样。她知道有好几本。 影阁……这三个字我听过。十年前九大派围山,有人提过影阁插手江湖事务,后来消息就断了。如今它又出现,盯上了《九章》。我慢慢走回房,雨水顺着发尾流进脖颈。 我关上门,拧干布巾,点灯。灯芯跳了一下。我从暗格取出那本残卷——真本已经不在了,现在这本是昨夜我抄的假页,错漏三处,一处在“断雪拂柳”的运劲路线,一处在“寒江截月”的步法转折,第三处是故意多写一行无关口诀,混在中间。 我把它放回原处,盖上木板,撒了层薄灰。第三日午后,我去库房查冬衣登记。 管事递来册子,我翻到叶蓁那页,提笔批道:“添棉袍一件,厚底靴一双,另备姜汤炉,每日申时送至西厢。”管事抬头:“少夫人要示好?”“她夜里练功,别冻坏了。 ”我合上册子,“裴少主看重的人,我自然要照应。”管事笑了:“您心善。 ”我低头整理袖口,没接话。当晚,我躲在西厢对面的耳房里。二更天,一道黑影翻墙进来,直奔我住处。那人动作熟门熟路,撬开窗闩,钻进去,直奔床下暗格。我数着时间。 一盏茶后,他出来,手里攥着那本假残卷,跃墙而去。我没追。第四日清晨,我照常去执事堂领事务。长老头也没抬:“昨夜有人进你房?”“窗没关严。”我递上账册,“许是老鼠。”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裴砚之的人昨夜巡夜,竟没拦那黑影。要么是认得,要么是放行。我走出执事堂,雨还在下。我回房,掀开床板,暗格里留了点灰,但有两道指痕——有人动过,还特意抹过,但没抹匀。我蹲下,用指甲刮了点残留的灰在指尖捻了捻。是库房用的那种松香粉。专用来防潮,只西厢和藏书楼有。我站起身,走到铜镜前。镜中人脸色白,眼底青黑,但眼神稳。 我取下素银簪,轻轻摩挲簪尾。里面藏着真本。外面那本,已经被拿走了。我把它插回头发,转身去西厢。叶蓁正在练剑。雨水打在院中青砖上,她剑尖挑起水花,一招“断雪拂柳”使得行云流水。看见我,她收剑,行礼:“少夫人。”“昨夜雨大,你还练?”“习惯了。”她低头擦剑,“夜里安静,心也静。”“你倒有毅力。 ”我走近两步,“我听说,有人进过我屋子。”她手一顿:“谁?”“不知道。”我笑了笑,“翻了东西,但没拿走什么。许是找错了。”她抬头看我,眼里还是那副干净模样:“那就好。少夫人若丢了东西,我也不安。”“你心善。”我说。 她抿唇一笑。我转身走开,脚步不急不缓。走到门口,我停下:“对了,你练的这招‘断雪拂柳’,劲路是不是该从肩井过肘外侧?”她愣了一下:“是。 ”“我见你刚才走的是内侧。”我回头,“是不是记错了? ”她握剑的手紧了紧:“昨夜练得久,许是手滑。”“也是。”我点头,“毕竟……不是亲传。”她没说话。我走出院子,雨打在伞上,啪啪作响。回到房里,我关上门,从袖中取出素银簪,拔开尾塞,倒出那卷蚕丝纸。展开,字迹清晰,一页不少。 我重新卷好,放回去,蜡封。窗外雨未停。我坐在灯下,手抚簪身。你拿走的,是空壳。 我闭了眼。下一局,该我出招了。指尖刚触到灯芯,门外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一条缝。 叶蓁站在外面,手里捧着那本假残卷,脸上笑意淡淡:“少夫人,你这儿……掉东西了。 ”3门开了一条缝,叶蓁站在外面,手里捧着那本假残卷,脸上笑意淡淡:“少夫人,你这儿……掉东西了。”我伸手接过,指尖掠过纸面,平整无损。她没拆过,只是拿去走了一遭,再还回来。这一趟,不是为查真假,是为告诉我——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看中。“多谢你送回来。”我接过,声音没颤。她点头,转身走了,脚步轻得像没踩地。门关上,我走到铜盆前,掀开盖子,划了火折子,点着。火苗窜起,舔上纸角,字迹开始蜷缩、发黑。我没有看它烧成灰,只盯着那一点火光,直到它自己熄灭。 灰落在盆底,像一层薄霜。我起身,从袖中取出素银簪,拔开尾塞,确认蚕丝纸还在。 蜡封完好,没被动过。真本仍在我发间,从未离身。窗外雨还在下,敲着瓦片,一声接一声。 天快亮时,我听见脚步声由远及近,踏着水洼,停在我门外。门被推开,裴砚之站在门口,手里握着剑,剑尖滴水,在地上积出一小片湿痕。他没穿雨披,发梢往下淌水,衣领湿透,贴在脖颈上。他不开口,只盯着我。“有事?”我问。他抬手,剑尖指向我胸口,不刺,却像一道界线。“把真卷交出来。”他说。我看着他,眼睛没眨。“为了她?”他没回答。 我知道了。我慢慢抬手,取下发间素银簪,拔开尾塞,倒出那卷蚕丝纸。我没有展开真本,只将其中一段错漏的抄本抽出,递过去。他盯着那纸,伸手接过,快速扫了一眼,没细看。 这种抄本他见过太多,真假难辨,但他现在不需要辨。他只要一个结果。“就这些?”他问。 “你要的,都在上面。”我说。他收起纸卷,转身就走。门没关,风裹着雨潲进来,打湿了桌角的灯罩。我坐回椅上,吹灭灯芯。屋里暗了,只剩窗外灰白的天光。 外头传来人声,压得低,却掩不住。“少主真拿了剑去逼少夫人?”“亲眼见的,剑都出鞘了。”“为的还是叶姑娘……唉,少夫人这位置,怕是坐不稳了。”我没叫人进来,也没动。过了会儿,我起身,从柜底取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件旧袍。灰青色,领口磨得发白,是寒山门服。我脱下青锋门的少夫人常服,换上它。布料粗糙,贴在身上却像一层老皮,熟悉得让人安心。我坐回桌前,从暗格里取出一方木印,掌心大小,边角磕过,有些毛糙。我用拇指摩挲那个“沈”字,刻痕深,是父亲亲手雕的。 “我不是谁的妻,”我说,“我是沈砚声的女儿。”雨小了些,屋檐滴水变慢。 我起身走到窗前,推开扇页。风扑进来,带着湿气。远处回廊尽头,裴砚之的身影刚转过角门,背影笔直,走得决绝。我没看他走远。 我只看着他刚才站过的地方。地上那片水渍,正在慢慢干。---裴砚之回到西厢时,叶蓁正坐在灯下,手捧药碗,脸色泛白。他把纸卷扔在桌上。“拿去。”她没急着看,先抬眼看他:“她给的?”“嗯。”“没闹?”“没有。”她笑了,低头展开纸卷,一行行看过去。看到第三页,她指尖顿了顿,随即若无其事地翻过。“很好。”她说,“和影阁给的残卷对照,差了三处。”裴砚之皱眉:“你早知道她会交假的?”“她不傻。 ”叶蓁轻声说,“但她更不恨你。她恨的是当年九大派围山,是江湖不公,不是你拿剑指着她。所以她不会在这时候撕破脸。”裴砚之沉默。“她给你假卷,不是反抗,是成全。”叶蓁抬眼看他,“她在告诉你——你要走这条路,我拦不住,也不拦。 但从此以后,你我之间,再无半分情义可言。”裴砚之喉头动了动,没说话。 叶蓁把纸卷收好,吹熄灯。“你去吧。她现在不会逃,也不会揭发我。 因为她还不知道我是谁。”裴砚之站在原地,良久,转身出门。雨已停,石板路上积水映着天光,他走过时,踩碎了一片倒影。---我坐在灯下,把素银簪重新插回头发。簪子很轻,却压得住发。我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是昨夜默写的真本全文。我逐行对照脑中所记,确认无误。错漏三处,我都记得清楚。 假卷上的破绽,是诱饵,也是标记。谁拿了它,谁就会在关键时刻,练出岔气。我收起纸,塞进暗格。门外传来脚步声,轻而稳,是执事婆子。“少夫人,裴少主刚从您这儿出去,可要报执事堂?”“不必。”我说,“他来取东西,已经拿走了。 ”婆子顿了顿:“那……叶姑娘那边,要不要停了姜汤?”我抬眼:“为什么停? ”“这都第四天了,她夜里还练,也不知图什么。”“她想练,就让她练。”我说,“别亏待了人。”婆子应了声是,退下。我起身,走到镜前。镜中人脸色冷,眼神静。 我伸手抚过领口那道旧缝——是十岁那年,父亲帮我补的。一针一线,歪歪扭扭。我低头,解开发髻,取下素银簪。簪尾的蜡封,我重新涂了一层。然后,我重新绾发,插簪,抚平衣领。窗外,天光渐亮。我转身,走向门边。手搭上门闩时,听见远处钟楼敲了五响。 我拉开门。晨风扑面,带着雨后泥土的气息。我走出去,脚步落在湿石板上,没回头。 4晨光刚透,我踩着湿石板出了门。青锋门的檐角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青砖上,碎成水花。我没有回头,袍角沾了泥,也没去掸。旧袍贴在身上,领口那道歪斜的针脚蹭着脖颈,像父亲的手还在。玄枢台设在城西演武场,九派席位依序排开。我走到寒山旧位前,木椅蒙尘,案上签名录翻开一半。 执事长老抬头看了我一眼,眉心一皱:“沈姑娘,寒山已灭,你以何身份参会?”我没答话,从袖中取出木印,往案上一按。“寒山未灭,掌门在此。”印底“沈”字入木三分,全场静了两息。有人冷笑,有人低语,但没人再拦。我落座,目光扫过主位——裴砚之坐在那里,叶蓁立于侧后,垂手而立,姿态谦顺。他看也没看我。 钟声三响,大会开议。裴砚之起身,手捧三页残卷,立于高台中央。 他声音清朗:“此卷集寒山、青锋、落霞三派遗本,经我亲校,可证《九章剑谱》正统。 今以此卷,争盟主之位。”台下长老面面相觑。有人点头,有人皱眉,却无人当场驳斥。 他翻开第一页,念起“剑心九转”口诀:“气走神庭,意守天池,三转成枢……”我站了起来。“第三转,气走膻中,非走神庭。”我说,“你练的,是死路。 ”全场一静。裴砚之猛地抬头,眼神如刀。他身后叶蓁指尖微动,袖口一颤。“沈芜,”他冷声道,“你无故搅局,是想坏了玄枢规矩?”“我非搅局。”我直视他,“只是不愿见九派弟子,因错卷走火入魔。”“荒谬!”他抬手一扬,残卷展开,“此卷乃你亲手所交,如今反口否认,是何居心?”我仍不动:“我交的是残页,你拿去补全,补错了,便是祸根。”“你有何凭证?”我抬手,取下发间素银簪。 簪尾蜡封完好,指尖一旋,拔开。抽出一卷极薄的蚕丝纸,迎光展开。“此页藏于发间三年,字迹未褪,蜡封未启。”我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谁真谁假,一看便知。 ”我将真卷残页高举于天光之下。纸色微黄,墨迹沉稳,与他手中那页相比,笔锋更锐,行距更密。我逐字对照,指出三处错漏:其一,“神庭”误作“膻中”,逆行真气;其二, |
精选图文
 陆皎皎季晏礼全文(陆皎皎季晏礼免费小说-完整版-陆皎皎季晏礼在线赏析)最新章节已更新版
陆皎皎季晏礼全文(陆皎皎季晏礼免费小说-完整版-陆皎皎季晏礼在线赏析)最新章节已更新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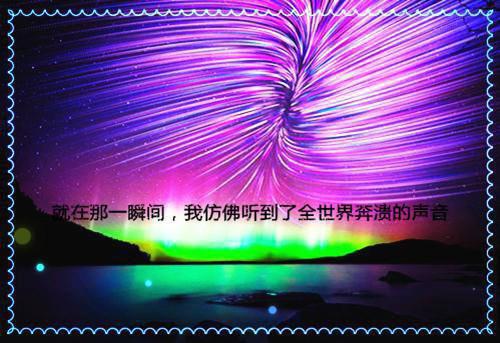 【新书】许溪蒋震霆全文全章节免费阅读-退婚后,八零肥妻被糙汉娇宠了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新书】许溪蒋震霆全文全章节免费阅读-退婚后,八零肥妻被糙汉娇宠了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楚小梨萧淮小说(楚小梨萧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楚小梨萧淮小说小说楚小梨萧淮小说列表(楚小梨萧淮)
楚小梨萧淮小说(楚小梨萧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楚小梨萧淮小说小说楚小梨萧淮小说列表(楚小梨萧淮) 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列表(季枝遥谢云礼)
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列表(季枝遥谢云礼) 季枝遥谢云礼(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免费阅读)季枝遥谢云礼最新章节列表(季枝遥谢云礼小说)
季枝遥谢云礼(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免费阅读)季枝遥谢云礼最新章节列表(季枝遥谢云礼小说) 沈幼星傅遇(沈幼星傅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幼星傅遇全文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沈幼星傅遇全文)
沈幼星傅遇(沈幼星傅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幼星傅遇全文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沈幼星傅遇全文) 沈幼星傅遇(沈幼星傅遇全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幼星傅遇全文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沈幼星傅遇全文)
沈幼星傅遇(沈幼星傅遇全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沈幼星傅遇全文免费阅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沈幼星傅遇全文) 桥小夏沈黎(桥小夏沈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桥小夏沈黎小说(桥小夏沈黎)
桥小夏沈黎(桥小夏沈黎)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桥小夏沈黎小说(桥小夏沈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