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阿阮《掌灯人阿阮》完结版免费阅读_王伯阿阮热门小说
|
第一章 青川镇的掌灯人上青川镇的雨,总下得黏黏糊糊,像扯不断的棉线,把整个镇子都裹在一层薄薄的雾里。连巷口那棵百年老槐树,都被雨雾染得发潮,树洞里积着的雨水,偶尔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像谁在数着时光的刻度。 镇东头的豆腐坊冒着白汽,混着雨雾飘在半空,远远望去,倒像幅没干的水墨画,连街角卖糖人的老周,都把担子挪到了屋檐下,手里转着竹签,却没几个孩子来买——雨天的青川镇,连热闹都透着股湿漉漉的静。 阿阮坐在“拾光阁”靠窗的旧木桌前,指尖捻着半片晒干的桂花瓣。 这花瓣是三年前中秋师兄陆执明留下的,如今边角已泛了黄,却还留着淡淡的甜香,像那段没来得及说完的话——那天师兄把花瓣塞进她手里时,还笑着说要带她去雾隐山采桂花,可转天清晨,人就没了踪影,只留下一盏没做完的琉璃灯,和一张写着“寻忘忧灯,归期未定”的字条。她抬头望向窗外,雨丝把檐下那盏红灯笼打湿。 灯笼是师兄亲手做的,灯架雕着细竹纹,每一道纹路都磨得光滑,灯面上用金粉描的“拾”字晕开一小片淡金,像撒在墨色宣纸上的碎星子,又像记忆里爹娘模糊的笑脸。柜台后挂着的布帘,印着细碎的竹纹,是娘生前绣的,针脚细密得能数清,风一吹,布帘轻轻晃,总让阿阮错觉娘还在里屋缝补衣裳,下一秒就会掀帘出来,手里端着盘刚蒸好的桂花糕,笑着问她:“阿阮,今天练做灯了吗?
”“姑娘,请问……这里是能寻‘念想’的地方吗?”木门被轻轻推开,带进来一股潮湿的草木香,还混着些许皂角的清苦。阿阮连忙放下桂花瓣,起身从柜台后取来一盏琉璃灯——灯身是淡青色的,像浸在溪水里的玉石,通透得能看到里面的灯芯;灯芯则是浅金色,是师兄当年教她用“念想绒”搓的。 这念想绒是用镇民遗失的细碎记忆凝成的,晒足七七四十九天,点燃时不会冒烟,只冒一缕暖香,像晒了一下午太阳的旧棉絮,能让人想起安稳的时光。“是。丢了什么念想? ”阿阮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散了客人身上的雨雾,也怕惊散了自己刚冒出来的回忆。 门口站着的年轻媳妇穿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领口缝着块补丁,是淡蓝色的布,显然是找了块旧布补上的;她梳着整齐的圆髻,发髻上别着根铜簪,簪头已磨得发亮,边缘都有些圆润了,想来是戴了许多年。她手里攥着块绣了半朵荷花的绢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指腹上还沾着点未洗净的草木汁,指甲缝里嵌着些泥,一看就是常下地干活的人。见阿阮看她,媳妇有些局促地把帕子往身后藏了藏,又很快递上来,像是下定了决心,指节因为用力,连带着帕子都微微发颤,帕角的线头都被扯得松了。“我夫君……”媳妇的声音发颤,眼圈慢慢红了,像被雨打湿的樱桃,“他去年清明去后山采笋,脚滑摔下了坡,撞到了头。醒了以后,就不认人了。连我们定情时,他熬夜给我绣的这荷花帕子,都说是路边捡的破烂,要扔了……”她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砸在绢帕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那泪珠滚过她的指缝,落在青石板上,很快被地上的潮气吸走,只留下一点浅浅的印记,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就像她夫君忘了的那些时光。阿阮接过帕子时,指尖触到帕面的纹理,能感觉到边缘被摩挲得发毛,是常年揣在怀里磨出来的;未完工的荷花绣线只用了半种颜色——粉色的花瓣只绣了三瓣,针脚还歪歪扭扭的,剩下的留白处,还能看到淡淡的针脚印,显然是当年没来得及绣完。 帕子中间,还沾着一点干了的泥渍,呈浅褐色,带着点腐叶的气息,想必是夫君摔下坡时,沾到的竹林里的腐叶土。“掌灯寻忆要‘信物’,你这帕子正好。”阿阮把绢帕铺在灯下,灯光映着帕子上的荷花,倒显得那半朵花有了些生气。她又从抽屉里取出个小巧的竹制灯架,将琉璃灯稳稳固定在架上,灯架上还留着师兄刻的小竹节,是当年两人一起练手时刻的,一节代表阿阮,一节代表师兄,“今晚是十五,月亮会破云。亥时三刻,你到后山竹林入口等我。寻不回念想,分文不取。”媳妇连忙点头,又从布兜里掏出一小袋铜板,袋子用粗麻绳系着,绳结打得紧实,磨得有些起毛,能听到里面铜板碰撞的“叮当”声。她双手捧着递过来,腰微微弯着,带着些讨好的姿态:“姑娘,这是定金,您先拿着。要是能让他记起来,我再给您补双倍! 我家夫君以前最疼我,冬天会把我的手揣进他怀里暖着,夏天会去溪里给我摸凉瓜,晚上还会给我讲故事……他要是记起来,肯定也会谢您的……”她说着,声音又低了下去,眼神里的光也暗了些,像是怕自己说的都是奢望,怕那些温暖的时光再也回不来。 阿阮看着她,想起师兄没走的时候,也总在冬天把她的手揣进怀里,说她的手像冰疙瘩,得好好暖着;夏天会去后山的溪里摸鱼,烤着给她吃,鱼刺都挑得干干净净。“先收着吧。 ”阿阮把铜板推了回去,指尖碰到媳妇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等事成了再说。你回去吧,今晚别熬夜,保存点精神,寻忆时得全神贯注才行。对了,你夫君现在还常去后山吗?”“不去了。”媳妇摇摇头,声音低得像蚊子哼,“他说看到竹子就头疼,天天待在家里,要么发呆,要么劈柴,劈完的柴堆得比人还高,却不知道烧。我看着他那样,心里比针扎还疼……有时候我跟他说以前的事,他就坐在门槛上,盯着远处的山,一句话也不说,像没听见一样。有次我把帕子给他看,他还把帕子扔在地上,说我别再拿破烂烦他……”说到最后,媳妇的声音哽咽了,她用袖子抹了把眼泪,又强撑着笑了笑:“姑娘,我知道我麻烦您了,可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不想他一辈子都这样……”阿阮拍了拍她的手背,她的手很粗糙,是常年干活磨出来的茧,阿阮轻声说:“放心,我会尽力的。”她见过太多丢了念想的人,有的沉默,有的暴躁,有的把自己关起来,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而掌灯人能做的,不过是帮他们把丢在时光里的灵魂碎片,一点点捡回来,再轻轻放回他们心里,让那些被遗忘的温暖,重新生根发芽。媳妇千恩万谢地走了,木门关上时,雨势似乎小了些,透过窗缝,能看到巷子里的青石板泛着光,像铺了层碎玻璃。阿阮坐在桌前,重新拿起那片桂花瓣,指尖轻轻摩挲着,花瓣的纹路硌着指尖,像在提醒她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时光,不是幻觉。三年前的中秋,师兄就是在这张桌前,把晒干的桂花瓣塞进她手里。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像块白玉盘挂在天上,他们在院子里摆了张桌子,放了娘做的桂花糕和爹酿的米酒。爹还在的时候,总说米酒要酿足三年才够香,那天他喝了不少,笑着说阿阮长大了,能帮着做灯了;娘坐在旁边,给他们剥石榴,红色的籽落在碟子里,像小小的红宝石。 师兄说:“阿阮,等明年桂花开,我就带你去雾隐山采最新鲜的桂花,那里的桂花比镇上的香十倍,做出来的桂花糕能甜到心里。到时候,咱们再给师父师娘扫扫墓,跟他们说你现在做灯越来越好了,都能自己掌灯了。”那时候,阿阮还笑着说要跟师兄比谁做的灯好看,说要做一盏比师兄的还亮的琉璃灯;娘笑着说她们俩都是孩子心性,爹则在旁边喝着酒,点头附和。可没等到桂花开,爹娘就没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把他们去后山采草药的路给冲了,等阿阮和师兄找到他们时,只看到娘紧紧护着的药篮,里面还有给阿阮带的野果子,已经烂了;爹手里还攥着块给师兄的木牌,是用后山的桃木做的,上面刻着“平安”二字。又过了半年,师兄也走了。那天清晨,阿阮像往常一样去敲师兄的房门,没人应,推开门,只看到桌上的字条和那盏没做完的琉璃灯——灯身刚刻好一半竹节,灯芯是他亲手搓的浅金色,灯座下还刻着个小小的“阮”字,刻得很深,像是怕被磨掉,怕阿阮忘了他。阿阮把那盏灯放在柜台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用软布擦一遍,擦得灯身发亮,总觉得师兄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会接着把灯做完,会笑着跟她说“阿阮,我找到忘忧灯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怕伤心了”。她翻出师兄的手记,那本手记的纸页已经泛黄,边角卷了边,是用粗麻布做的封面,上面还留着师兄的指印,是常年握刻刀留下的薄茧印,指印边缘有些模糊,想来是被翻了很多次。里面记满了掌灯人的诀窍,字迹工整,偶尔会画些小图,比如怎么搓念想绒,怎么让忆影更清晰,图上还会用红笔标注重点:- 寻孩童的念想,要带块麦芽糖,引记忆里的甜味——孩童心性纯,甜忆最易显。若忆影模糊,可轻声哼孩童熟悉的童谣,比如《月光谣》,青川镇的孩子都爱听。- 寻老人的念想,得在灯旁放杯热茶最好是老茶,比如去年的龙井,暖透时光里的凉——老人忆久,多带寒凉,需温养才能现。若老人情绪激动比如落泪、手抖,需暂停掌灯,递上热茶,待其平复再续,切记不可强行引忆,恐伤神智。- 寻爱人的念想,要取两人共信物越旧越好,最好是戴了三年以上的,信物越旧,忆影越清。 掌灯时需让寻忆人默念最难忘的场景比如定情时、初遇时,同时将信物贴在眉心,方能引忆影现形。- 灯芯变色需留意:暖忆则金如孩童笑、爱人相拥,冷忆则银如离别、思念,痛忆则灰如失去、伤病。若遇异忆,芯现青色——此忆非寻常,或涉“雾隐谷”,需慎之,勿轻碰。翻到最后一页,字迹突然变得潦草,墨水都有些晕开,像被眼泪泡过,只写了半句话:“青川镇的雾,藏着……”后面的字迹被水渍糊住,结成了深色的斑块,无论阿阮怎么用指尖蹭、用软布擦,都看不清,只能隐约看到“忘忧”两个字的残笔,像是“忘忧灯”,又像是“忘忧草”。 她对着那半句话看了很久,心里总觉得不安——师兄当年写下这句话时,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藏着”后面,到底是能让人忘记痛苦的宝贝,还是会让人万劫不复的陷阱?“吱呀”一声,窗外传来一阵轻响,是檐下红灯笼被风吹得撞在了木架上,灯穗晃了晃,洒下几滴雨水,落在窗台上,发出“滴答”的声。阿阮抬头,见灯影里站着个穿灰布衫的小男孩,约莫七八岁,头发乱糟糟的,沾着点草屑,额头上还贴着块用布条做的简易纱布,纱布边缘渗着点淡淡的红,想来是磕破了头。他手里攥着个断了线的风筝,风筝尾巴上沾着点泥和草屑,风筝面是用粗纸做的,画着只小白兔,耳朵已经磨破了,露出下面的竹篾;眼睛是用红色颜料画的,也掉了大半,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红点,像兔子哭红了眼。“姑娘,你能帮我寻个东西吗?”小男孩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点怯意,眼睛却亮得像星星,一眨不眨地盯着阿阮,手指紧紧攥着风筝线,指节都泛白了,“我娘说,镇西头的拾光阁有位姑娘,能帮人找丢了的东西,不管是物件,还是……还是记不起来的事。 ”阿阮起身开窗,一股凉意涌进来,带着雨后的青草香,还有远处溪水的潮气,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她看着小男孩单薄的身影,心里软了软:“丢了什么?”“风筝。 ”小男孩把断了线的风筝举起来,胳膊有些细,能看到里面的骨头轮廓,袖子也短了一截,露出手腕上的红痕,像是被树枝刮的,“是我娘做的,昨天刮风,风筝被吹到后山去了。 我娘说,那是她用我穿旧的衣服改的,布料软,风筝飞得稳。找不回风筝,就再也不给我做新的了。她还说,这风筝上的兔子,是照着我小时候的样子画的,说我小时候胖嘟嘟的,脸像兔子一样圆……”说到最后,小男孩的声音低了下去,眼圈也红了,他把风筝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宝贝,手指轻轻摸着兔子的耳朵,动作小心翼翼的,生怕把剩下的颜料蹭掉。阿阮看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娘也常给她做风筝——竹篾是爹劈的,选的是后山最韧的竹子,劈好后还要用砂纸磨光滑,怕扎手;纸是娘从镇上买的桃花纸,薄而轻,颜色是淡淡的粉,风一吹就像要飘起来;颜料是师兄帮着调的,每次都把她的手染得五颜六色,像沾了彩虹,师兄还会笑她是“小花猫”。每次风筝飞高了,娘都会牵着她的手,笑着说:“阿阮的风筝,能飞到云上去呢,说不定能让天上的神仙,看看咱们阿阮多乖。”那时候,师兄还在,爹娘也在,拾光阁里总是热热闹闹的。爹会在门口劈柴,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娘会在里屋做饭,香味能飘到巷口;师兄会教她做琉璃灯,偶尔还会偷偷带她去后山掏鸟蛋,回来被爹骂,却还是笑得开心,把掏来的鸟蛋煮给她吃。 可一场山洪,把爹娘都带走了,也把那些热闹的时光,埋进了记忆深处,像被雨雾裹住,看不清,却总在夜里冒出来,让她睡不着,想起娘的桂花糕,爹的米酒,还有师兄的笑声。 “能寻。”阿阮的声音软了些,从抽屉里拿出块麦芽糖,用油纸包着,递给他,糖块是金黄色的,能看到里面的芝麻,“不过要等我今晚帮完那位婶婶,明晚带你去后山,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石头!”小男孩立刻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像小松鼠一样可爱,接过麦芽糖时,手指还蹭了蹭阿阮的手心,暖暖的。 他把麦芽糖揣进怀里,又把风筝抱好,生怕掉了,“我明天傍晚就来这里等你! 我还能帮你扫地,帮你擦桌子,不要你给钱!我娘说,不能白麻烦别人,要懂得报恩。 ”说完,他攥着风筝和麦芽糖,蹦蹦跳跳地跑进了雨雾里,跑了几步还回头喊:“姑娘,你可别忘啦!我会准时来的!”他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带着孩子特有的清脆,很快被雨声盖过,只留下一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衣角还在风里晃。 阿阮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青川镇的人,好像都藏着点丢不掉的念想——有的是半朵荷花的绢帕,有的是画着兔子的风筝,有的是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有的是一段不敢提起的回忆。而她的念想,是师兄的归期,是爹娘没说完的叮嘱,是那本手记里没写完的秘密,还有那年没来得及去采的桂花。她低头看了看桌上的琉璃灯,灯芯还是浅金色的,安静地躺在灯身里,像在等着被点燃,等着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时光。阿阮轻轻摸了摸灯身,心里默念:师兄,今晚我要帮李嫂寻忆,要是你在就好了,你肯定知道怎么让忆影更清晰。 你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也在某个地方,帮人寻忆,或者……在找我? 第一章 青川镇的掌灯人下亥时三刻,雨果然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像被洗过一样,清辉洒在青石板上,像铺了层霜,又像撒了把碎银。 阿阮提着琉璃灯走出拾光阁,锁上门时,指尖碰到门环上的铜锈,凉丝丝的。夜风吹过,带着竹林的清甜味,还混着点泥土的气息,偶尔有竹叶上的水珠滴下来,落在灯纸上,发出“嗒”的轻响,像时光在轻轻敲门,问她准备好了吗。她带了个布包,里面装着师兄留下的一小瓶“忆露”——手记里说,遇到模糊的忆影,滴一滴忆露,就能让影子变清晰,这忆露是师兄用晨露和桂花蜜熬的,瓶身上还贴着师兄写的“忆露”二字,字迹娟秀;还有一块用油纸包好的桂花糕,是早上从镇上的糕点铺买的,掌柜的说是用去年的桂花做的,还带着点甜香,想着要是寻忆顺利,能给李嫂分一块,让她也尝尝甜;另外还有一根蜡烛,怕竹林里太暗,琉璃灯的光不够用。后山竹林入口,李嫂已经在等了,手里提着个陶壶,壶身裹着厚厚的蓝布,是她自己缝的,怕茶水凉了。见阿阮来,她连忙迎上来,脚步有些急,差点被路边的石头绊倒,手里的陶壶都晃了晃,却没洒出一点水:“姑娘,你可来了! 我还怕你不来了呢!”“说好的事,不会忘的。”阿阮笑了笑,把布包放在旁边的石头上, |
精选图文
 苏天妤轩辕忌(重生五年前,藏起孕肚嫁权王)全文免费苏天妤轩辕忌读无弹窗大结局_(苏天妤轩辕忌重生五年前,藏起孕肚嫁权王免费苏天妤轩辕忌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苏天妤轩辕忌)
苏天妤轩辕忌(重生五年前,藏起孕肚嫁权王)全文免费苏天妤轩辕忌读无弹窗大结局_(苏天妤轩辕忌重生五年前,藏起孕肚嫁权王免费苏天妤轩辕忌读全文大结局)最新章节列表(苏天妤轩辕忌) 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完整全文在线阅读 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抖音热推小说全集无删减
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完整全文在线阅读 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抖音热推小说全集无删减 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的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完整章节阅读
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的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走错手术室,误把肿瘤当阑尾林远》完整章节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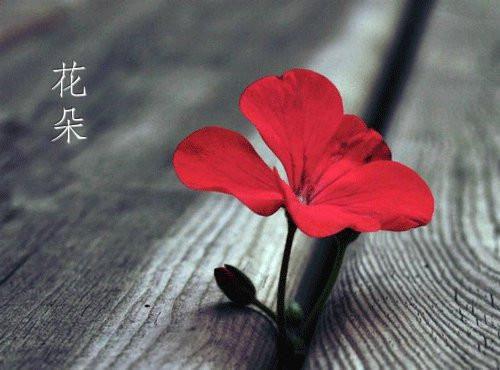 (热推新书)程轻语谈戚言完整版免费小说无弹窗阅读_程轻语谈戚言最新章节列表(程轻语谈戚言)
(热推新书)程轻语谈戚言完整版免费小说无弹窗阅读_程轻语谈戚言最新章节列表(程轻语谈戚言) 程轻语谈戚言小说(程轻语谈戚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程轻语谈戚言小说免费阅读
程轻语谈戚言小说(程轻语谈戚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程轻语谈戚言小说免费阅读 苏晚枝傅司寒小说 是他亲手把她送进了地狱全文免费阅读
苏晚枝傅司寒小说 是他亲手把她送进了地狱全文免费阅读 苏晚枝傅司寒是他亲手把她送进了地狱多人追免费无弹窗小说,是他亲手把她送进了地狱已完结全集大结局
苏晚枝傅司寒是他亲手把她送进了地狱多人追免费无弹窗小说,是他亲手把她送进了地狱已完结全集大结局 热文推荐哪有动情是意外 纪知意傅明楼小说无弹窗大结局
热文推荐哪有动情是意外 纪知意傅明楼小说无弹窗大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