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雪,江湖骨荣海城芙珂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最新更新小说长安雪,江湖骨(荣海城芙珂)
|
第一章 长安夜雨,刀影初逢荣海城的刀藏在伞骨里。上元节的夜雨裹着脂粉气,将朱雀大街的青石板浸得发亮。他踩着积水走过平康坊,檐角滴落的水珠砸在油纸伞上,混着楼里传来的琵琶声,像极了二十年前渭水畔的厮杀。“客官,打尖还是住店? ”悦来客栈的灯笼在风里摇晃,照出掌柜脸上堆得发僵的笑。荣海城抬头时,檐下的铁马突然叮当作响——不是风动,是有人踩着瓦片掠过时带起的气流。 他反手将伞柄旋了半圈,伞骨里的“碎星”刀已滑入掌心。刀身薄如蝉翼,映着二楼窗口探出来的半张脸——女子鬓边别着支银步摇,流苏坠着颗鸽血红的玛瑙,正随着她的呼吸轻轻颤动。“荣某找个人。”他的声音压在雨声里,“姓秦的镖师。 ”掌柜的脸色骤变,刚要摸向柜台下的响箭,就被窗上飞落的茶盏砸中手背。 茶盏在他脚边碎裂时,那女子已站在大堂中央,青色罗裙下摆还沾着夜露。
“秦镖头今早出了城,”她的指尖划过腰间的玉佩,“往潼关去了。 ”荣海城的刀在袖中转了半圈。这女子的步法带着江南水派的轻俏,可捏碎茶盏的指力却藏着西北马家的“裂石功”——江湖上能把两种路数糅得这般自然的,除了三年前销声匿迹的“玉面罗刹”芙珂,再无第二人。“姑娘知道得倒是清楚。 ”他眯起眼,看她鬓边的玛瑙在灯笼下泛出血光,“就不怕荣某是来寻仇的? ”芙珂突然笑了,步摇上的玛瑙撞在一起:“荣大侠三年前在洛阳渡口,用‘碎星’刀挑断黑风寨七十三条锁链,救了整船的镖师家眷。这般人物,寻的该是公道,不是仇怨。”她的话像根针,刺破了荣海城刻意维持的冷硬。三年前那个雪夜,他确实在洛阳渡口挥过刀,可救的不是什么镖师家眷,是被黑风寨掳走的朝廷密使。 江湖传言总爱添油加醋,把他这朝廷暗卫,说成行侠仗义的绿林客。“姑娘谬赞。 ”他收了刀,伞骨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只是不知秦镖头为何要连夜离城? ”“因为他押的镖丢了。”芙珂突然凑近,罗裙上的冷香混着雨气漫过来,“丢的是西域都护府的鸽符,据说能调动边关十万铁骑。”檐外的雨突然急了,打在窗纸上噼啪作响。荣海城猛地按住伞柄——他这次下山,正是为了追查失窃的鸽符。 密探回报说鸽符落在秦镖头手里,可没说已经丢了。“姑娘怎么确定? ”“因为我见过偷鸽符的人。”芙珂的指尖点向自己的鬓角,“那人左耳后有块月牙形的疤,用玄铁打造的飞爪,爪尖淬了‘牵机引’——沾了皮肉,半个时辰就会全身僵硬,像块石头。 ”荣海城的喉结动了动。牵机引是唐门的独门毒药,三年前他在岭南追查叛党,亲眼见个孩童沾了毒药,最后缩成块黑紫色的石头。那用飞爪的人,难道是唐门余孽? “秦镖头……”“他中了牵机引。”芙珂转身看向门外,雨幕里隐约有马蹄声,“我今早去秦府,见他躺在密室里,全身已经开始发僵。桌上留了张字条,写着‘潼关,青龙庙’。”马蹄声越来越近,荣海城瞥见街对面的槐树后,有个黑影正往这边张望。 他突然抓起桌上的茶壶,朝芙珂掷过去:“接住!”芙珂旋身接住茶壶的瞬间,荣海城的伞已经飞了出去,正砸在槐树后的黑影脸上。黑影闷哼一声倒地时,他已拽着芙珂窜出后门,手里的碎星刀划破雨幕,劈开了巷子里突然落下的渔网。 “是‘天罗教’的人。”芙珂踩着墙根翻身跃上屋顶,青色罗裙在雨里展开如蝶翼,“他们的渔网浸过松脂,沾了就脱不开。”荣海城跟着跳上屋顶,脚下的瓦片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看见远处的雨幕里,有十几个黑影正往这边移动,手里都拖着缠了铁链的渔网。“往南走!”芙珂突然抓住他的手腕,她的指尖冰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那边有片竹林,能卸开他们的合围。”穿过雨帘时,荣海城闻到芙珂发间的冷香里,混着丝极淡的药味——是“九转回魂草”的气息,这种药只在西域雪山才有,据说能解百毒,也能……让人忘记前尘往事。第二章 潼关古道,青龙泣血竹林深处的破庙里,荣海城用碎星刀挑开篝火。火星溅在芙珂的罗裙上,她却浑然不觉,正用根银簪,小心翼翼地挑开秦镖头留下的字条。“字是用左手写的。 ”她的鼻尖几乎碰到纸面,“墨迹里掺了朱砂,应该是想留记号。 ”荣海城往火堆里添了根枯枝。秦镖头是右撇子,用左手写字定是被人胁迫。 可这朱砂记号……他突然想起密使卷宗里写的,天罗教的教徒,都会在指甲缝里藏朱砂。 “这字条是假的。”他抓住芙珂的手腕,银簪差点戳到她的指尖,“秦镖头根本没去过青龙庙,是天罗教的人设的局。 ”芙珂的睫毛颤了颤:“可他中了牵机引,除了天罗教,谁还能解?”“解不了。 ”荣海城的声音沉下去,“牵机引无药可解,除非……”除非用活人做药引,把毒素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话他没说出口,三年前在岭南,他就见过唐门用这种法子,让个丫鬟替叛党死了。篝火突然噼啪作响,映出庙门外的黑影。 荣海城拽着芙珂滚到香案下时,三支淬了毒的弩箭已经钉在他们刚才坐的地方,箭羽上的蛇形纹在火光里闪着冷光。“天罗教的‘蛇吻弩’。”芙珂从袖中摸出把短匕,匕身刻着细密的花纹,“箭头淬了‘腐骨散’,比牵机引厉害。”庙门被踹开的瞬间,荣海城的碎星刀已经出鞘。刀光劈开迎面扑来的黑影,却在触及对方咽喉时顿住——那人左耳后,没有月牙形的疤。“不是偷鸽符的人! ”他低喝一声,刀势急转,削断了对方手里的铁链。芙珂的短匕也没闲着,匕身的花纹在火光里亮起,竟是用西域的“荧石”所制。她每刺出一刀,都有荧光顺着伤口钻进对方体内,那些黑影顿时像被火烧般惨叫起来。“是‘蚀骨纹’。 ”她边打边解释,匕尖挑飞个黑影的面具,“我在西域学的,能让中者骨头发痒,恨不得把自己抓烂。”荣海城的刀突然停在半空。被挑落的面具下,是张少年的脸,眉眼间竟有几分像他早逝的弟弟。那少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伸手想抓荣海城的衣角,却在触及碎星刀的瞬间,全身冒出绿烟,化作一滩脓水。“是傀儡。”芙珂拽了他一把,短匕刺穿另一个黑影的心脏,“天罗教用活人炼制的,没有自主意识。”荣海城的喉头发紧。 三年前在岭南,他也见过这样的傀儡,是用叛党的家眷炼的。 当时他挥刀砍断了所有傀儡的脖子,却在回营后吐了整整一夜。“往庙后走! ”芙珂突然指向香案后的暗门,“我早上来探过,有条密道通往后山。”穿过暗门时,荣海城瞥见香案上的香炉,里面插着三支没烧完的香,香灰攒成个奇怪的形状——是天罗教的“血祭阵”图腾。他们根本不是来抓人的,是想用这些傀儡做祭品,启动什么阵法。密道里弥漫着霉味,芙珂的荧石短匕成了唯一的光源。荣海城听见身后传来石块滚动的声音,知道暗门已经被封死,那些没被杀死的傀儡,怕是永远困在庙里,成了血祭阵的养料。 “你好像很怕天罗教?”芙珂突然停下脚步,荧光照亮她眼底的疑惑,“刚才砍那个少年傀儡时,你的手在抖。”荣海城握紧了碎星刀。刀柄上的纹路硌着掌心,那是他刚入暗卫营时,总教头用烙铁烫上去的——暗卫当断则断,不可有半分恻隐。 “只是觉得……”他喉结动了动,“用活人做傀儡,太过阴毒。”芙珂突然笑了,荧石的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荣大侠倒是心善。可江湖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她凑近一步,声音压得很低,“就像三年前洛阳渡口,你救密使时,不也杀了整船的黑风寨喽啰?他们里头,说不定也有被迫入伙的。”荣海城的刀差点脱手。 她怎么知道洛阳渡口的细节?那是朝廷绝密,除了暗卫营的人,绝不可能有外人知晓。 “你到底是谁?”他的刀抵住芙珂的咽喉,荧石的光映得刀刃泛着青蓝,“天罗教的细作? 还是……唐门的人?”芙珂没有躲,反而往前凑了凑,刀尖刺破她颈间的肌肤,渗出血珠:“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鸽符现在在天罗教教主手里,他要在三日后的月蚀之夜,用鸽符打开西域的密道,放突厥铁骑入关。”血珠滴在刀身上,发出轻微的嘶声。荣海城突然想起密探的另一份报告——天罗教教主,原是前隋的皇室遗脉,一直想打败大唐,复辟旧朝。“你怎么知道这些?”“因为我是前朝公主。 ”芙珂的声音很轻,像密道里的尘埃,“我爹是隋炀帝的幼子,三年前被天罗教灭了满门,只有我逃了出来。”荣海城的刀垂了下去。他见过前朝皇室的画像,芙珂的眉眼间,确实有几分像画里的杨妃。可一个前朝公主,怎么会懂西域的蚀骨纹,又怎么会知道暗卫营的秘辛?“不信?”芙珂从怀里摸出块玉佩,荧光照亮上面的“杨”字,“这是我娘留给我的,说戴着它,到了长安就找荣家军的后人。”荣海城的瞳孔骤缩。 荣家军是他祖父统领的军队,当年随李世民平定天下,后来被奸臣构陷,满门抄斩,只剩他父亲逃了出来,隐姓埋名当了个铁匠。这世上,该没人知道他是荣家军的后人。 “你娘……”“她叫荣晚照。”芙珂的指尖抚过玉佩上的刻痕,“说当年在雁门关,是荣家军的少将军救了她。”荣晚照是他的姑姑。当年姑姑随祖父征战,在雁门关被突厥俘虏,所有人都以为她死了,没想到……“姑姑她……”荣海城的声音发颤,“她还活着吗?”芙珂摇了摇头,眼眶在荧石光里泛着红:“我娘去年冬天没的。 她说天罗教的人追来了,让我带着玉佩来长安,找荣家军的后人帮忙,阻止天罗教打开密道。 ”密道的入口在青龙庙的地宫。荣海城突然明白,秦镖头留下的字条不是假的,天罗教故意设局引他们来破庙,是想拖住他们,好让教主在青龙庙专心准备月蚀祭典。 “我们得去青龙庙。”他握紧碎星刀,刀身映出自己眼底的决绝,“就算是陷阱,也得闯一闯。”芙珂突然抓住他的手,她的指尖不再冰凉,带着体温:“荣大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但天罗教的地宫机关密布,我们得找个帮手。”“找谁? ”“‘鬼手’苏缺。”芙珂的嘴角勾起抹笑意,“他是天下第一锁匠,也是……我娘的故人。 ”密道尽头的月光漏下来,照在两人交握的手上。荣海城突然觉得,芙珂的掌心很暖,像极了小时候姑姑给他糖吃时,握住他的那只手。第三章 鬼手开锁,人心如锁长安城以西的乱葬岗,有间用棺材板搭的屋子。荣海城站在屋外,闻着空气中的腐臭味,突然觉得悦来客栈的霉味都算清香。“苏缺就在里面。 ”芙珂敲了敲门板,上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锁,“他这人怪得很,只认锁不认人。 ”门板吱呀作响地打开,露出张布满疤痕的脸。那人的右手缺了根小指,左手却异常灵活,正把玩着串铜钥匙,钥匙上的纹路在月光里闪着光。“玉面罗刹,别来无恙。 ”苏缺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三年不见,你的蚀骨纹倒是精进了。 ”芙珂的脸色微变:“苏前辈说笑了。”“说笑?”苏缺突然笑起来,钥匙串叮当作响,“当年在西域,你用蚀骨纹杀了唐门十二位长老,这事江湖上可没几人知晓。怎么,现在改头换面,想当回前朝公主了?”荣海城的手按在刀柄上。 原来她不是不知道蚀骨纹的厉害,是真的用过这阴毒功夫杀人。那所谓的前朝公主身份,恐怕也是假的。“苏前辈若不愿帮忙,芙珂不勉强。”芙珂转身就要走,却被苏缺扔过来的铜钥匙挡住去路。“钥匙能开锁,可人心这把锁,谁能开? ”苏缺的独眼盯着荣海城,“荣大侠,你知道她为什么找你吗?”荣海城没说话,碎星刀在袖中微微颤动。“因为你是荣家军的后人,手里有‘破阵图’。 ”苏缺的声音突然压低,“当年你祖父平定西域,画了张密道布防图,能破天罗教的所有阵法。这图,就藏在荣家的祖传玉佩里。”荣海城猛地抬头。破阵图的事,只有他父亲临终前说过,这苏缺怎么会知道?“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 ”苏缺的独眼闪过丝狡黠,“重要的是,天罗教教主也在找破阵图。他抓了秦镖头的女儿,说要在青龙庙的地宫里,用这丫头做祭品,逼你交出图。”芙珂突然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你怎么不早说?”“早说了你会来?”苏缺掂了掂手里的钥匙串,“那丫头是秦镖头的命根子,也是……你娘当年留在秦府的眼线。”荣海城的喉结动了动。 姑姑当年竟在秦府安了眼线?那芙珂说的话,到底有几句是真的?“地宫里的机关,我能破。 ”苏缺突然抛出一把铜钥匙,落在荣海城手里,“但得用破阵图换。不然,就算你们闯进地宫,也会被‘万箭阵’射成筛子。”荣海城握着那把钥匙,冰凉的金属硌着掌心。破阵图藏在他贴身的玉佩里,那是父亲用命换来的,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可秦镖头的女儿……“我可以给你图的拓本。”他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但你得保证,先救那丫头。”苏缺的独眼亮了:“成交。明晚子时,青龙庙后门见。”门板关上的瞬间,芙珂突然抓住荣海城的胳膊:“荣大哥,不能信他! 苏缺是天罗教的叛徒,当年就是他帮教主打开了西域的第一道密道! ”荣海城看着她眼底的焦急,突然想起刚才苏缺说的话——人心是把锁,谁能打开? 芙珂这副急切的模样,是真的担心那丫头,还是怕苏缺得到破阵图?“他就算是叛徒,也需要破阵图。”荣海城掰开她的手,钥匙在掌心转了个圈,“只要我们比他先找到丫头,就能掌握主动。”回客栈的路上,芙珂一直没说话,步摇上的玛瑙在月光里泛着暗红光。 荣海城突然觉得,这女子像团雾,看似清澈,实则深不见底。“荣大哥,”快到客栈门口时,芙珂突然停下脚步,仰头看他:“你是不是在怀疑我?”荣海城避开她的目光,看向檐角的灯笼:“江湖路远,彼此留几分余地总是好的。”她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点自嘲:“也是。毕竟我这身份,说出来连自己都觉得荒唐。 ”她抬手摘下鬓边的银步摇,塞进荣海城手里,“这步摇里藏着半张密道图,是我娘临终前缝进去的。荣大哥若信不过我,现在就可以砸开看看。 ”步摇上的玛瑙贴着他的掌心,凉得像块冰。荣海城突然想起三年前在岭南,那个中了牵机引的孩童,最后也是这样浑身冰凉。他把步摇塞回芙珂手里:“荣某信你。 ”其实他不信。可不知为何,看着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失落,他竟说不出怀疑的话。 第四章 青龙地宫,旧怨新仇子时的青龙庙被月光浸得发白,香炉里残留的香灰被风吹起,像极了地宫里游荡的冤魂。荣海城握紧碎星刀,看着苏缺用那把铜钥匙,打开后门上的七道锁。“这锁是我当年给天罗教做的,”苏缺的独眼在月光里发亮,“用的是‘北斗七星’的阵理,错开时辰就会触发弩箭。”地宫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荣海城的靴底踩在黏腻的地面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芙珂的荧石短匕照出两旁的石壁,上面刻满了扭曲的人脸,眼睛的位置嵌着发亮的磷火,像无数双窥视的眼睛。 “是‘生人壁’。”苏缺的声音压得很低,“每块石头里都嵌着个活人,被灌了水银活活钉进去的。”荣海城的胃里一阵翻腾。他想起父亲说过,前朝皇室最喜欢用活人殉葬,难道天罗教的教主,真的在效仿隋炀帝?“前面就是万箭阵。 ”苏缺突然停在一道石门前,门上刻着只张着嘴的虎头,“破阵图呢? ”荣海城从怀里摸出块羊皮纸,上面是他连夜拓的破阵图。苏缺接过羊皮纸时,独眼突然闪过道寒光,手里的钥匙串猛地砸向石门上的虎头眼。石门轰然洞开的瞬间,荣海城听见箭羽破空的呼啸。他拽着芙珂扑到石壁后,眼睁睁看着苏缺被乱箭穿身,羊皮纸从他手里飘落,被一支箭钉在对面的墙上。“他是故意的!”芙珂的声音发颤,“他根本不是要破阵图,是想让我们跟着送死!”荣海城盯着苏缺的尸体,突然发现他缺了小指的右手里,攥着块碎玉。玉上刻着个“唐”字,是暗卫营的腰牌碎片——这苏缺,竟是朝廷安插在天罗教的密探!“他在拖延时间。 ”荣海城突然反应过来,“万箭阵的箭雨只会持续一炷香,他是想让我们等箭停了再走。 ”箭雨停时,地宫里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荣海城捡起那支钉着羊皮纸的箭,发现箭杆上刻着行小字:“秦女在血池,速去。”血池在地宫最深处,池边立着尊青铜雕像,雕的是个披甲的将军,手里握着柄长戟,戟尖正对着池中央的石台。 石台上绑着个穿红裙的少女,手脚都被铁链锁着,嘴里塞着布团,眼里却没有半分惧色。 “是秦珠!”芙珂的声音发急,“秦镖头的女儿!”荣海城刚要上前,青铜雕像突然动了。 长戟带着风声扫过来,他举刀去挡,只听“当”的一声脆响,碎星刀竟被震得脱手飞出。 “是‘机关人’。”芙珂扔出枚烟雾弹,拉着他躲到石柱后,“用千年玄铁做的,刀枪不入! ”烟雾里传来铁链拖地的声响,荣海城看见秦珠正拼命扭动,想挣开锁链。 可那铁链像是活的,越动收得越紧,已经勒进了少女的皮肉里。“我去引开机关人,你救秦珠!”荣海城突然冲出石柱,赤手空拳扑向青铜雕像。他记得破阵图上画着,机关人的关节处有块弱点,用蛮力就能拆开。芙珂的短匕划破铁链时,荣海城正被机关人的长戟逼到血池边。池里的血水泛着泡泡,散发出甜腻的腥气,他瞥见池底沉着无数白骨,都是被当作祭品扔进池里的人。“荣大哥!”芙珂拽起秦珠,突然尖叫一声,“小心后面!”荣海城转身时,看见个黑袍人站在机关人身后,手里举着个铜铃。铃声响起的瞬间,机关人的动作突然变快,长戟带着劲风刺向他的胸口。 “是天罗教主!”芙珂将秦珠推到石柱后,自己举着短匕冲过来,“他能操控机关人! ”黑袍人掀开兜帽,露出张苍白的脸。他的左眼是空洞的黑洞,右眼却亮得惊人,像淬了毒的蛇眼:“荣家军的后人,果然有几分本事。”荣海城认出他了。三年前在岭南,就是这只独眼,看着他把那个中了牵机引的孩童,抱进了焚尸炉。“你是唐门的余孽! ”他的声音发颤,“当年岭南的叛党,就是你勾结的!”“是又如何?”教主冷笑一声,铜铃摇得更急,“你以为你父亲真是病死的?他是被我用牵机引毒死的,死前还在喊你的名字呢。”荣海城的脑子“嗡”的一声。父亲临终前确实全身僵硬,像块石头,当时他以为是积劳成疾,没想到……“我杀了你!”他像头疯了似的扑过去,手指抠向教主的独眼。就在他指尖触到对方皮肤的瞬间,突然觉得心口一麻。低头时,看见支淬了毒的飞爪,正扎在自己的胸口——爪尖淬的,正是牵机引!“荣大哥! ”芙珂的短匕刺穿了教主的肩膀,可她自己也被机关人的长戟扫中,青裙上顿时染开片血红。 荣海城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凝固,视线开始模糊。他看见教主捂着肩膀后退,看见芙珂倒在血泊里,还看见秦珠从石柱后冲出来,手里举着块石头,狠狠砸向机关人的关节。“破阵图……在玉佩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扯下脖子上的玉佩,朝芙珂扔过去。玉佩落在芙珂手边时,荣海城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僵。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想起姑姑留在雁门关的传说,想起芙珂鬓边的玛瑙步摇……原来这江湖路,从一开始就是场骗局。意识消失的前一秒,他看见芙珂捡起玉佩,眼里的泪落在上面,映出玉佩背面刻着的字——那不是破阵图,是“荣晚照”三个字,是他姑姑的名字。第五章 长安雪落,恩仇难偿荣海城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辆马车上。车帘外飘着雪,落在梅枝上簌簌作响,像极了他小时候在荣家老宅,听姑姑弹的琵琶声。“你醒了?”芙珂端着碗药进来,青裙上的血迹已经洗净,鬓边换了支素银簪,“这是用九转回魂草熬的,能暂时压制牵机引。 ”荣海城没接药碗:“为什么救我?”芙珂的手顿了顿:“因为你是荣大哥。 ”“我不是你荣大哥。”他别过脸,“我是朝廷暗卫,是来抓前朝余孽的。 你这前朝公主的身份,还有天罗教的阴谋,我都该上报朝廷。”车帘被风吹开,飘进片雪花,落在芙珂的手背上。她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以为苏缺为什么要帮你? 他是你父亲当年安插的眼线,临死前发了密信回暗卫营,说天罗教的教主,其实是当今圣上的私生子。”荣海城猛地坐起来,胸口的伤口被扯得生疼:“你说什么? ”“当年你父亲发现了这个秘密,才被教主灭口。”芙珂的声音很轻,“我娘不是荣晚照,是你父亲的养女,也是暗卫营的人。她留在秦府,就是为了查教主的身份。 ”马车载着他们进了长安,雪越下越大,把朱雀大街的青石板盖得严严实实。 荣海城站在暗卫营的门前,看着芙珂从怀里摸出块腰牌——那是他父亲的暗卫腰牌,背面刻着个“珂”字。“我叫芙珂,不姓杨。”她把腰牌塞给他,“我娘说,等查清真相,就让我用这个身份,认祖归宗。”荣海城握紧腰牌,金属上还带着芙珂的体温。 他突然想起地宫血池边,她扑向教主时的决绝,想起她用荧石短匕照亮前路的模样,想起她鬓边那枚沾过血的玛瑙步摇……原来那些所谓的阴险狡诈,不过是她在江湖里,为了活下去的伪装。“天罗教主呢?”“被秦珠用机关人的长戟杀了。”芙珂望着漫天飞雪,“那丫头说,她爹当年就是被教主胁迫,才偷了鸽符。现在仇报了,她要带着秦镖头的骨灰,回江南老家。”荣海城突然笑了。这江湖,果然是恩将仇报,也是仇将恩报。 他杀过无辜的人,也被他要抓的“逆党”所救;他信错了人,也被欺骗过,可到头来,支撑他走下去的,不是朝廷的命令,不是荣家的仇恨,是芙珂递过来的那碗药,是秦珠砸向机关人的那块石头,是苏缺用命换来的密信。“去荣家老宅看看吧。”他突然说,“那里的梅花开了,像你鬓边的玛瑙。”芙珂的眼里亮了亮,像落了星光:“好。 ”荣家老宅的梅树下,荣海城用碎星刀挖了个坑,把父亲的玉佩埋了进去。雪落在坑里,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像给往事盖了层被子。“牵机引的毒,还能解吗? ”芙珂的声音带着点哽咽。荣海城摸了摸胸口的伤口,那里的僵硬已经蔓延到指尖:“解不了。但能多活几个月,看长安的雪,看江南的梅,够了。 ”他突然抓住芙珂的手,她的指尖还是凉的,却比地宫血池的水要暖。“你说江湖险恶,可我觉得,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江湖最好的模样。”雪越下越大,落在两人的发间,像染了层白霜。芙珂从袖中摸出支短匕,正是那把刻着蚀骨纹的荧石匕,她把匕尖对准自己的手腕:“九转回魂草能续命,只要把我的血输给你……”荣海城按住她的手:“别傻了。我这暗卫的命,早就该在岭南那场大火里烧尽了。能多活这几个月,看你笑,看雪落,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赏。 ”他从怀里摸出个东西,塞进芙珂手里——是那支银步摇,玛瑙在雪光里泛着温润的红。 “这步摇,原是我姑姑的嫁妆。当年她没来得及用,现在送给你。”芙珂攥着步摇,指节泛白:“荣大哥……”“叫我海城吧。”他笑了笑,胸口的僵硬已经到了脖颈,“等我走了,你就拿着我父亲的腰牌,去暗卫营报到。那里有我安排的人,会护着你。 ”雪花落在荣海城的睫毛上,结了层薄冰。他看着芙珂的脸,突然觉得这长安的雪,比岭南的雨要温柔,比地宫的血要干净。“珂儿,”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若有来生,我不当暗卫,你也不是什么前朝公主,我们就守着这荣家老宅,种梅,煮茶,好不好? ”芙珂的泪落在他的脸上,滚烫的,像要把结的冰融化。她点了点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荣海城的眼睛慢慢闭上时,手里还攥着片梅花瓣。那花瓣被他的体温焐得发暖,像极了芙珂掌心的温度。雪还在下,落满了荣家老宅的屋顶,落满了梅枝,也落满了芙珂的发间。她站在梅树下,手里攥着那支银步摇,直到天亮时,雪地里留下两串脚印,一串深,一串浅,像未写完的诗,像未完的江湖路。后来,长安城里多了个女暗卫,腰佩荧石匕,鬓插玛瑙步摇,据说她总在雪天去荣家老宅,在梅树下站一整天。有人说她是前朝余孽,有人说她是行侠仗义的女侠,可没人知道,她的怀里总揣着半块玉佩,背面刻着“荣晚照”三个字,像个永远不会说出口的秘密。 而那把碎星刀,被芙珂埋在了梅树下,和荣海城的尸骨一起,守着长安的雪,守着那段恩仇难偿的江湖岁月。刀身的纹路里,永远浸着梅香,像他最后那句未完的话——“珂儿,这江湖路,有你,真好。”第六章 梅下旧物,刀影藏心三年后的长安,雪落得比往年更急。芙珂站在荣家老宅的梅树下,指尖抚过树干上斑驳的刻痕——那是荣海城当年用碎星刀刻的,歪歪扭扭的“荣”字,被岁月磨得只剩浅淡的印记。她如今已是暗卫营的百户,腰间悬着父亲的旧腰牌,鬓边的玛瑙步摇换了支素银的,唯有那把荧石短匕,始终别在袖中。刚才在暗卫营的密档里,她翻到了一卷泛黄的卷宗,封皮上写着“岭南旧事”。卷宗里夹着张画像,画中少年眉眼清亮,背着柄比人还高的刀,站在渭水畔的芦苇丛里。 芙珂的指尖划过画像上的落款——“海城十七岁,初入营”。原来他当年,也曾有过这般飞扬的模样。“百户大人,”身后传来下属的声音,“查到了,当年给天罗教主提供牵机引的,是唐门现任门主唐缺。”芙珂转过身,雪落在她的睫毛上,瞬间融成水珠。唐缺,这个名字她记得。三年前在地宫,荣海城说过,岭南的叛党就是他勾结的。“备马。”她的声音裹在雪风里,带着荧石的冷光,“去唐门。 ”唐门所在的青城山,终年云雾缭绕。芙珂站在山门处,看着石阶上斑驳的血迹——那是三年前,荣海城带人围剿唐门余孽时留下的。 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场围剿,本就是天罗教主设的局,目的是铲除异己。“来者何人? ”山门后传来沙哑的声音,个拄着拐杖的老者走了出来,左眼蒙着黑布,正是唐缺。 芙珂的短匕在袖中轻颤:“荣海城的故人。”唐缺的身体僵了僵,蒙眼布下的嘴角扯出抹冷笑:“原来是荣大侠的人。怎么,他自己不敢来,派个女娃娃来送死?”“他死了。”芙珂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件寻常事,“中了你的牵机引,死在长安的雪地里。”唐缺突然大笑起来,拐杖在石阶上敲得笃笃响:“死得好! 当年他在岭南,杀了我儿子,烧了我唐门的药庐,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 ”芙珂的短匕突然出鞘,荧石的光映出唐缺耳后的月牙形疤痕——和当年偷鸽符的人,一模一样。“秦镖头的牵机引,是你下的。”她的刀尖抵住唐缺的咽喉,“天罗教的飞爪,也是你做的。你帮教主偷鸽符,帮他毒杀海城的父亲,甚至帮他设计围剿唐门,就是为了报你儿子的仇?”唐缺的喉结动了动:“是又如何?荣海城就是个刽子手! 他以为自己行侠仗义,可他杀的那些人,哪个不是被教主胁迫的? 我儿子……我儿子只是给叛党送过药,就被他挑断了手筋,最后在牢里活活饿死! ”芙珂的手在抖。卷宗里没写这些,只说荣海城在岭南“肃清叛党,功绩卓著”。 原来那些所谓的功绩,背后藏着这么多血债。“你可知他为什么杀你儿子? ”她突然收回短匕,“因为你儿子用牵机引毒杀了三个暗卫,其中一个,是他情同手足的兄弟。”唐缺愣住了,蒙眼布下的眼眶微微颤动。“他在岭南烧的药庐,藏着教主私通突厥的密信。”芙珂从袖中摸出卷纸,扔在唐缺脚下,“这是从他遗物里找到的,你自己看。”密信上的字迹扭曲狰狞,正是教主的手笔。 唐缺捡起密信,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突然将密信狠狠摔在地上,拐杖劈碎了石阶:“我竟被他骗了这么多年!我竟帮着仇人报了假仇! ”芙珂看着他痛苦的模样,突然想起荣海城临终前的眼神。那里面有不甘,有遗憾,却唯独没有恨。或许他早就知道,这江湖里的恩仇,从来都分不清对错。“牵机引的解药,你有吗?”她突然问。唐缺抬起头,蒙眼布下的泪浸湿了胡须:“有。 但需要用唐门的‘血莲’做药引,那花十年才开一次,昨天刚谢。”芙珂的指尖划过荧石匕,匕身映出自己眼底的红。原来有些债,注定是还不清的。“我不是来要解药的。 ”她转身往山下走,“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临终前,托我给唐门留句话——当年烧药庐时,他特意避开了药圃里的幼苗,那些是你儿子亲手种的。”唐缺的拐杖“当啷”落地,在空荡的山门前,传来迟来的呜咽。第七章 血莲重开,江湖新生回长安的路上,芙珂绕道去了潼关。青龙庙的地宫早已被封死,只留下断壁残垣,在夕阳里像头沉默的巨兽。 秦珠正在庙前的空地上晒草药,红裙在风里翻飞,像极了当年血池里的那抹艳色。 她看见芙珂,放下手里的活计,笑着迎上来:“芙珂姐姐,你可算来了!”“药圃怎么样了? ”芙珂看着她身后的田垄,里面种满了绿油油的幼苗。“好得很!”秦珠指着最边上的畦田,“你看,这是唐前辈送来的血莲种子,说十年后就能开花了。”芙珂的心里动了动。 唐缺最终还是把血莲的种子给了秦珠,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偿还些什么。“暗卫营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秦珠递过来个药包,“这是用溯灵草做的香囊,能安神。你总说睡不着,枕着这个试试。”芙珂接过香囊,里面的草药味清苦,像荣海城留在她记忆里的味道。 她突然想起三年前,在地宫里,秦珠用石头砸向机关人时,眼里的决绝——这江湖里的女子,总是比想象中更坚韧。“我要去趟西域。”芙珂突然说,“教主虽然死了,但他勾结突厥的密道还在,我得去封死它。”秦珠的眼睛亮了:“我跟你一起去! 我爹当年押的镖,就是往西域送的,我熟路!”芙珂看着她眼里的光,突然笑了。这江湖路,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走的。西域的风沙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芙珂和秦珠骑着马,走在当年荣海城追查叛党时走过的路上。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像极了他碎星刀的寒光。“芙珂姐姐,你看!”秦珠突然指着前方,“那是不是平衡树? ”路边的戈壁上,长着棵奇怪的树,一半枝繁叶茂,一半枯枝败叶,正是传说中的平衡树。 芙珂翻身下马,走到树下,发现树干上刻着行字——“守人间清明”,字迹苍劲,是荣海城的笔锋。她突然明白,他当年说的“行侠仗义”,从来都不是空话。 他用暗卫的身份做掩护,在黑暗里守护着些什么,哪怕被误解,被仇恨,也从未停下脚步。 密道的入口在雪山深处,被厚厚的冰层封着。芙珂用荧石匕劈开冰层,里面黑漆漆的,像头张着嘴的巨兽。“我先进去。”她回头看了眼秦珠,“你在外面等着,若我半个时辰没出来,就点燃烽火台,通知边关的守军。”秦珠攥紧了手里的火把:“不行! 要进一起进!”密道里的寒气刺骨,芙珂的荧石匕照亮了两旁的壁画——上面画着突厥铁骑入关的场景,血腥而惨烈。 她突然想起荣海城留下的卷宗里写的:“密道若开,长安危矣。”走到密道尽头,是道石门,门上刻着天罗教的图腾。芙珂举起短匕,正要劈下去,突然发现门楣上刻着行小字——“荣家军在此”。是他祖父当年平定西域时,留下的印记。 原来这密道,早就被荣家军发现,只是因为工程量太大,没能彻底封死。“用这个试试。 ”秦珠突然递过来个东西——是荣海城的碎星刀。当年芙珂把它埋在梅树下,秦珠偷偷挖出来,磨得锃亮。芙珂握住刀柄,上面的纹路硌着掌心,像他残留的温度。 她举起刀,用力劈向石门上的图腾。“轰隆”一声巨响,石门轰然倒塌,后面露出的不是通往关内的路,而是堵厚厚的土墙——原来荣家军早就把密道封死了,天罗教的教主,从一开始就是在痴心妄想。风沙从石门的缺口灌进来,吹得人睁不开眼。 芙珂站在土墙上,看着远处的雪山,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又满满的。“我们回去吧。 ”她对秦珠说,“长安的梅,该开了。”回去的路上,秦珠突然问:“芙珂姐姐,你说荣大哥在天上,会不会看着我们?”芙珂抬头看向天空,流云飘过,像他当年在长安雪地里,笑起来时眼角的纹路。她点了点头:“会的。他会看着我们,把这江湖,走成他希望的模样。”荣家老宅的梅花开了,粉白的花瓣在雪地里格外显眼。 芙珂站在树下,将碎星刀重新埋进土里,旁边是秦珠种下的血莲种子。 她从袖中摸出那支银步摇,玛瑙在雪光里泛着温润的红。她把步摇插在梅枝上,像给这棵老树,别了支嫁妆。“海城,”她轻声说,“这江湖路,我替你走下去。 ”风穿过梅枝,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回应。远处的长安城里,传来了打更的声音,清脆,安稳,像无数人用生命守护的,人间清明。后来,江湖上少了个叫芙珂的女暗卫,多了个背着荧石匕的游医,走遍大江南北,救死扶伤,身边总跟着个穿红裙的少女,据说她们在找一种叫血莲的花,说那花开的时候,能治愈所有的伤痛。 而荣家老宅的那棵梅树,每年冬天都会开出格外艳的花,有人说,那是因为树下埋着把刀,刀里藏着个人,人心里,揣着整个江湖的温柔。第八章 十年花开,雪落有声十年后的长安,雪似乎比往常更缠绵。芙珂坐在荣家老宅的梅树下,手里捧着盏温热的茶,看秦珠在院子里扫雪。红裙早已换成了素色布裙,当年扎着总角的少女,如今鬓边也别上了简单的木簪。“芙珂姐,你看!”秦珠突然举着株含苞的花跑过来,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红,像染了层胭脂,“血莲真的开了!”芙珂接过那株花,指尖触到冰凉的花瓣,突然想起十年前唐缺临终前的模样。老人把血莲种子交给秦珠时,枯瘦的手指在种子上摩挲了很久:“告诉那丫头,当年牵机引的解药,其实不用血莲也行……是我骗了她,我只是不想她再为仇恨困住。”原来有些谎言,是为了让人放下。“唐门的孩子们怎么样了?”芙珂将血莲插进青瓷瓶里,瓶身上的冰裂纹路,是当年荣海城用碎星刀不小心划的。“都好。”秦珠擦了擦手上的雪,“唐大哥接了门主之位,上个月还派人送来新药,说能治风寒。”唐大哥是唐缺的孙子,当年才五岁,被芙珂从唐门废墟里抱出来时,怀里还揣着半块发霉的饼。 如今已是能独当一面的江湖医者,背着药箱走遍南北,像极了当年的秦镖头。 院门外传来马蹄声,芙珂抬头,看见个穿玄色劲装的少年翻身下马,背上的长刀在雪光里闪着冷光——那是柄和碎星刀很像的刀,只是刀身更窄,刻着细密的云纹。“百户大人,”少年单膝跪地,声音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暗卫营急报,漠北发现天罗教余孽,正勾结回纥部落,想在雁门关外闹事。 ”芙珂接过密信,指尖划过信上的朱砂印。十年前她辞去了暗卫营的职务,却始终和营里保持着联系。有些责任,就算脱下了官服,也卸不掉。“备两匹快马。 ”她站起身,梅枝上的雪落在肩头,“秦珠,你守着院子,我去去就回。 ”秦珠却从屋里拎出个包袱:“我跟你去。当年我爹在雁门关押过镖,那里的地形我熟。 ”芙珂看着她眼里的坚定,突然想起十年前在西域密道,这丫头也是这样,攥着火把不肯后退。她笑了笑,接过包袱:“走。”雁门关的雪比长安更烈,卷着沙砾打在脸上,像小刀子。芙珂站在关隘上,看着远处的戈壁,风里似乎还飘着当年荣家军的号角声。“芙珂姐,你看那!”秦珠指着戈壁尽头的黑点,“是回纥的骑兵!”芙珂握紧腰间的荧石匕,刀鞘上的纹路被摩挲得发亮。十年间,她用这把刀杀过恶人,救过好人,却再没动过牵机引——唐缺临终前说,最好的解药,是心里的放下。“他们人不多,像是诱饵。”芙珂眯起眼,看见骑兵后面的沙丘里,藏着无数黑影,“天罗教的人想引我们出关,在戈壁里设埋伏。”秦珠从包袱里掏出张地图,上面用朱砂标着雁门关的布防:“我爹说过,关隘西侧有个暗道,能绕到沙丘后面。 ”夜袭的时候,雪停了。芙珂的荧石匕在黑暗里划出冷光,每一刀都避开要害,只挑断对方的经脉。她想起荣海城当年在地宫,明明可以杀了教主,却只是刺穿了他的肩膀——原来有些狠戾,是逼出来的,而真正的强大,是懂得留有余地。 沙丘后的帐篷里,绑着个白发老者,脸上刻着天罗教的图腾。芙珂认出他了,是当年教主的副手,三年前在青龙庙地宫,被秦珠用石头砸断了腿。“你终究还是来了。 ”老者笑起来,牙床都露在外面,“荣海城的女人,果然和他一样蠢,明知是陷阱还要跳。 ”芙珂的刀抵住他的咽喉:“当年你把秦镖头的女儿扔进血池,就该想到有今天。 ”“我只是奉命行事!”老者突然嘶吼起来,“是荣海城!是他当年在洛阳渡口,杀了我唯一的儿子!我儿子只是个撑船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密使!”秦珠突然捂住嘴, |
精选图文
 陆皎皎季晏礼新书陆皎皎季晏礼看全文小说-陆皎皎季晏礼小说资源阅读陆皎皎季晏礼
陆皎皎季晏礼新书陆皎皎季晏礼看全文小说-陆皎皎季晏礼小说资源阅读陆皎皎季晏礼 梁沐荞江鹤时是什么小说-梁沐荞江鹤时免费小说在线阅读
梁沐荞江鹤时是什么小说-梁沐荞江鹤时免费小说在线阅读 梁沐荞江鹤时小说全文完整版 梁沐荞江鹤时免费阅读
梁沐荞江鹤时小说全文完整版 梁沐荞江鹤时免费阅读 陆皎皎季晏礼全文(陆皎皎季晏礼免费小说-完整版-陆皎皎季晏礼在线赏析)最新章节已更新版
陆皎皎季晏礼全文(陆皎皎季晏礼免费小说-完整版-陆皎皎季晏礼在线赏析)最新章节已更新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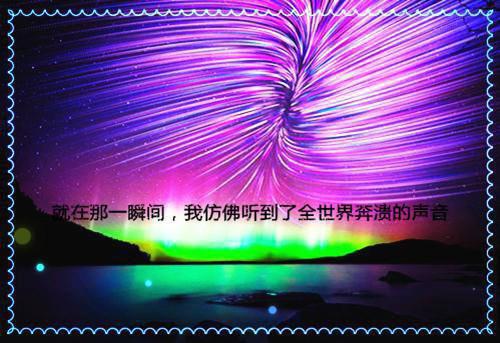 【新书】许溪蒋震霆全文全章节免费阅读-退婚后,八零肥妻被糙汉娇宠了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新书】许溪蒋震霆全文全章节免费阅读-退婚后,八零肥妻被糙汉娇宠了 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楚小梨萧淮小说(楚小梨萧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楚小梨萧淮小说小说楚小梨萧淮小说列表(楚小梨萧淮)
楚小梨萧淮小说(楚小梨萧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楚小梨萧淮小说小说楚小梨萧淮小说列表(楚小梨萧淮) 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列表(季枝遥谢云礼)
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小说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列表(季枝遥谢云礼) 季枝遥谢云礼(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免费阅读)季枝遥谢云礼最新章节列表(季枝遥谢云礼小说)
季枝遥谢云礼(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枝遥谢云礼小说免费阅读)季枝遥谢云礼最新章节列表(季枝遥谢云礼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