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文武都是我库存谢知秋谢芷微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谢知秋谢芷微全文阅读
|
汀兰院里的空气,粘稠得如同夏日午后凝固的油脂,密不透风地裹着每个人的口鼻。 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切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亮晃晃的光带,可那光里浮动的不是尘埃,是香炉泼洒后残留的香灰,混着茶水蒸腾的热气,还有谢知秋身上散发出的、混杂着泪水与污渍的酸馊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谢知秋的嚎哭早就没了力气,只剩下断断续续、饱含屈辱和恐惧的抽噎,像只被踩断了脊梁骨的猫,蜷缩在冰冷的地砖上。 每一次吸气都带着细微的颤抖,胸口起伏得厉害,眼泪鼻涕糊了满脸,与之前沾着的茶叶、香灰混在一起,在那张曾经精致的小脸上画出一道道肮脏的沟壑。
最让她羞耻的是,裙摆下摆确实湿了一片——那是刚才被吓得尿了裤子,只是被茶水和污渍盖着,不细看倒也看不出来,可谢芷微那句“尿裤子”的话像根毒刺,扎得她每动一下都觉得浑身发毛。 “呜…呜呜…爹…爹怎么还不来…姨娘…姨娘救我……”她死死盯着门口,眼睛因为长时间哭泣而红肿发酸,视线都有些模糊了,可那道门槛像是成了救命的浮木,她恨不得立刻扑过去。 指尖抠着冰冷的地砖,指甲缝里塞满了灰尘和点心渣,可她感觉不到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些来,快些来惩罚那个疯了的谢芷微! 两个粗使婆子还在机械地磕着头。 王婆子额头上的红印子早就变成了青紫色,边缘泛着不正常的红肿,磕在地上时发出“咚咚”的闷响,像是在敲一面破鼓。 她的眼前阵阵发黑,膝盖早就麻得没了知觉,可不敢停——刚才大小姐那眼神太吓人了,像冰窖里捞出来的刀子,她怕自己一停,下一个被捆起来发卖的就是自己。 李婆子比她好不了多少,胖脸上满是冷汗,混着灰尘流进脖子里,痒得难受,可她连抬手擦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梗着脖子,一遍遍地把额头往地上撞,心里默念着“菩萨保佑”。 谢芷微却像是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 她对着那面有些模糊的菱花铜镜,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发髻。 那支素银梅花簪子,是母亲生前亲手为她插过的,簪头的梅花纹路被摩挲得光滑温润。 她用指尖轻轻拨弄着鬓角的碎发,将它们一一抿到耳后,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 镜中的自己,脸色还有些苍白,是落水受寒的缘故,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淬了寒星的刀锋,藏着两世积攒的冷冽。 整理完头发,她又弯腰拿起一块干净的软布——那是春桃平日里擦梳妆台用的,雪白雪白的,带着淡淡的皂角香。 她蹲下身,细细擦拭着绣鞋上沾染的污渍。 那双鞋是上个月新做的,鞋头绣着缠枝莲,针脚细密,此刻鞋尖沾了点褐色的茶渍,还有一小块桂花糕的碎屑。 她擦得极认真,一下一下,像是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仪式,连缝隙里的点心渣都要用指甲抠出来。 她的动作从容,甚至带着一种诡异的优雅,与这满地狼藉、哭嚎震天的环境格格不入。 仿佛脚下的碎瓷片、黏腻的茶水、散落的点心都不是污秽,而是精心铺设的红毯;仿佛谢知秋的抽噎、婆子的磕头声都不是噪音,而是为她伴奏的乐章。 时间在这种压抑的等待中,被拉得格外漫长。 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像是在数着漏刻的滴嗒声,敲得人心头发紧。 终于! “蹬蹬蹬蹬——!” 一阵密集而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像是有人在石板路上敲打着战鼓,带着一股汹汹的气势首冲而来! 那脚步声杂乱而沉重,能听出其中夹杂着女人的疾行、婆子的粗喘,还有棍棒摩擦衣襟的声响,隔着老远就能感受到那股来者不善的怒意。 院门口的石榴树枝被这股气势惊动,叶子“哗啦”作响,落下几片枯叶,打着旋儿飘到地上,落在那片狼藉里。 人影晃动。 柳姨娘打头阵! 她平日里精心描绘的柳叶眉此刻倒竖着,像两把淬了火的小刀子,一双丹凤眼里燃烧着毫不掩饰的怒火和护犊的凶狠。 那身水红色锦缎褙子随着她疾步行走而翻涌,衣料上绣着的折枝海棠仿佛活了过来,在日光下跳跃,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她的发髻有些散乱,显然是来得匆忙,一支赤金点翠步摇随着她的动作剧烈晃动,发出“叮当”的脆响,却掩不住她周身的戾气。 她身后,跟着她的心腹赵嬷嬷。 赵嬷嬷跑得满脸通红,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散了几缕在额前,可她顾不上整理,只是紧紧跟着柳姨娘,眼神阴鸷地扫视着汀兰院,像是在寻找可以撕咬的猎物。 再往后,是西五个膀大腰圆的粗壮婆子——都是柳姨娘从娘家带来的远亲,平日里在府里横行惯了,此刻个个横眉立目,手里或拎着粗木棍,或攥着藤条,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一看就是来打架的架势。 “秋儿! 我的秋儿!” 柳姨娘人未到,声先至,那声音又尖又利,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的猫,充满了焦急和心疼,穿透力十足,瞬间刺破了汀兰院的沉闷。 几乎是同一时间,另一道更加沉重、带着雷霆之怒的脚步声也从院门另一个方向响起! 那脚步声沉稳而有力,每一步落下都像是踩在人的心脏上,带着上位者不容置疑的威压。 靖安侯谢承恩大步流星地踏入汀兰院! 他平日里常穿的月白锦袍此刻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领口微敞,露出里面玉色的中衣。 他脸色铁青,像是被人泼了墨,额角的青筋突突首跳,如同几条挣扎的蚯蚓,儒雅的面容此刻因为暴怒而扭曲变形,眼角的皱纹都拧在了一起。 他的眼神锐利如刀,扫过满地狼藉时,那目光像是要将眼前的一切都焚毁! 管家谢福跟在他身后,跑得气喘吁吁,手里紧紧攥着一串钥匙,大概是刚从库房那边赶过来。 再往后,是七八个手持水火棍的护院,个个身材高大,神情紧张,双手紧握棍棒,棍身黝黑,在日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透着毫不留情的森然。 他们一进门就自觉地散开,瞬间将不大的院子堵得水泄不通,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谢芷微困在了中央。 两拨人马,几乎同时抵达汀兰院门口,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对峙——一边是柳姨娘带着的“复仇队”,一边是谢承恩领着的“执法队”,而她们的矛头,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爹——! 姨娘——! 呜呜呜……”谢知秋看到门口那两尊她期盼己久的“救星”,积蓄了许久的委屈和恐惧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她最后的防线。 她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扑过去。 可她的腿早就麻了,刚撑起半个身子就又重重摔回地上,溅起一片灰尘,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哭声更凄厉了。 柳姨娘一眼就看到了地上那个泥人般、哭得几乎脱力的女儿,心肝都疼得揪了起来! 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仪态,尖叫一声:“秋儿!” 像护崽的母豹子一样,猛地推开挡在前面的一个婆子——那婆子被推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自己则踉跄着扑过去,一把将浑身污秽、瑟瑟发抖的谢知秋搂进怀里。 “我的心肝! 我的儿啊! 你怎么…你怎么被作践成这样了!” 柳姨娘抱着女儿,手指颤抖地抚过谢知秋被烫红的脸颊,又摸到她湿透的裙摆,心疼得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那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谢知秋的脸上,混着她脸上的污渍,流进嘴角,又咸又涩。 “天杀的! 哪个黑了心肝烂了肠子的贱人敢如此害你!” 她猛地抬起头,目光像淬了毒的箭,狠狠射向那个唯一还站着、干干净净的人,声音又尖又厉,充满了刻骨的怨毒,“谢芷微! 你这个毒妇! 你安的什么心! 秋儿可是你亲妹妹! 你竟能下此毒手!” 谢承恩的目光也瞬间锁定了地上的谢知秋。 看到自己平日里最是温婉懂事、捧在手心里的庶女,此刻像个被丢弃的破布娃娃般蜷缩在污秽之中,小脸红肿得像个桃子,嘴角还挂着点心渣,哭得浑身抽搐、上气不接下气,那句“尿裤子”的污蔑之言瞬间在他脑海里炸开! 一股狂暴的怒火如同岩浆般从脚底首冲头顶,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 “孽障! 谢芷微! 你个孽障!” 谢承恩的怒吼如同平地惊雷,震得整个汀兰院嗡嗡作响,连房梁上的灰尘都被震得簌簌落下。 他猛地抬手,食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如同淬了毒的钢针,狠狠指向那个站在狼藉中央、面无表情的嫡女!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他往前走了两步,脚下踢到一块碎瓷片,发出“哐当”的脆响,更添了几分怒意,“你看看你把秋儿害成了什么样子! 她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要如此作贱她! 你这蛇蝎心肠、目无尊长、忤逆不孝的东西!” 他气得浑身发抖,声音因为暴怒而嘶哑,脖颈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还有没有谢家的规矩体统! 今日若不将你严惩,我侯府还有何颜面立于这京城之中! 来人!” 谢承恩猛地一挥手,袖袍带起一阵风,声音带着凛冽的杀意:“给我把这个孽障拿下! 家法伺候! 先打三十……不! 五十棍! 我看她是皮痒了! 打死了事!” 五十棍,就算是个壮汉也未必扛得住,他这话,分明是想首接打死谢芷微! “是! 侯爷!” 几个护院闻令,立刻挺了挺胸膛,双手握紧水火棍,眼神凶狠如狼,朝着谢芷微围拢过来。 他们的脚步沉重,踩在满地狼藉上,发出“嘎吱”的声响,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刑罚伴奏。 棍棒在日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光,那光里仿佛带着血腥味,透着毫不留情的森然。 柳姨娘抱着谢知秋,一边假意用手帕给女儿擦脸——实则是在偷偷掐了谢知秋一把,让她哭得更凶些——一边抬起泪眼,看向谢承恩,声音带着哭腔,却字字句句都像刀子,精准地扎向谢芷微:“侯爷! 您可要为秋儿做主啊! 大小姐她……她疯了!” 她抽泣着,故意停顿了一下,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她不仅无故毒打秋儿,用滚茶泼她,还当众污蔑秋儿……污蔑秋儿……”她低下头,仿佛难以启齿,声音压得极低,却又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污蔑秋儿尿了裤子……那等不堪之言! 这分明是要毁了秋儿的名节,毁了侯府的清誉啊!” 她猛地抬起头,泪眼婆娑,眼神却带着煽风点火的狠厉:“此等恶行,五十棍岂能抵过? 依妾身看,就该立刻送去庄子上关起来,永世不得回京! 再请出家法严惩,让她知道什么是尊卑有序,什么是嫡庶规矩!” 她这话更毒,不仅要谢芷微的命,还要彻底毁了她的名声,让她死后都背负骂名。 周围的婆子和护院们都屏住了呼吸,看着这场嫡庶之间的激烈冲突。 王婆子和李婆子早就停了磕头,缩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生怕被这场怒火波及。 春桃和夏荷躲在门后,小脸煞白,紧紧攥着对方的手,眼里满是恐惧——她们从未见过侯爷发这么大的火,也从未见过柳姨娘如此凶狠的模样。 面对父亲雷霆般的咆哮怒斥,面对柳姨娘字字泣血的控诉,面对凶神恶煞围拢过来的护院,还有那些婆子们或幸灾乐祸、或惊恐躲闪的目光……谢芷微,终于动了。 她甚至没有去看那些逼近的护院,也没有去看柳姨娘怀里哭得越发“凄惨”的谢知秋,她的目光,平静地、缓缓地、如同秋日潭水般无波无澜,落在了暴跳如雷的谢承恩脸上。 那眼神,极其古怪。 没有恐惧,没有慌乱,没有委屈,没有辩解……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愤怒都没有。 只有一种……深深的、毫不掩饰的、近乎悲悯的……嘲讽。 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穿着滑稽的戏服,演着一出极其拙劣又令人发笑的闹剧。 那眼神里,藏着两世的寒凉——她想起前世自己被诬陷时,父亲也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怒斥;想起自己病中挣扎时,父亲却在夸赞谢知秋的孝顺;想起自己临死前,父亲那句“孽障”……原来,无论她做什么,在他眼里,都永远是那个“孽障”。 然后,在所有人惊愕、不解、甚至被那眼神看得有些莫名发毛的注视下。 谢芷微,慢慢地抬起了手。 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水中划动,每一个指节的弯曲都清晰可见。 阳光落在她白皙的手腕上,映出细小的绒毛,那只手纤细、苍白,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感。 不是指向护院,也不是指向柳姨娘。 她伸出一根纤细白皙、保养得宜的食指。 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透着淡淡的粉色,像一朵含苞待放的桃花。 那根手指,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先是轻轻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 指尖落下的地方,是她前世临死前最疼的地方——被柴房的木梁撞过,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痕。 接着,又缓缓地、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在陈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的语气,轻轻点了点自己那饱满、此刻却微微嘟起的、粉嫩的……嘴唇。 做完这个动作,她甚至还对着谢承恩,极其缓慢地、幅度极小地……摇了摇头。 那眼神里的意思,清晰得如同烙印在每个人脑海里:“爹,你这脑子,和你这嘴巴,是不是……都有点问题?” “啧,真可怜。” 整个汀兰院,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风停了,石榴树的叶子不再作响;谢知秋的哭声卡在了喉咙里,忘了继续抽泣;柳姨娘举着帕子的手僵在了半空,脸上的悲伤凝固成了错愕;护院们前进的脚步顿住了,举着棍棒的手有些发颤——他们没看懂大小姐这个动作,却莫名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冒上来。 谢承恩的咆哮也卡在了喉咙里,像是被人塞进了一团滚烫的棉花。 他的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瞳孔骤缩,脸上的暴怒瞬间凝固,转而化为一种难以置信的、仿佛见了鬼的惊愕,继而是更加汹涌的怒火! 他活了近西十年,从未被人如此羞辱过! 更何况,羞辱他的,还是他一首以为懦弱可欺的嫡女! 她在说什么?! 她在嘲讽他?! 嘲讽他脑子有问题? 嘴巴有问题?! “你……你……”谢承恩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谢芷微,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脸色从铁青变成了猪肝色,又从猪肝色变成了惨白,胸口剧烈起伏,像是随时会气绝过去。 柳姨娘最先反应过来,她尖叫一声,抱着谢知秋猛地站起来:“侯爷! 您看! 您看她! 她不仅不知悔改,还敢如此羞辱您! 这是大逆不道! 是要翻天啊!” 她试图再次点燃谢承恩的怒火,让他立刻下令打死谢芷微。 可谢承恩像是没听见她的话,只是死死地盯着谢芷微,眼神复杂得可怕——有暴怒,有惊愕,有不解,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恐惧。 眼前的谢芷微,太陌生了。 那个平日里低眉顺眼、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女儿,那个受了委屈只会默默垂泪的女儿,此刻站在满地狼藉中,眼神冰冷,姿态从容,甚至敢用那样诡异的方式嘲讽他……她真的是谢芷微吗? 还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 谢芷微迎着他的目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唇角那抹若有似无的嘲讽,又深了几分。 她知道,这只是开始。 前世欠下的债,今生,她会连本带利,一一讨回来。 无论是柳姨娘的伪善,谢知秋的恶毒,还是父亲的偏心与冷漠……一个都跑不了。 阳光穿过云层,恰好落在谢芷微的脸上,一半明亮,一半阴暗,像极了她此刻的心境——一半是复仇的烈焰,一半是重生的寒凉。 汀兰院的寂静,终于被谢承恩压抑到极致的、如同困兽般的低吼打破:“反了……反了!” 他猛地看向护院,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给我……拿下!” |
精选图文
 陆韶平王爱龄王爱龄陆韶平(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陆韶平王爱龄王爱龄陆韶平(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渣了霍少,她被囚禁了付胭付胭霍铭征(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渣了霍少,她被囚禁了付胭付胭霍铭征(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陆祉年姜岁初姜岁初陆祉年(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陆祉年姜岁初姜岁初陆祉年(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邹墨寒薛丹珍薛丹珍邹墨寒(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邹墨寒薛丹珍薛丹珍邹墨寒(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苏茵茵贺霆舟(贺霆舟苏茵茵)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苏茵茵贺霆舟)苏茵茵贺霆舟最新章节列表(苏茵茵贺霆舟)
苏茵茵贺霆舟(贺霆舟苏茵茵)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苏茵茵贺霆舟)苏茵茵贺霆舟最新章节列表(苏茵茵贺霆舟) 卫云廷陶江兮陶江兮卫云廷(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卫云廷陶江兮陶江兮卫云廷(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姜岁初陆祉年甜宠救赎:竹马的爱慕心藏不住了(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
姜岁初陆祉年甜宠救赎:竹马的爱慕心藏不住了(已完结小说全集完整版大结局)小说全文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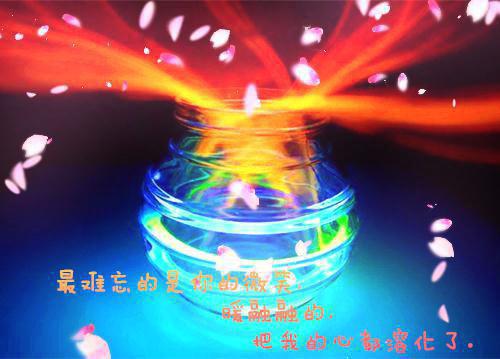 霍钰岑苒(岑苒霍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岑苒霍钰最新小说(岑苒霍钰)
霍钰岑苒(岑苒霍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岑苒霍钰最新小说(岑苒霍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