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夸我哥,我送他们上路陈昂陈昂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全家夸我哥,我送他们上路(陈昂陈昂)
|
他们都以为,今晚的家宴是为了庆祝我哥陈昂,拿下了那个价值三千万的项目。 餐桌上那瓶82年的拉菲,是我父亲炫耀的资本;我妈炖了一下午的佛跳墙,是我哥最爱的味道;就连我那拜金的嫂子,也戴上了我哥新买的卡地亚手镯,笑得花枝乱颤。 他们觥筹交错,高谈阔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骄傲。而我,陈默,这个家里的“沉默者”,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板。他们不知道,这场盛宴真正的主角,是我。是我精心策划的一切,是我为他们准备的最后晚餐。桌上的每一道菜,我都“加了料”,不是毒药,而是比毒药更精妙的东西——我那该死的“抑郁症”药片,头孢。医学常识说,头孢配酒,说走就走。而今晚,我将亲眼见证,这个冰冷的常识,如何在我这群所谓的“家人”身上,绽放成一朵最绚烂的、名为复仇的烟花。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最盛大的一场告别。1“小默,别光坐着,给你哥和你爸把酒满上啊! 愣着干什么?”我妈王秀兰的声音穿过饭桌上空,带着一丝习惯性的不耐烦。她的眼睛,像所有时候一样,只落在我哥陈昂身上,仿佛他才是会发光的太阳。我顺从地站起身,拿起那瓶被我爸擦了又擦的拉菲。暗红色的酒液在水晶吊灯下摇曳出惑人的光泽,像极了新鲜的血液。我小心翼翼地,先给父亲陈建国的杯里斟了三分之一,然后是我哥陈昂的,最后是嫂子李倩的。“爸,哥,嫂子,慢用。”我轻声说,然后坐回自己的位置,端起面前的橙汁。“看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父亲陈建国呷了一口酒,眉头立刻舒展开,但嘴里的话却像刀子一样扎过来,“你哥在外面拼死拼活,谈下这么大的单子,你呢?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连句像样的祝贺都不会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我低下头,看着橙汁里自己模糊的倒影,没有反驳。反驳有用吗?在这个家里,我的人生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用来反衬我哥陈昂的辉煌成功。他从小就是学霸,名校毕业,进入大公司,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部门总监。而我,成绩平平,大学毕业后不愿进厂,自己折腾着开了个小小的设计工作室。一年前,工作室资金链断裂,我走投无路,第一次低头向家里求助。我记得那个下午,我跪在父亲面前,求他借我二十万周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把我的计划书扔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二十万?你拿什么还?就你那个破工作室,几个月不开张,还想让我拿钱给你打水漂?我告诉你陈默,我们陈家没有赌徒!”而就在第二天,我亲眼看到,他笑呵呵地拿出五十万,给我哥换了一辆全新的宝马X5。
理由是:“我儿子是总监了,出门谈生意,车就是脸面,不能丢人。”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彻底崩塌了。从那天起,我关了工作室,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他们说我得了“心病”。医生诊断为重度抑郁,给我开了药。其中一种,就是头孢拉定胶囊。 他们每天监督我吃药,不是关心我的死活,而是怕我死在家里,给这个“光荣”的门楣抹黑。 “建国,少说两句,今天高兴。”我妈夹了一块鲍鱼放进我哥碗里,嘴上劝着,眼睛里却没有丝毫对我的心疼,“小默,你也多吃点,看你瘦的。 ”嫂子李倩抚摸着手腕上的钻石手镯,娇声笑道:“妈,您就别管他了。他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像我们家陈昂,真是越看越有本事。爸,您说是不是?”“那是! ”陈建国红光满面,举起酒杯,“来,我们一家人,敬阿昂一杯!我们陈家的骄傲! ”“谢谢爸,谢谢妈。”陈昂得意地举杯,目光扫过我,带着一丝轻蔑的怜悯,“小默,你也别灰心。哥以后多的是项目,随便给你找个跑腿的活儿干干,也比你在家发霉强。 ”他们三人碰杯,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看着他们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即将喷薄而出的兴奋。期待感。原来,这就是期待感。 过去一年里,我以为这种情感已经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了。但现在,它像一棵疯狂的藤蔓,缠绕着我的心脏,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却又带来了病态的快感。我期待着,酒精在他们的血管里奔腾,与他们血液里早已潜伏的头孢成分,发生那场注定致命的化学反应。双硫仑样反应。这个名词,是我在查阅了无数医学资料后,刻在脑子里的。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视线模糊、血压下降,最终导致休克甚至死亡。 多么美妙的词汇。为了今天,我准备了整整三个月。我假装病情好转,主动承担了家里的采购任务。家里的酱油、醋、料酒,甚至是我爸泡药酒用的高度白酒,都被我悄悄换成了含有微量酒精的特制调味品。剂量很小,不足以立刻引发反应,但足以在他们体内日积月累。而我每天吃的头孢药片,也并非全都进了我的肚子。 我将大部分药丸磨成无色无味的粉末,小心翼翼地混入他们每天必喝的汤里,撒进他们最爱吃的菜肴中。我是这个家的厨子,是他们的投毒者。他们吃下的每一口饭,喝下的每一口汤,都是我亲手递过去的催命符。信息差,多么迷人的东西。 我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一切。我知道他们引以为傲的健康身体,早已被我改造成了一个个精密的化学炸弹。而今晚这瓶82年的拉菲,就是那根被我亲手点燃的引线。“好酒!真是好酒!”父亲又为自己满上一杯,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阿昂,等你这个项目奖金下来,咱们再开一瓶更好的!”“爸,只要您开心,多少瓶都行。”陈昂的脸颊也泛起了红晕。酒精开始起作用了。 我紧紧攥着手中的玻璃杯,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在心里默数着。根据我查阅的资料,反应通常在接触酒精后的15到30分钟内开始。现在,过去了十分钟。“哎,我怎么觉得……有点热?”我妈王秀兰突然用手扇了扇风,她的脸颊浮现出不正常的潮红。 我心中一紧,来了!“妈,您是不是喝得有点急了?”嫂子李倩笑着说,但她自己的呼吸似乎也有些急促,“别说,这酒后劲还真大,我心跳得好快。”“是吗? 我怎么没感觉?”陈建国不以为意地摆摆手,“你们女人就是不能喝酒。来,阿昂,我们爷俩再走一个!”陈昂端起酒杯,正要与父亲相碰,他的手却在半空中顿了一下。 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爸,我……我头有点晕。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就是现在!我慢慢站起身,脸上努力挤出一个关切的微笑:“爸,妈,哥,你们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喝点水休息一下? ”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打破了其乐融融的假象。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陈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胡说八道什么!我们好得很! 你是不是看不得你哥好?”“不是的,爸。”我摇摇头,目光依次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 我看到母亲的潮红已经蔓延到了脖子和前胸,像一片片恐怖的红斑。 我看到嫂子开始不自觉地抓挠着自己的手臂,呼吸越来越困难。我看到我哥,那个不可一世的陈昂,正用手撑着桌子,身体微微发晃,他的嘴唇开始泛出青紫色。 只有我父亲,常年喝酒,身体底子好,目前还只是面色通红。“我只是觉得,”我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大家脸色都不太好。尤其是哥,你看,你都出虚汗了。 ”我的话,终于让他们意识到了不对劲。“我……我喘不上气……”李倩第一个尖叫起来,她捂着自己的胸口,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紧接着,陈昂“砰”地一声,一头栽倒在餐桌上,打翻了面前的酒杯。红色的酒液流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桌布。“阿昂!”“儿子! ”陈建国和王秀兰同时惊呼出声,饭桌瞬间乱成一团。我站在一片混乱之中,像一个冷漠的审判官,欣赏着我亲手导演的杰作。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上演了。 父亲慌乱地去扶我哥,却发现他浑身滚烫,已经开始意识模糊。母亲想去打急救电话,可她自己也已经站不稳,扶着椅子瘫软下去,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她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没用的。”我轻声说。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混乱中却异常清晰。陈建国猛地回过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陈默!是你!是不是你干了什么?!”他终于不蠢了。 可惜,太晚了。我看着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个灿烂的、发自内心的微笑。“爸,你还记得吗?一年前,我求你的时候,你说,我们陈家没有赌徒。”我顿了顿,环视着这满屋的狼藉和痛苦,一字一句地说道:“没错,我们陈家没有赌徒。因为今晚,我做庄,而你们,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我的话音刚落,父亲的身体也猛地一晃,他捂住自己的喉咙,脸上露出了和母亲、嫂子、哥哥一般无二的、极度痛苦和窒息的表情。 他体内的酒精,终于和我埋藏的头孢,完成了最后的合奏。一曲华丽的死亡乐章。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没有拨打120,而是打开了录像功能,对准了他们一张张因为缺氧而扭曲、狰狞的脸。这个家,这张餐桌,这张全家福,终于以我最期待的方式,永远定格。2手机镜头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正在上演一出精彩绝伦的默剧。父亲陈建国,这个家里的暴君,此刻正瘫在椅子上,双手死死掐着自己的脖子,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旧风箱般的声响。 他那张因为酒精和权势而常年红润的脸,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为猪肝色,然后是青紫色。他想骂我,想扑过来撕碎我,但缺氧的大脑已经无法有效指挥他的四肢,只能徒劳地抽搐着。我妈王秀兰,那个永远偏心的女人,已经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 她蜷缩在桌角,华贵的丝绸连衣裙皱成一团,脸上的红斑已经融合成一片,像是被人泼了硫酸。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每一次吸气都像一次凌迟,却只能吸入微不足道的空气。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瞳孔涣散,绝望地望着天花板上那盏璀璨的水晶灯,或许,那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光。嫂子李倩,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此刻的模样最是狼狈。她引以为傲的妆容已经哭花,呕吐物弄脏了她名牌衣裙的前襟。她趴在地上,像一条离水的鱼,徒劳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只戴着卡地亚手镯的手臂,无力地垂在一边,钻石的光芒在这一片狼藉中,显得格外讽刺。至于我的好哥哥,陈昂,陈家的骄傲,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他就那么趴在桌上,脸埋在流淌的红酒和菜汁里,一动不动。 只有后背还在轻微地、有节奏地痉挛,证明他还活着。我冷静地移动着镜头,确保将他们每个人的特写都录制下来。我要记录下他们最痛苦、最丑陋、最无助的瞬间。 这是他们欠我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呕吐物和死亡交织的酸腐气息。 我贪婪地呼吸着这股味道,感觉过去一年多来压在胸口的巨石,正在一点点被搬开。抑郁症? 不,我没有病。有病的,是他们,是这个家。我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家庭治疗”。就在我以为这场盛大的演出将以寂静的死亡告终时,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毫无预兆地响彻了整个屋子。 叮咚——叮咚——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像一把尖刀,瞬间刺破了我精心营造的、与世隔绝的审判场。我的心脏猛地一缩,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是谁?这个时间点,会是谁来?我的计划里,没有任何外人。我算好了一切,唯独没有算到这个意外。门铃声还在执着地响着,伴随着砰砰的敲门声。“建国?秀兰? 开门啊!是我,老刘!”一个熟悉的、洪亮的男声从门外传来。刘叔。我爸的牌友,也是我哥公司的老前辈,看着我们长大的邻居。他最是热心肠,也最爱凑热闹。 我脑中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怎么办?不理他?不行,他知道家里在庆祝,肯定会起疑。 让他进来?更不行,他会立刻看到这人间地狱般的景象。恐慌像潮水般涌来,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慌,陈默,绝对不能慌。游戏才刚刚开始,不能在这里就前功尽弃。我迅速停止录像,将手机揣回兜里。然后,我深吸一口气,环顾了一下餐厅。一片狼藉,四个濒死的人。这个场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 我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合理的“信息差”。我快步冲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左臂上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剧痛传来,温热的血液立刻涌了出来,顺着我的手臂滴落在地。疼痛让我更加清醒。接着,我冲回餐厅,抓起一个空酒瓶,狠狠地砸在地上,玻璃碎裂的声音刺耳又真实。然后,我故意撞翻一把椅子,弄出更大的响动。做完这一切,我用没受伤的右手捂住流血的左臂,跌跌撞撞地冲向门口。 在开门前,我对着猫眼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让它看起来充满了惊恐、无助和仓皇。 “谁……谁啊?”我用颤抖的声音问道,仿佛一只受惊的兔子。“小默?是我,刘叔! 你家怎么了?我刚在楼下好像听到有东西砸碎的声音?”“刘叔……”我带着哭腔拉开了门,身体一软,顺势靠在门框上,“刘叔,快……快救救我爸妈他们! ”刘叔被我满身是血的样子吓了一跳,连忙扶住我:“小默,怎么回事?你这胳膊……哎呀! 你家这是怎么了?”他探头向屋里望去,当他看到餐厅里的景象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这……这是……”他目瞪口呆,显然被眼前的一幕冲击得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开始了我准备好的表演,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我们……我们正在吃饭,给我哥庆祝。突然……突然我哥就倒了,然后我妈,我嫂子,还有我爸,全都……全都倒下了。我吓坏了,想去扶我爸,结果他好像疯了一样,把我推开,还拿酒瓶砸我……”我一边说,一边指向地上的玻璃碎片和流血的手臂,每一个细节都在佐证我的谎言。“集体中毒?”刘叔毕竟是见过些世面的,立刻反应过来,“是食物中毒还是煤气中毒?不对,窗户开着……”“我不知道啊刘叔!”我哭喊着,抓着他的胳膊,“他们刚才都喝酒了,就我没喝,我喝的橙汁,所以我才没事! 是不是酒有问题?刘叔,你快帮忙打120吧!我……我的手抖得拿不稳手机! ”我把“喝酒”这个关键信息,以一种最自然、最无辜的方式,传递给了第一个现场目击者。 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唯一的受害者。刘叔立刻被我带入了节奏,他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对对对,打120!小默你别怕,叔在这儿!”他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焦急地描述着地址和情况:“喂!120吗?这里是xx小区x栋x单元xxx! 出大事了!一家四口好像是食物中毒,全都昏迷了,还有一个孩子也受伤了!你们快来啊! ”挂了电话,刘叔想进屋查看情况,我立刻拦住了他。“刘叔,你别进去! 我怕……我怕这屋里有什么毒气……”我用恐惧的眼神看着他。“好好好,不进去,我们就在门口等。”刘叔扶着我,不停地安慰,“别怕孩子,救护车马上就到。 ”我靠在他身上,身体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内心却是一片冰冷的平静。我知道,我的第一步计划,成功了。我不仅是投毒者,还是唯一的报案人、受害者和幸存者。 在等待救护车的几分钟里,我的思绪飘回了三年前。那也是一个晚上,我哥陈昂同样喝了酒,开着他那辆宝马,载着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路上,他为了跟一辆跑车飙车,在一个路口闯了红灯,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瓶车。骑车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被撞飞出去十几米远。我当时吓傻了,催促我哥赶紧打120。可他是怎么做的? 他第一时间不是救人,而是打电话给了我爸。我爸在电话那头,声音冷静得可怕。 他只说了三句话:“第一,不准报警。第二,不准叫救护车。第三,你现在立刻离开现场,剩下的我来处理。”“爸!那个人……”我抢过电话想说什么,却被我哥一把推开。 “你懂个屁!听爸的!”他冲我低吼,眼睛里满是惊慌和自私。后来,我爸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和金钱,摆平了这件事。那个女孩没死,但断了一条腿,成了终身残疾。他们给了女孩家里一笔钱,让她父母签了谅解书,条件是永远不许再提这件事。而整件事的责任,被推到了一个愿意顶包的醉驾司机身上。 从始至终,我哥陈昂没有去看过那个女孩一眼,没有道过一句歉。我们全家,包括我妈和嫂子,都默契地对此事绝口不提,仿佛它从未发生。只有我,夜夜被那个女孩倒在血泊中的画面惊醒。我试图跟他们理论,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记耳光。 “你给我闭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再敢提一个字,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你哥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不能有任何污点!”那一刻我才明白,在这个家里,没有对错,只有利益。没有亲情,只有价值。我哥是有价值的,所以他的罪恶可以被掩盖。而我,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良知一文不值。我的抑郁,从那天起,便种下了根。 尖锐的救护车鸣笛声将我从回忆中拉回。我看着医护人员冲进屋子,将我那四个“家人”一个个抬上担架,我的嘴角,在刘叔看不见的角度,微微勾起。 我当然知道他们不会死。至少,现在不会。我查阅过,双硫仑样反应虽然凶险,但只要抢救及时,死亡率并不高。我给他们下的头孢剂量,经过了精确的计算,足以让他们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却又留有一线生机。杀了他们?太便宜他们了。 死亡是一瞬间的解脱,我要的,是比死亡更漫长、更深刻的折磨。我要他们活着,清醒地活着,看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如何被我一点一点地,全部摧毁。“小默,你也得上车,去医院包扎一下伤口。”一个护士对我说。“好。”我点点头,乖巧地跟了上去。坐上救护车,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灯火通明,满地狼藉,仿佛一场战争刚刚结束。不,战争不是结束了。而是,才刚刚开始。我的计划,环环相扣。今晚,只是一个华丽的开场。我期待的,是接下来更精彩的大戏。 而我手里那段录像,就是送给我亲爱的家人们,苏醒后的第一份大礼。3医院的急诊室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刺鼻,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我坐在冰冷的塑料长椅上,左臂缠着厚厚的纱布,伤口缝了七针,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去,只剩下木然的钝痛。我低着头,双手插在发间,努力扮演着一个惊魂未定、濒临崩溃的儿子和弟弟。 我的“家人们”被分别送进了不同的抢救室,门上的红灯亮着,像四只嗜血的眼睛,冷漠地注视着我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刘叔陪在我身边,不停地拍着我的背,嘴里念叨着:“没事的,小默,别怕,医生肯定能救回来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用肩膀的颤抖来回应他的安慰。我的大脑,此刻却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运转着。 医生和警察,他们很快就会来问话。我的说辞必须天衣无缝。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刘叔,问道:“谁是病人家属?”“我是,我是他儿子。”我立刻站起来,声音沙哑地应道。 “你父亲他们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是典型的双硫仑样反应。”医生言简意赅,语气里带着一丝职业性的审视,“他们是不是在服用某些药物期间,喝了酒?”来了,关键问题。我眼中立刻蓄满泪水,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茫然和无辜:“双什么……反应? 医生,我不知道啊。我们家没人吃药啊,除了……除了我。”“你?”医生的目光锐利起来。 “我……我有点抑郁症,一直在吃药。”我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蝇,仿佛在陈述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我吃的药里,有一种叫头孢拉定胶囊。”我说完,小心翼翼地抬眼看着医生,眼神里充满了“难道是我的错”的恐慌。医生的眉头紧紧皱起,他显然捕捉到了“头孢”这个关键词。“你确定只有你一个人在吃药?”“我确定!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的药都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他们……他们平时连我房间都不进的。而且今晚,他们都喝了酒,就我因为吃药,医生叮嘱过不能喝酒,所以我喝的橙汁。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会……”我的表演恰到好处。我抛出了最关键的线索——头孢,但又将自己完美地摘了出去。我是一个遵医嘱的病人,一个因为没喝酒而幸免于难的幸运儿。 而他们,是四个在未知情况下摄入了头孢又饮酒的受害者。这盆脏水,我泼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医生沉吟片刻,大概也觉得事情蹊跷,便没再追问,只是说:“我们会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你先别急,等警察来了,配合他们做个笔录。 ”医生刚走,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就到了。一老一少,老的那个看起来经验丰富,眼神像鹰一样。“陈默?”老警察开口问道。我点点头。“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 你家里的情况,我们需要你详细说一下。”我深吸一口气,将早已在心中排练了无数遍的说辞,用一种混合着恐惧和悲伤的、断断续续的语气,又重复了一遍。从晚宴的起因,到哥哥突然倒下,再到全家人相继出现恐怖的症状,最后,是我在惊恐中被“发疯”的父亲砸伤,然后拼尽全力跑出去开门求救。我的叙述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酒瓶的碎片,我手臂上的伤,刘叔的证词,以及我因为吃药而滴酒未沾的事实,所有证据链都指向一个结论:这是一场意外的、原因不明的集体中毒事件,而我,是其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年轻的警察负责记录,老警察则一直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想从我的微表情中找出破绽。“你说,你父亲用酒瓶砸你?”老警察突然发问。 “是……是的。”我点点头,眼中流露出后怕的神色,“他当时的样子很吓人,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全是血丝,就像……就像不认识我一样,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然后就抓起桌上的酒瓶朝我扔了过来。我躲了一下,但还是被划伤了胳膊。”“他喊了什么,你听清了吗?”“太乱了,我没听清……好像……好像在骂我……”我低下头,肩膀又开始抽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我只是想去扶他……”我将父亲最后的、清醒的指控,模糊成了一个病人中毒后的胡言乱语和暴力行为。这样一来,等他醒来后,无论他说什么,都会被先入为主地打上“神志不清”的标签。信息差,就是我此刻最坚固的堡垒。 老警察沉默了,他似乎没有找到任何疑点。盘问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抢救室的灯接二连三地熄灭,医生通知我们,四个人都已脱离生命危险,转入重症监护室观察。我“长舒了一口气”,瘫倒在椅子上,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刘叔和警察都过来安慰我,说我受惊了,让我好好休息。我知道,最危险的一关,我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我亲爱的家人们,一个个苏醒过来。我无比期待,他们睁开眼看到我时,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第一个醒来的是我爸,陈建国。 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我正坐在他的病床边,削着一个苹果。我削得很慢,很认真,长长的果皮连成一线,垂落下来。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 |
精选图文
 林枳陆云霄小说(林枳陆云霄)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枳陆云霄)林枳陆云霄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林枳陆云霄)
林枳陆云霄小说(林枳陆云霄)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林枳陆云霄)林枳陆云霄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林枳陆云霄) 重活一世,他和名妓私奔(重活一世,他和名妓私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江砚孟小蝶全文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列表(重活一世,他和名妓私奔)
重活一世,他和名妓私奔(重活一世,他和名妓私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江砚孟小蝶全文免费阅读最新章节列表(重活一世,他和名妓私奔) 姜楚盈周聿时小说(姜楚盈周聿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姜楚盈周聿时)姜楚盈周聿时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姜楚盈周聿时)
姜楚盈周聿时小说(姜楚盈周聿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姜楚盈周聿时)姜楚盈周聿时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姜楚盈周聿时) 温璃顾礼熔(温璃顾礼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璃顾礼熔免费阅读)温璃顾礼熔最新章节列表
温璃顾礼熔(温璃顾礼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璃顾礼熔免费阅读)温璃顾礼熔最新章节列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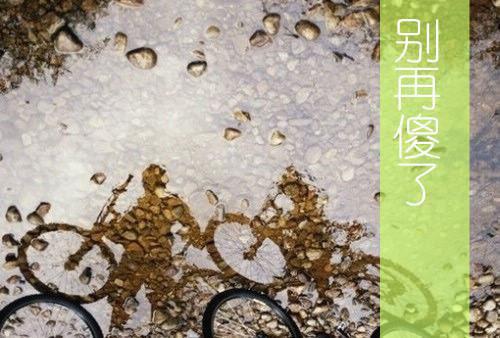 我都化佛了,你们还说木系不能上战场?最后结局如何 2023最火热点小说 林仓蒋梦云
我都化佛了,你们还说木系不能上战场?最后结局如何 2023最火热点小说 林仓蒋梦云 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小说(乔夏初容怀延 )全文免费阅读_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小说乔夏初容怀延 小说最新章节列表
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小说(乔夏初容怀延 )全文免费阅读_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小说乔夏初容怀延 小说最新章节列表 乔夏初容怀延推荐免费新书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推荐已完结 乔夏初容怀延今日更新最新章节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在线阅读
乔夏初容怀延推荐免费新书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推荐已完结 乔夏初容怀延今日更新最新章节末世囤货:这空间又双叒叕装不下了在线阅读 (简诺)2023最火小说全文 团宠小福宝,小丫头她才三岁半免费阅读
(简诺)2023最火小说全文 团宠小福宝,小丫头她才三岁半免费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