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逼宫,反手送她和渣男进监狱阮琴付怀瑾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小三逼宫,反手送她和渣男进监狱(阮琴付怀瑾)
|
1我这副金丝眼镜还是三年前离开村子时小雅送的。她说城里记者都该有副像样的眼镜,用她采山货攒了整整一年的钱,换来此刻架在我鼻梁上这道冰冷的金属弧线。 轮胎碾过泥泞村道时,黑压压的乌鸦群正从老槐树上腾空而起。 它们嘶哑的啼叫像钝刀割裂空气,车窗上瞬间布满凌乱的爪痕。 “鸦神显灵了...”穿蓑衣的老农蹲在田埂上喃喃自语,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我的车牌。 雨水顺着他的斗笠边缘淌成水帘,那水竟是诡异的锈红色。祠堂里祖母的棺木停在正中央,而更中央的是村民脸上那种糅合恐惧与狂热的扭曲表情。男人们往火盆里扔符纸,女人们跪在地上用指甲抠挖砖缝,嘴里念诵着我童年时常听见的古老祷词。
他们在为晚上的鸦鸣祭做准备——那个用乌鸦叫声占卜吉凶的荒唐仪式。“阿鸣回来了? ”粗糙的手掌突然拍在我肩上。村长陈富贵咧着满口黄牙笑,金牙在昏暗烛光下闪着油腻的光,“城里大记者还记得咱这穷沟沟?”我下意识后退半步。 他指缝里嵌着黑泥,指甲盖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三年前就是他带头说小雅“不洁”,说那姑娘的桃花眼会招来灾祸。暴雨是突然砸下来的。铜钱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敲在瓦片上,祠堂里的烛火疯狂摇曳。有人惊叫着指向房梁——那里不知何时落满了乌鸦,血红的眼珠在黑暗中连成一片嗜血星河。“鸦神怒了!”不知谁喊了这一嗓子,村民哗啦啦跪倒一片。陈富贵倒是挺着肥硕的肚子站在那儿笑,直到窗外划过一道惨白的闪电。雷声炸响时,我清楚地看见他脸上的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 守夜到后半夜,雨声渐歇。我靠着柱子假寐,突然被某种黏腻的声响惊醒。 像是湿漉漉的羽毛拖过地面,又像是...指甲抠刮木板。祠堂侧门虚掩着。 推开时腥风扑面而来,陈富贵仰面倒在血泊里,胸口的窟窿还在汩汩冒血。 三根漆黑鸦羽直挺挺插在心窝处,羽毛根部的皮肉已经翻卷发黑。 最骇人的是他裸露的皮肤——从脖颈到脚踝布满深可见骨的抓痕,那些伤口纵横交错组成诡异的图腾,像极了乌鸦的爪印。“鸦神降罚! ”闻声赶来的村民疯了一样磕头,额头撞在青砖上砰砰作响。我强忍着恶心蹲下身,电筒光扫过尸体右手时猛地顿住。在那片血肉模糊中,几点蓝色人造纤维牢牢嵌进指甲缝里。 绝不是乌鸦羽毛该有的东西。人群突然骚动起来。陈大虎提着猎枪冲进来,通红的眼睛瞪着我:“外姓人滚开!就是你带来晦气!”他枪管几乎戳到我脸上,浓烈的火药味混着酒气喷涌而来。我被推搡着退到墙角,后腰突然被什么硬物硌到。 趁乱摸出来一看,是半枚鸦神图腾银饰,断裂处还沾着新鲜的血迹。 心脏骤然缩紧——这图案和小雅当年贴身戴的吊坠一模一样。窗外就在这时传来鸦鸣。 三长一短,精准得像秒针走动。祠堂里的哭嚎声瞬间死寂,所有人脸色惨白地望向窗外。 陈大虎的猎枪“哐当”掉在地上。第二声鸦鸣接踵而至,这次近得仿佛就贴在后颈。 我猛地扭头,只看见漆黑窗玻璃上自己惊惶的倒影——以及倒影身后,那个佝偻的独眼老人正举着砍柴刀站在雨幕里。2雨水还在顺着屋檐滴答往下淌,空气里那股铁锈似的血腥气却已经散尽了。我捏着那半枚鸦神银饰,冰凉的金属边缘硌得指腹生疼。祠堂里乱哄哄的,陈大虎抱着他爹的尸体哭得像个三百斤的孩子,周围跪倒的村民还在不停磕头。 没人注意我悄悄退到阴影里,把银饰举到眼前细看。做工很糙,边沿还有毛刺,像是自家打的。可鸦神村早二十年就没银匠了,年轻人都往外跑,谁还学这老掉牙的手艺? 除非…我猛地想起个人。福伯。村西头那个瘸腿老光棍。小时候常见他坐在门槛上敲敲打打,给姑娘们打镯子,给娃娃打长命锁。他手上那套模具还是祖传的,全村独一份。 “福伯还活着?”我扯住一个正要往外溜的半大小子。那孩子吓得一哆嗦,看清是我才喘匀气:“活、活着呢…就是脑子不清爽了,见天蹲门口磨刀,说要宰了鸦神派来的勾魂使。”问清地址,我把银饰揣进兜,转身扎进雨幕里。 福伯家比印象中更破了。土墙塌了半边,茅草屋顶凹下去一大块,活像被巨人踩过一脚。 木门虚掩着,里头传出有节奏的敲击声。我推门进去。老头正背对着我,佝偻着身子在煤油灯下捣鼓什么。听见动静,他猛地回头,浑浊的眼珠在深陷的眼窝里转动,手里还攥着个小锤。“谁?”“福伯,是我,陆家小子。”我放缓声音,尽量显得人畜无害,“想请您帮忙看个东西。”他眯着眼打量我,目光落在我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时顿了一下,表情有些恍惚。“陆家小子…都长这么大了。”他嘟囔着,放下锤子,“看啥? ”我掏出那半枚银饰递过去。煤油灯噼啪爆了个灯花。福伯的手指刚碰到银饰就猛地缩回,像是被烫着了。那张布满老年斑的脸瞬间失去血色,嘴唇哆嗦起来。“这、这东西哪来的? ”“祠堂捡的。”我盯着他,“听说全村就您还会打银器?”老头突然发起疯来。 他一把抢过银饰扔进脚边的火盆,又踉跄着扑到墙角,从一堆废料里扒拉出个黑乎乎的铁盒子,举起锤子就砸!“不能留…都不能留…要遭报应的! ”他边砸边嘶吼,口水从嘴角滴落,“鸦神看着呢…全都看着呢!”我冲上去拦他,却被他一把推开。老人爆发出惊人的力气,几下就把铁盒子砸变了形,里头那些精细的模具叮叮当当散了一地。他还不解气,又抄起柴刀要去砍工作台。“福伯! 你冷静点!”我箍住他挥舞柴刀的胳膊,“这银饰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和小雅有关? ”听到小雅的名字,他整个人僵住了。柴刀“哐当”掉在地上。他缓缓转过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瞳孔里倒映着跳跃的灯火。 “那闺女…冤啊…”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像是破风箱在抽气,“他们…他们把她按在祭台上…那么多人看着…鸦神看着…我也…”他猛地抱住脑袋蹲下去,身子缩成一团剧烈颤抖。我再问什么他都不答了,只反复念叨着“鸦神看着”、“报应快了”。眼看问不出东西,我只好捡起地上几片还没彻底毁掉的模具残片塞进口袋,退出了这间弥漫着疯狂气息的屋子。 门外天已经黑透了。雨不知何时停了,月亮从云缝里漏出半张脸,照得满地水洼亮晶晶的。 我心里乱得很。福伯的反应太反常,那银饰绝对有问题。还有他未尽的话…祭台?什么祭台? 没等我想明白,远处突然炸开一声凄厉的尖叫。“死人了——又死人了!”心脏猛地一沉,我拔腿就往声音方向跑。越跑心越凉——那方向正是福伯家后面那片老林子,林子正中央,矗立着那棵不知道活了几百年的鸦神树。树下已经围了不少人,火把的光跳跃着,映亮一张张惊惶的脸。没人敢靠太近,全都挤在十几步外伸着脖子看。我也看见了。 福伯瘦小的身体吊在粗壮的横枝上,随风轻轻打着转。脖子被麻绳勒得变了形,舌尖吐出来老长,脸上还凝固着极度恐惧的表情。他那条瘸腿的裤管空荡荡地垂着,下面滴滴答答淌着水珠——或者别的什么液体。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裸露的胸口。 那里用某种锐器划得血肉模糊,图案正是一只展开翅膀的乌鸦,和银饰上的图腾一模一样。 “又一个…又一个祭品…”身边的老太太喃喃自语,手里念珠捻得飞快,“鸦神收人啦…都要死…谁都跑不了…”人群突然骚动起来。陈大虎提着猎枪挤到最前面,抬头看了一眼就破口大骂:“操他娘的!又一个外姓老杂毛找死!”他猛地扭头,通红的眼珠子剜在我身上,“还有你!下午是不是你来过?福伯死前就见你一个外人! ”猎枪抬了起来,黑黢黢的枪口对准我胸口。“说!是不是你搞的鬼?”我慢慢举起手,脑子飞快转动。这蠢货显然想找个替罪羊平息恐慌,但和他硬碰硬不划算。“我下午是来过,”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福伯当时情绪很不稳定,砸了很多东西,还说了些胡话。 我担心他出事才来看看,没想到…”“放屁!”陈大虎啐了一口,“就是你! 自从你回来就没好事!爹死了,福伯也死了!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了?”他手指扣上扳机,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就在这时,吊在树上的尸体突然剧烈摇晃起来! 一股邪风卷着落叶扑簌簌打转,火把明灭不定。福伯僵硬的腿撞在树干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有什么东西从他松开的袖口掉了出来,啪嗒落进树下积水的泥坑里。 是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所有人的目光都盯住了那东西。 陈大虎显然也看见了,脸色变了几变,枪口微微下垂。趁他分神的刹那,我猛地侧身撞开身边一个看热闹的半大小子,在那孩子哎哟的叫声中就地一滚,抓起泥坑里的油布包塞进怀里,扭头就往林子深处跑!“操!拦住他! ”陈大虎的咆哮和枪声同时在身后炸响。子弹啾地擦过耳畔,打在旁边树干上,溅起一片木屑。我顾不上回头,拼命迈开两条腿。多年城市生活掏空了身体,肺叶火辣辣地疼,但童年在这片林子里疯跑的记忆还在。我灵活地绕过树根和石块,把身后的叫骂和脚步声越甩越远。直到彻底听不见动静,我才敢靠着一棵老槐树喘气。 胸口心跳得像要炸开,手指哆嗦着摸出那个油布包。剥开层层油布,露出本手缝的册子。 封面上用娟秀的字迹写着《采药札记》,右下角是个小小的“雅”字。是小雅的字。我认得。 深吸一口气,我翻开第一页。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草药习性、采摘时节,偶尔夹杂着少女的心事。字里行间能看出这是个认真又温柔的姑娘,梦想着攒够钱就去山外读卫校。直到中间某一页,画风陡然一变。三月十七,阴。 后山的鸦羽开了,我去采药。陈大虎从后面抱住我,手往衣服里摸。我咬了他跑了。恶心。 三月二十,雨。他又堵我,说给他摸几下就给我钱。我用药锄砸破他的头。 他骂我是外姓贱货,说让他爹把我家地收回去。四月末,忘了日子。 他们…他们好几个人…在祭台…好疼…鸦神看着…所有人都在看…字迹从这里开始凌乱,页面上有点点干涸的暗褐色痕迹,像泪痕,又或者…血。最后几页全是狂乱的涂鸦,黑色的乌鸦,扭曲的人脸,密密麻麻的眼睛。 最后一页用深红色的、黏腻的液体写着一行大字:他们都在看!!!都在看!!! 每一个惊叹号都力透纸背,像绝望的呐喊。我合上册子,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多年前那个桃花眼姑娘的笑脸在眼前晃动。她说:“鸣哥,城里是不是真有五层楼高的百货大楼?”远处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吆喝,火把的光在林间晃动。陈大虎带人搜过来了。我把册子塞回怀里,猫着腰往林子更密处钻。 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把这东西藏好。祠堂!现在所有人都在林子里,祠堂反而最安全。 而且我记得祠堂后厢有个堆放杂物的旧档案室,或许能找到更多线索。凭借记忆绕回村子,祠堂果然空无一人。灵堂的白蜡烛还在烧着,映着中央那口空棺材,阴森得吓人。 档案室锁着,但老式挂锁经不起我两脚。屋里弥漫着灰尘和霉味,成摞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 我打开手机电筒,快速翻找起来。死亡记录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我直接翻到三年前。 赵小雅,女,十六岁。失足落水溺亡。短短一行字,像冰冷的钉子。 落款是村长陈富贵的签名,盖着村里红戳。操。我忍不住骂出声,手指用力到几乎把纸页捏破。失足落水?那么会水的姑娘?死在旱季深不及腰的小溪里? 我不死心,捏着那页纸对着光仔细看。纸张明显比前后页新,像是后来替换的。 指尖摩挲着纸缘,忽然感觉到一点突兀的厚度。轻轻捻开边缘,里面竟然藏着张对折的纸条! 抽出来展开,是一张镇卫生院的产检单。姓名:赵小雅年龄:16诊断:宫内早孕,约12周检查日期,正是她所谓“失足落水”的前一天。血液瞬间冲上头顶,耳边嗡嗡作响。 所有碎片在这一刻轰然拼凑——侵犯,怀孕,被灭口,伪装成意外。而福伯,那个可能知情的银匠,也成了鸦神树上的祭品。好一个鸦神村。好一个“失足落水”。 愤怒和恶心让我浑身发抖。就在这时,窗外毫无预兆地响起了鸦鸣。不是杂乱无章的啼叫,而是精准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奏。三长一短,和祠堂那晚一模一样。我猛地关掉手机电筒,屏息缩到窗边。月光下,那个佝偻的独眼身影正站在村道中央,面朝祠堂方向。 他微微仰着头,喉结滚动,那催命的鸦鸣正是从他喉咙里发出的!他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缓缓低下头。那只独眼似乎穿透黑暗,精准地锁定了我藏身的位置。干裂的嘴角慢慢咧开,形成一个扭曲到极点的笑容。然后他转过身,不紧不慢地朝着村东头走去。 那边…是村小学的方向。3我猛地从祠堂窗边缩回头,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赵伯那佝偻的身影正不紧不慢地消失在通往村小学的土路尽头,月光把他拖出一道扭曲的长影。小学。他去小学做什么? 脑子里瞬间闪过小雅日记里那些触目惊心的血字,还有产检单上冰冷的“12周”。 下一个…是林秀?那个总是扎着马尾辫,说话轻声细气的代课老师? 小雅生前唯一还算说得上话的人。操。我低骂一声,再也顾不上会不会被陈大虎那伙人发现,猛地从祠堂后窗翻了出去,落地时踩进一洼泥水,冰凉的泥浆瞬间灌满了鞋袜。 管不了那么多。我沿着屋檐下的阴影发足狂奔,夜风刮过耳畔,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血腥气。 村小学就在村子最东头,一排低矮的瓦房,围着一圈歪歪扭扭的木头栅栏。 小时候我常和小雅偷爬进去,坐在单杠上看星星。她说总有一天要飞出这鬼地方。 栅栏门虚掩着。我闪身进去,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间教室还亮着昏黄的灯。 心跳得更快了。我猫着腰摸到窗边,小心翼翼探出半只眼睛。教室里没人。 讲台上摊着作业本,粉笔盒打翻了,白色的粉末洒了一地。黑板上还写着半道数学题。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太正常了。正常得让人头皮发麻。赵伯明明往这个方向来了,他人呢? 我屏住呼吸,视线仔细扫过教室的每个角落。突然,讲台旁边地板上一点暗沉的反光抓住了我的目光。是血。还没完全凝固,黏糊糊的一小滩。 旁边散落着几根漆黑的乌鸦羽毛,硬挺的羽根沾着猩红。血滴断断续续,指向教室后门。 后门开着一条缝,外面是黑黢黢的后山。我推开后门,一股混合着泥土和腐叶的冷风扑面而来。血滴在门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草地上被拖拽的痕迹,一路蜿蜒着通向半山腰。那座山叫鸦嘴岩,小时候老人总吓唬我们说上头住着吃小孩的鸦神。痕迹尽头,似乎有个被藤蔓半遮住的黑洞。 是山洞。祭台?福伯临死前嘶吼的“祭台”? 我拔出腰间别着的柴刀——刚从祠堂杂物间顺来的——砍开纠缠的藤蔓,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霉味混合着涌出,呛得人直恶心。山洞很深,壁上插着几支快要燃尽的火把,光线摇曳,投下鬼魅般的影子。洞壁被人为打磨过,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诡异符号和乌鸦图腾,无数双刻出来的眼睛在火光下仿佛都在转动,死死盯着闯入者。正中央是一块平坦的巨石,打磨得光滑如镜,上面用深褐色的、干涸的血画着巨大的鸦神图案。林秀就躺在石台上,双眼紧闭,脸色白得像纸。手腕被粗糙的麻绳捆着,固定在石台两侧凸起的石笋上,脚踝也是。 额角破了,血顺着太阳穴流进鬓发里。她还活着,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林秀! ”我压低声音喊她,几步冲过去,柴刀刀刃割向麻绳。绳子比想象中结实,割得我虎口发麻。 就在最后一根绳索即将断裂的瞬间,脚下突然传来“咔哒”一声轻响。 像是某种机括被触发了。我心里猛地一沉。轰隆隆——头顶传来令人牙酸的巨石摩擦声! 大大小小的碎石和泥土簌簌落下,一块巨大的山岩猛地砸落在洞口,彻底封死了出路! 紧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整个山洞都在震颤,灰尘弥漫。完了。最后一点光线被彻底隔绝,只剩下壁上那几支苟延残喘的火把,发出噼啪的悲鸣。 “咳…咳咳…”石台上的林秀被尘埃呛得苏醒过来,她茫然地睁开眼,待看清周遭环境和眼前的我时,瞳孔骤然收缩,发出惊恐的呜咽。“别怕!是我,陆鸣! ”我按住她挣扎的肩膀,“怎么回事?谁把你绑来的?是不是赵伯?”听到赵伯的名字,她浑身一颤,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混合着脸上的血污往下淌。 “他…他疯了…鸦神…赎罪…”她语无伦次,牙齿磕碰得咯咯响。“什么赎罪?说清楚! ”我捏着她肩膀的手用力了些,强迫她冷静,“小雅的事,你知道多少? 她是不是被陈大虎他们…”林秀的哭声戛然而止。她瞪大了眼睛,恐惧几乎要溢出眼眶,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摇头。“说话啊! ”压抑了一晚上的怒火和恶心终于窜了上来,“他们都死了!村长死了!福伯死了! 下一个可能就是你我!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小雅把你当朋友!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崩溃地哭喊,声音嘶哑,“放过我吧…我不能说…”“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我盯着她,“你去找过村长,对不对?小雅出事后,你去求过他主持公道?”林秀猛地僵住,像是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是能看透人心的怪物。“他…他把我赶了出来…”她终于崩溃,话语混着泪水决堤而出,“他说小雅是自己不检点,勾引他儿子…说如果我敢乱说,生…”她的身体因为恐惧和回忆剧烈颤抖起来:“那天…那天我看见了…小雅跑出来的时候,我想帮她…可是陈大虎他们追出来…那么多人都看着…没人敢拦…没人…”她的声音低下去,的自责:“我看着他们把她拖回去…我跑了…我没用…我该死…”洞壁的火把又熄灭了一支,阴影更深了。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带着诡异笑意的声音,突然从头顶某条岩石缝隙里钻了进来,缥缈得像是地狱传来的回音:“看了…就是同谋…”是赵伯的声音!“鸦神…只要血债血偿! ”话音未落,几条细长的、滑腻的影子猛地从岩壁四周的缝隙里被抛了进来,噼里啪啦掉在我们周围的地上,迅速扭动着昂起头。是蛇!好几条!三角形的脑袋,猩红的信子嘶嘶作响,竖瞳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毒蛇!林秀发出凄厉的尖叫。 最近的一条猛地弹射起来,直扑我的面门!我想都没想,挥起柴刀猛地一劈!蛇头飞了出去,腥臭的血溅了我一脸。但更多的蛇游了过来,速度极快,把我们逼得紧贴冰冷的石壁。“火! 怕火!”我猛地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去摸口袋。手机早就没电了。 烟盒里只剩两根皱巴巴的烟,还有个廉价的一次性打火机。 |
精选图文
 简奕阳安枝予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安枝予简奕阳)
简奕阳安枝予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安枝予简奕阳) 司荣轩胡灵莎小说小说最新章节_司荣轩胡灵莎小说免费阅读
司荣轩胡灵莎小说小说最新章节_司荣轩胡灵莎小说免费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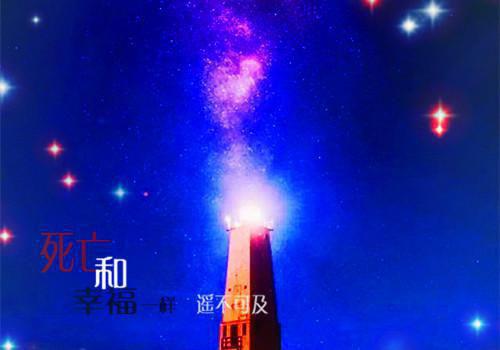 许浩辰安怡棠(安怡棠许浩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浩辰安怡棠)
许浩辰安怡棠(安怡棠许浩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许浩辰安怡棠) 许浩辰安怡棠全文安怡棠许浩辰用完结版免费试读
许浩辰安怡棠全文安怡棠许浩辰用完结版免费试读 司梦佳傅时璟免费阅读无弹窗司梦佳傅时璟(司梦佳傅时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司梦佳傅时璟)司梦佳傅时璟最新章节列表(司梦佳傅时璟)
司梦佳傅时璟免费阅读无弹窗司梦佳傅时璟(司梦佳傅时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司梦佳傅时璟)司梦佳傅时璟最新章节列表(司梦佳傅时璟) 傅峥慕音(慕音傅峥)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傅峥慕音)
傅峥慕音(慕音傅峥)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傅峥慕音) 慕音傅铮免费阅读无弹窗慕音傅铮(慕音傅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慕音傅铮)慕音傅铮最新章节列表(慕音傅铮)
慕音傅铮免费阅读无弹窗慕音傅铮(慕音傅铮)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慕音傅铮)慕音傅铮最新章节列表(慕音傅铮) (冯熙芷蒋浔轩)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冯熙芷蒋浔轩阅读无弹窗)冯熙芷蒋浔轩最新章节列表(冯熙芷蒋浔轩)
(冯熙芷蒋浔轩)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冯熙芷蒋浔轩阅读无弹窗)冯熙芷蒋浔轩最新章节列表(冯熙芷蒋浔轩)

